♦ 本文轉載自 雅理讀書。若有侵害著作權,請速告知,我們將盡速移除 ♦
2020/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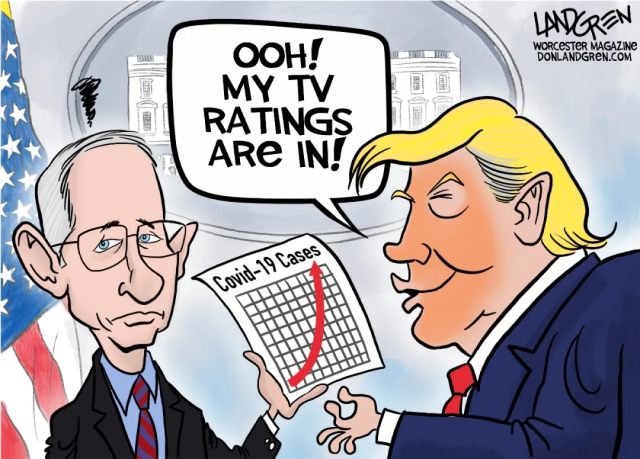
本文揭示了選主體制如何把政治代表的資格變成陌生權貴的私人財產。我們今天應當思考的是,如何才能發展出一套更有效能與回應性的代表制體系,以超越作為陌生權貴私產的代議制體系。作者拉尼·吉尼爾為哈佛大學法學院Bennett Boskey法學講座教授,本文譯自Lani Guinier, “Beyond Electocracy: Rethinking the Political Representative as Powerful Stranger,” The Modern Law Review, Vol. 71, No. 4 ( 2008), pp. 1–35,以下為節選。全文收入王紹光主編、歐樹軍譯:《選主批判:對當代西方民主的反思》,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第1版,第87-134頁。若您閱讀後有所收穫,敬請關注並分享”雅理讀書“(微信公號:yalipub)。
在一些歐洲國家…老百姓不關心村莊的狀況,不關心街道的治安,不關心教堂或牧師住所的修繕,他們認為這一切與己無關,那是政府這個陌生權貴的事。
——托克維爾,《民主在美國》第一卷第五章
選舉越多越民主嗎?我的答案比較負面:通過選舉的統治,也就是我所說的選主,並不充分滿足民主的價值需求。選主是指一種以神聖選擇權自居的政治環境。競爭性比賽下的選擇行為會產生一個明確的獲勝者。通過投票表決,公民把民主責任授予獲勝者。同時,贏得競爭的勝利者甚至比投票者更重要。選民比公民參與的質量與數量更重要,比其他重要的自治政治行為的政策後果更重要,比如審議、說服或集體動員等等。
我的主張是,專注於選舉,無法實現它所承諾的對全體人民負責,在贏者通吃的政治環境下尤其如此。儘管現代代表觀暗示代表在某些方面受被代表者意志的約束,但代表在歷史上是被選出來約束其選民的,而不是相反。我們的選主制延續的正是這樣的歷史,它常常服務於把政治力量轉化成世襲特權。
作為選主體制的關鍵,選舉甚至再選都沒有成為民主問責的首要來源。首先,選舉太容易鼓勵貴族式馴順。選民被訓導將自己對官員的權力龜縮於一個神聖的選擇時刻。這個過程讓他們屈從於當選官員的判斷、品格或者眼界,直到下次選舉到來。其次,這個過程導致代表們將自己視為金錢施主的代理人,而不是選民的代理人。與官員保持不間斷聯繫是選舉施主們的利益源泉。相比之下,在兩次選舉之間的間歇期,選民們實在無法讓自己在選舉日的決定產生預期結果。第三,在贏者通吃式選主制下,比如在美國,選區劃分將實際選擇權從選民手中奪走,轉交給政客。現任政客控制著選區劃界權;他們可以選擇選民。在選民走向投票站之前,真正的選舉早就開始了。許多代議士確信自己會在劃分不公的選區中再次當選,他們成為自己權位的專有者,他們把自己的權位視為一種職業,而不是受制約的服務平台。
選主制的這些特徵疊加在一起,強化了下述觀念:代表對其權位擁有獨占權或所有權。當選官員學會了把自己的官職視為一種“代表財產”(representational property)。與巴倫內斯·惠特克的同僚們一樣,他們覺得應該對自己的位置行使專有控制權,不是臨時看守,而是長期優先擁有。久而久之,他們越來越像“陌生的權貴”,就像托克維爾筆下19世紀歐洲一些鄉村的政府官員那樣。

正如托克維爾所警告的,一旦政府被視為“陌生權貴的財產”,老百姓就不怎麼關心村莊狀況、街道治安了。老百姓就不再相信政府兌現承諾的能力了。一旦不滿的老百姓開始把政府看作是別人的財產,他們甚至就不去投票了。
請大家注意,我並非主張我們應該放棄選舉。相反,我是想說,對於民主問責、民主結果和民主過程而言,無論選舉本身如何進行,只有選舉這個工具是不夠的。選舉常常是決策過程中的一個必要的整合步驟,但是,一旦我們把民主和選民參與縮減為一系列互不相干的選擇點,就貶低了民主,損害了選民參與。一旦我們把公民參與的要義界定為全體選民的投票能力,代議制民主的目標、結果和過程就都會落空,而代議制民主的結果、過程正是其自身正當性的體現。
我們的選主體制
當代美國選主體制的激勵結構強化了一種歷史模式。投票行為與被代表經驗之間毫不相關,這種感覺與更早的理念聯繫在一起:在早期英國國會中,代表約束選民,而非選民約束代表。而且危險的是,在美國,代表選舉最初就是用來認可“自然貴族”的,代議士與特權階層之間的契合得以延續。今天,許多政客念茲在茲的,不僅是確保再次當選,還有提高自己任內和任後的社會地位。此外,正如早期英國國會代表那樣,今天政客們的首要關鍵關係人並不是選民,而是其他內部人。與出資助選的金主之間的非正式關係(我稱之為“水平關係”),取代了與選民之間的正式關係(我稱之為垂直關係)。在非正式層面,政客、大選金主、說客通過重重複雜的關係網進行權權交易,靜態的選擇點對這類交易並不重要。同時,現代大選的各種需求,鼓勵政客們放棄而不僅僅是忽視潛在的選民。
意識到自己被拋棄了,選民們對這種政治體系狐疑滿腹。在一項全國民意測驗中,過半數受訪者、超過三分之二的黑人受訪者,非常懷疑自己的投票是否算數。政治犬儒主義已經從政治“制度”蔓延到了公民自己的代表。34-55%的選民相信國會議員收受賄賂。在最近的一項調查中,71%的美國人認為議員們將黨派政治擺在選民利益前面;其中63%的人強烈認同這個觀念。一名進行這項調查的跨黨團體成員認為,美國現在的實際政治狀態至少是“高度不穩定的”。如果一般美國人都持這種懷疑論,非洲裔美國人就更是如此了。2007年4月,南卡羅萊納州700名黑人接受了一項調查,77%認為華盛頓的政治過程“漏洞百出”,69%認為美國的前進方向錯了。
世界上還存在另一套歷史悠久但卻不那麼為人所知的傳統,就像英國早期的國會代表,或者詹姆斯·麥迪遜所想像的理想領袖那樣,“最好”或者“最高貴”的人被期待棲息於不同的世界,對不同的利益負責,而不僅僅是選民的利益。那麼,貴族制與代議制民主之間也就存在著一種緊密而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關聯,這種關聯已經永久地嵌入了美國當代選主體制的方方面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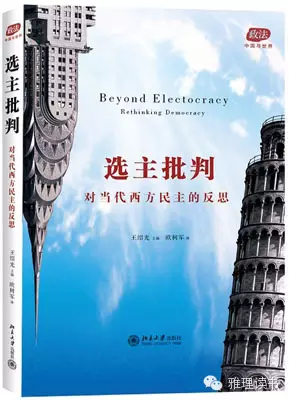
王紹光主編、歐樹軍譯:《選主批判:對當代西方民主的反思》,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第1版
代表作為陌生權貴的財產
在選主制中,據說人民參與治理是通過選別人來替自己做做主。當選者通過扮演一個或幾個角色來代表選民利益。他們或是充當受託人(trustee),通過與其他立法者進行協商,但最終徵詢良心,來代表公共利益、採取行動;或是充當代表(delegate),忠心履行選民賦予的使命;或是把自己當作一面反射鏡(Descriptive Mirror),準確反映選民的社會特徵。代表的反射論可能是最有爭議的。但是,所有這些角色都假定,選民利益相當靜態,代表能夠或者應該在個體意義上行動起來,弄清楚這些利益到底是什麼;提供個人選區服務是諮詢或者吸引選民的一種手段。
這些有關代表的傳統理解方式都假定,代表的角色直接來自當選這一事實。根據選後製度激勵,當選官員可以或者應該單方行動,將選舉結果轉變成為一個角色。每兩年、四年或者六年需要再次面對選民,這是一條在形式上約束代表如何解釋自己角色的紀律,選舉將權力從人民手中讓渡給了代表。這種權力讓渡給了在位官員一種賦權感,放鬆了人民與其政府之間的聯繫。正如托克維爾的評論,公民開始“覺得事不關己”。
代表可以被視為通過贏得公開競賽而獲取的一種公共地位。然而,在選民走向投票站之前,與該地位相關的一切都已經確定了。儘管選擇時刻因發生在選舉期間而被神聖化,但實際上,在此之前,選擇時刻早在選區劃分過程中就已經發生了。而在選區劃分這個真正關鍵的選擇時刻,選民並沒有參與。選區劃分一般比選民正式投票日早得多,在位當選官員深深捲入這個高度黨派化的過程中。在自私自利的黨派分子控制下,選區劃分會觸發一系列涉及技術專家和政客的水平關係,這些人操控確定選區邊界的程序,表面上卻要擺出符合美國最高法院人口均等原則的樣子,這項原則要求選區所囊括的人口數量必須相等。代表們就是通過這個過程來選擇選民,他們這麼做是基於選民認同假設。由於這個過程基本上是在密室政治中完成的,膽大妄為的現職政客們傾向將選民驅趕到人為劃定的政治單元之中,把選民與代表栓在一起,賦予同一種身份:民主黨人或共和黨人、福音派基督徒或主張墮胎合法的女性主義者,這樣做的目的只有一個,即讓在位者得以保持對該選區的政治控制。通過選區劃界,現職政客實際上提前決定了選舉結果,而選民投票則是很久以後的事了。

地理區域與選區劃分混在一起製造出符合憲法的過程,其受益者正是在任者。自私自利的在任者將單議席贏者通吃制選區,重塑為自己界定、控制和保護的選舉財產。與托克維爾所譴責的陌生權貴一樣,政治當權者學會了把選區和區內選民視為一種“代表財產”。這實際上是假定在職官員將來也有資格擁有這個位置,尤其是那些已經連任數屆的官場老油條們。與他們在早期英國國會歷史上的先輩一樣,代表在本質上約束了選民,而非相反。
無論是反射(鏡子)、代表(使命)還是受託人(德智兼備),無論全體一致還是勉強多數當選,代表個體都代表整體,並代表全體選民做決策,甚至也代表那些沒有投票給他的人。由於結果是贏者通吃,無論誰獲得51%的選票,他都可以代表整個選區,包括那些投反對票的人。剩下的49%“事實上”也被代表了,因為代表是“本選區”的代理人,他或她被假定會為區內全體民眾服務。這種實質代表(virtual representation)意味著當選官員也是其反對者的代理人,儘管那些人並不支持或“不同意”由當選官員代表他們的利益。代表們代表生活在本選區的所有人,就好像本選區所有人事實上都支持她贏得選舉。同時,人們經常假定,在一個選區失敗的少數,在另一個選區可能在數量上處於多數,後者實質上代表了前者。換句話說,當選代表被假定既代表反對自己的人,也代表支持自己的人。她同時被假定也代表了那些如果能夠投票也會支持她的人。結果,代表既是本選區身份的“代理人”,也是其仲裁人。
假公濟私的兩黨政客都把他們所代表的選區視為專有利益,當他們劃分選區界線或者用政策倡議換取高額政治回報的時候,這種利益顯而易見。因此,這些治理單位會繁殖托克維爾筆下十九世紀中期歐洲鄉村的那種狀況。贏者通吃制選區會培育一種消極公民,他們遵從當選官員,最終與政府保持距離,這個政府被視為“陌生權貴的財產”。即便更多黑人或拉丁裔政客當選,他們也需要有組織的、動員起來的公民,來確保政客們在選後負起責任。得克薩斯州和紐約市所缺的,正是支持和鼓勵負責選民的製度結構,所謂負責選民指的就是動員起來的公民組織,它們既能讓當選官員對共同(儘管不必然固定)議程負責,也能在這些官員因為推動共同議程而受攻擊時保護他們。
相同的命運而不只是相同的長相:集體效能假設
在本部分,我把集體效能作為集體權力的一種表徵來加以討論。集體效能涉及的是從社會權力中建構政治能力的過程。在人民將鄰里、同事或者社團之間的網絡和紐帶轉化成為一種政治力量之前,這種權力處於蟄伏期。集體效能通常是由兩個相互增強的信念觸發的:一群人有能力作為一個群體採取行動,這種行動定會取得成功。
借用集體效能這個術語,我這裡試圖把民主問責的標準重新概念化,其重點是公民在政治上作為議程設置者而不僅僅是選舉者的集體智慧、集體信念、集體能力。集體效能尋求通過各種途徑擴大公民參與:1)在集體論壇或協商論壇中,而不僅僅是個體做出選擇;2)整個政治過程,而不僅僅是在選舉之前;3)各種提高“代表正當性”的方式;4)影響決策或政策制定過程;5)塑造利益不斷演化、、適時調整的負責選民;以及6)促使公民敢於承擔風險,富於創新意識,挑戰各類不公。然而,集體效能不會在選舉背景之外單獨作用。實際上,致力於集體效能可能會激發更多公民參與投票,無論是作為代表的選舉者,還是公民複決或創始的投票者。通過讓人們相信自己有能力做出影響自己生活的決定,促進集體效能的各種制度安排,更傳統投票形式的參與水平也會提高。
集體效能給作為一種身份或者地位的代表理念製造了壓力。集體效能不把選舉看作是一次從選民到代表的權力傳遞,而是把在選民中間、在動員起來的選民與其代表之間形成一種負責關係的過程,視為代表成功的關鍵,視為社區有效實現共同目標的核心。代表及其選民互相影響;在代表過程中開始理解各自的利益。而且,為了在選民中間實現集體效能,代表把自己視為選民共同體一員,而不是一個外來權貴。

根據慣例,公民在選舉競技場上的角色非常消極,集體效能提供了一個與西蒙類似的替代方案。它挑戰的是下述觀念:代表最好通過接受一種固定身份為選區服務,比如受託人、代表或者反射式代表。在集體效能職責刺激下,代表與其選民建立了協作而非獨占關係。為了讓這一關係具有某種特徵,代表謀求設立制度化論壇,讓選民有辦法去發展和交流其集體智慧和集體力量。代表推動創造一個以議程而非候選人為中心的選區,其中代表與其選民的利益都在協商式爭鬥中逐步發展。
群眾大會是蒙哥馬利罷乘公車運動的支柱,舉足輕重,除此之外,我還可列舉三個例證,即巴西的社區劇場、帕圖阿雷格里港的參與式預算、以及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有關選舉體制改革的公民會議。通過這些故事,我試圖展現集體效能不僅僅是替代空間中的草根參與,也不單單是為參與而參與。在四個例證中,公民動員都影響了國家或地方政策。在四個例證中,公民及其代表共同提出公共政策目標。代表本身並不是民主。代表也無法獨立運作。相反,負責任的選民們改造了公民與其代表之間的關係,最終也改造了公民與其政府之間的關係。
一個民主問責的新標準就從這些集體效能的例證中浮現出來,這個新標準不單純依賴選舉。這個新標準的生命力來自下述三個假設:(1)民主結果應該體現集體智慧:普通人是重要的決策者,而不僅僅是個統計數據點;(2)參與過程增強了民主的正當性:人民更信任自己做出貢獻、付出心血的結果;(3)民主要回應的是基於公平的各式各樣的表達,而不僅僅是選票:參與不能被縮減成一個單一的選擇時刻。
這些假設都建立在更普遍的參與價值之上:參與讓公民有能力承擔風險、富於創造力、挑戰不公以及對公共辯論有所貢獻。這些假設也都是在回應讓我們的選主體制感染瘟疫的各種變量:公民不參與、不信任政客、不尊重政策結果。每個假設都值得我們大書特書。如果予以更加認真的研究,它們在總體上就能成為一種規範的代表敘事根基,這種敘事強調公民參與的下述潛能:產生更好的結果,更正當的過程,為民主問責提供基於公平的更牢固根基。然而,本文的目標沒有這麼遠大。我使用這些古今例證是為了證明:一個更多參與、更有活力、更注重交往的民主問責方式是可能的,至少在地方層面是可能的,它是對選舉的昇華而非取代。
結論
本文一方面考察了將選舉作為重心會產生什麼樣的窄化和扭曲效應,另一方面討論了個體之間的相互合作,以及他們與其代表的通力合作,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滿足他們的需要、實現社會變革。我質疑的是這樣的傳統智慧:修補民主主要就是修補選舉體系。選主理念是一個糟糕的民主觀,尤其是因為它將政治代表與其選民分離開來,將選民彼此分離開來。英國上議院議員常說,選舉不是萬靈藥。儘管他們這樣說有其自我辯護的緣由,但這個主張不是完全沒有道理。陌生權貴的統治,不論是選舉的、任命的還是靠爵位得來的,都是對民主的挑戰。

我已經論證,真正致力於民主的美國人應該考慮,如何才能在我們的公民同胞中間建構集體效能以回應這一挑戰。我想問的是:我們能否超越過時的代表觀念?我們能否超越實質上沒有活力的代表,能否超越作為固定代理人而非有活力夥伴的代表,能否超越以贏者通吃為基礎的選舉?這種選舉削弱而不是鼓勵全體選民根據自己的界定加入一個共同體,成為精力充沛的問責選民。這個問題最終是為了尋求闡明一個更大的道理:民主與自治相關,而不僅僅是代議。
(參考文獻略)
編輯/闐黎遠人
♦ 專文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