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內容轉載自 新視界電子報。若有侵害著作權,請速告知,我們將盡速移除 ♦
2023/5/15

馬克吐溫國際影像有限公司主辦《少了一個之後》系列講座,2020年1月19日假臺北里山咖啡邀請曾建元主講〈曾群芳與1947年的臺北青年〉
如果,要以一句話來縱貫1928年出生的曾群芳一生,這個接受日本教育、在二戰後經過國民黨接收的年代,受到時代巨浪的影響,憑著熱情與正義感,參加地下黨而後終生受影響的故事,他會說自己「歹命好運」!歹命的是出生在這樣的時代上,對民主、對正義的理想追求全為枉然;好運的則是,靠著家族與友人的幫忙,讓他與死神擦肩而過,不過也從此緘默,縱使在子女的研究追查下,仍不願多提。而和他一同在1947年正青春的青年們,又是在什麼樣的社會情境下,會前仆後繼地參加在今日看來「萬惡」的共產黨呢?讓我們藉由曾群芳的人生故事來告訴你。

▌一夜改變的「戰敗國」與「戰勝國」
「喂!曾我信重!」渡邊萬年叫喊一聲,隨即匆匆走近,一巴掌落在曾我的臉上。「這是告訴你,下次記得要向學長問好!」
曾群芳當下的反應是立即回敬對方一掌,並止不住怒氣說:「你在說什麼啊!之前在竹中的時候,你的確是我學長,但我們現在已經是同學!」,他生氣得似乎可以感受到自己在顫抖!
「學長是稱謂!不服氣的話,等下到軍械室前面空地見真章!你可不要怕了不敢來!」
不得已被逼著到軍械室前面空地的曾群芳,看著渡邊萬年一行人一共八人,為了先發制人,他趁對方還沒準備好,選了其中塊頭最大的同學,狠踢猛揍!其他人紛紛看傻眼似的,一時間不敢上前助陣,直到大塊頭哀叫求饒,才結束這一回合!沒想到那天夜裡,渡邊萬年又在夜間潛至曾群芳住的營房,被曾群芳發現大叫:「做什麼!」,曾群芳身邊的臺灣同學發現是日本同學偷襲,紛紛爬起出手動腳,一吐平日被日本人欺負的怨氣,渡邊萬年最後倉皇而逃。──類似這樣的求學經驗,是許多人在日治時期求學經驗的一環。
1945年8月15日,已經是經專本科生的曾群芳,以學徒兵身分正被日本皇軍徵調去現在的汐止山中挖防空洞,隔了幾天才知道戰爭已經結束。臺灣人從戰敗國民,變成戰勝國民,那一年的10月25日將會有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代表聯合國來接收,然而距離國民政府接收這將近兩個月的空窗期,除了一些零星的衝突,像是先前受到日本人欺壓的報復,基本上並沒有太大的鬥毆事件。整體社會相當自制,學生甚至自願組成治安維持隊,跟警察配合維持社會秩序。
青年學生們也組織讀書會,讀《三民主義》,公開地研讀與討論。曾群芳並將之前日治時期在學校學的共產主義政治經濟學及其相關東西,跟著放到讀書會裡面來研究,然而要說他們這些學生對於三民主義懂到甚麼程度,只能說當時知道得很朦朧,不過因為他們有一種期待臺灣人出頭天的心態,日本殖民者垮臺了、戰敗了,臺灣人便有了機會自己當主人,而這個中國,是戰勝國和世界五強之一!臺灣人可以分享中國人的光榮感,當時他們都認同臺灣人就是中國人,要和中國人共同建立新國家。
正值17歲青年曾群芳,還滿腔熱血地跑去基隆參加國民革命軍第70軍陳孔達部登陸接收,然而未久,當時臺灣省行政長官的陳儀公布兩道命令,像是瞬間澆了青年學生一大桶冷水:一是11月17日公布的《人民團體組織臨時辦法》,規定所有的社會團體要重新登記,經核准才可設立,就連之前熱烈歡迎國民政府來臺的臺灣學生聯盟都被迫解散;再來則是依《臺灣接管計畫綱要》於年底公告的《民國三十五年度工作要領》,下令所有公文書自此禁用日文書寫,各級學校以中文授課。但當時這群受日本教育的學生幾乎都不會中文,且在那年代能升學幾乎都是日本國語家庭出身,怎會講中文、又或講得好?臺灣社會和校園的巨大變化,還有戰後臺灣物資大多被送往中國戰場,物價飛漲,日本學生被遣返,臺灣學生無心上課,造成「當時學校裡的野鳥好像比學生還多」,生活的困難,讓曾群芳這個未滿20歲的少年曾餓著肚子從臺北搭車回到中港,再帶米回學校⋯⋯
▌掀起巨浪的「二二八事件」
1947年2月27日傍晚,臺灣省菸酒專賣局查緝員葉得根以槍托毆傷私菸販林江邁,接著查緝員傅學通為擺脫群眾開槍示警,又在永樂町迪化街誤傷民眾陳文溪。翌日,歸綏市場的流氓林秉足、周達鵬等為替好友陳戊己三叔陳文溪出氣,招集群眾從大稻埕出發示威,許多學生風聞而至,陳炳基找來表弟巫金聲,開著卡車上載大鼓,也一同上街。
2月28日當天的遊行曾群芳並不知情,和一同打麻將整天的同學晚上要回學校時,遇上軍人於街頭叫他們站著,卻因為語言隔閡被軍人突然開槍示警並被上膛的槍對著,情急之下,曾群芳突然拉著同學往持槍軍人方向衝去,軍人被突如其來的舉動驚嚇,才結束這場對峙,但曾群芳的心中十分不滿,認為軍人行為魯莽,極易誤傷人命。在知道臺灣各地都有騷亂後,曾群芳的心中更是憤怒,像是這兩年累積的怒氣一次被點燃。
3月3日,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臺北市工作委員會書記廖瑞發有意發動武裝起義,次日,約集臺北各大專院校學生自治會和臺灣學生聯盟領袖商議作戰計畫,共同決定組織學生軍。學生軍成立後,鄭文峰找曾群芳一起加入,目標就是要去打開軍火庫,兩人相約一起前往建國中學,就在曾群芳要出門的時候,哥哥曾培芳由於局勢混亂,就拿了一把槍給他防身,裡面有兩顆子彈,是一位在他家避難的廈門籍警察繳械給的,而曾群芳到了集合現場的時候才發現,這把槍是所有人帶來的武器中最精良的,其他同學有的帶竹竿、有的帶鐮刀、菜刀等等,甚至有人兩手空空還是跑來,即使沒有武器也完全不減他們激動高昂的情緒,戰鬥意志非常堅定。
但在武器這麼短少的情況下,為什麼覺得自己可以贏過「打了八年抗戰的國軍」?
正因為曾群芳曾經到基隆港歡迎第70軍上岸,親眼看見國民政府的軍隊如乞丐兵一般,物資匱乏的慘況。反觀在日治時期受過學徒兵訓練的曾群芳,不僅會使用機關槍,也因為日本教育尚武,學校中都有設立武德殿,從小就訓練每個學生劍道、柔道等,所以當他一看到國軍的樣子,就覺得中國兵很遜,如果單挑一對一,打敗中國兵絕對沒問題,也不僅僅曾群芳如此覺得,當時許多的學生們都認為:「只要搶到軍火武器,他們一定能打敗國軍!」這就是他們當時的想法。
▌清鄉與逃難
1947年3月8日國軍整編第21師劉雨卿部自基隆登陸後,開始了清鄉,曾培芳看情形不對,就叫才剛上小學的女兒曾惠美陪著曾群芳搭火車回竹南中港避風頭。事平之後,當年6月的某一天,鄭文峰帶曾群芳去臺大法學院附近的咖啡店,裡面烏壓壓擠滿了包括臺大法學院同學在內的學生,陳炳基開門出來招呼,他們正在宣誓參加共產黨。陳炳基已參加了,鄭文峰也參加,最後曾群芳也參加。
「四六事件」後,當月的地下黨機關報《光明報》刊登了「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做好準備,迎接臺灣解放!」等標語以及三大戰役勝利的消息,臺灣全省各地都出現了《光明報》和大大小小的革命標語。據說7月中連臺灣省政府主席陳誠家裡信箱都被塞了《光明報》,陳誠震驚不已,立刻向國民黨總裁蔣中正報告,立即在8月於草山(今陽明山)召開緊急會議,清查《光明報》來源,誓言剷除地下黨組織。
1950年《臺灣工委會學委會李水井案》(簡稱學委案)遭國防部保密局所破獲,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領導人蔡孝乾、張志忠、洪幼樵等人被捕後,經過嚴刑逼供,政府依其口供於5月展開臺灣全省的大逮捕,幸好曾群芳友人陳廷裕從臺北趕到花蓮通風報信,曾群芳下班後回到宿舍聽到訊息,不僅西裝沒換,連宿舍燈也沒關,東西拿了就騎著腳踏車起身逃亡。過程中為了怕收容者起疑或畏懼,絲毫不敢透露任何與政治相關的原因,一律自稱是因感情糾紛必須借住一陣子,也因為害怕增加曾經幫助過他的人的麻煩,至逝世前未向當年藏匿他的恩人致謝,這成為他一生中心中最大的陰影⋯⋯
▌共產黨的理想主義
為什麼要參加共產黨?共產黨當時的論述真的鼓動當時的青年人。加上那一代學生對國民黨在臺灣的統治,以及二二八後全島的鎮壓、屠殺,深惡痛絕,厭惡「再殖民」的經驗,許多人紛紛轉向共產黨。當時大部份的學生想法偏向「大中國意識」,當然也有少部分學生受到廖文毅的影響,有「臺灣地位未定論」與「託管論」等多元思考的存在。
對那一代的臺灣青年來說,他們反對國民黨再殖民,至於說臺灣的下一個出口在哪裡,他們還在摸索當中,可是就眼前可以看到的,曾經打敗國民黨的就是共產黨,便把臺灣再解放的希望寄託在共產黨,也前仆後繼相邀入黨。雖然這些臺灣人的入黨程序大都不合格,但心志的確是向著共產黨的。像是當時曾群芳參加了《光明報》編寫和油印工作,想辦法用各種方式把解放軍的狀況散播出去,讓臺灣人知道解放軍何時可以解放臺灣。所以像他在臺糖工作時期,他心心念念的就是要把臺糖的糖廠維護好,一旦解放戰爭爆發,不要破壞到糖廠等公共建設,以便臺灣在戰後可以在最短時間內復原,這是他們重要的任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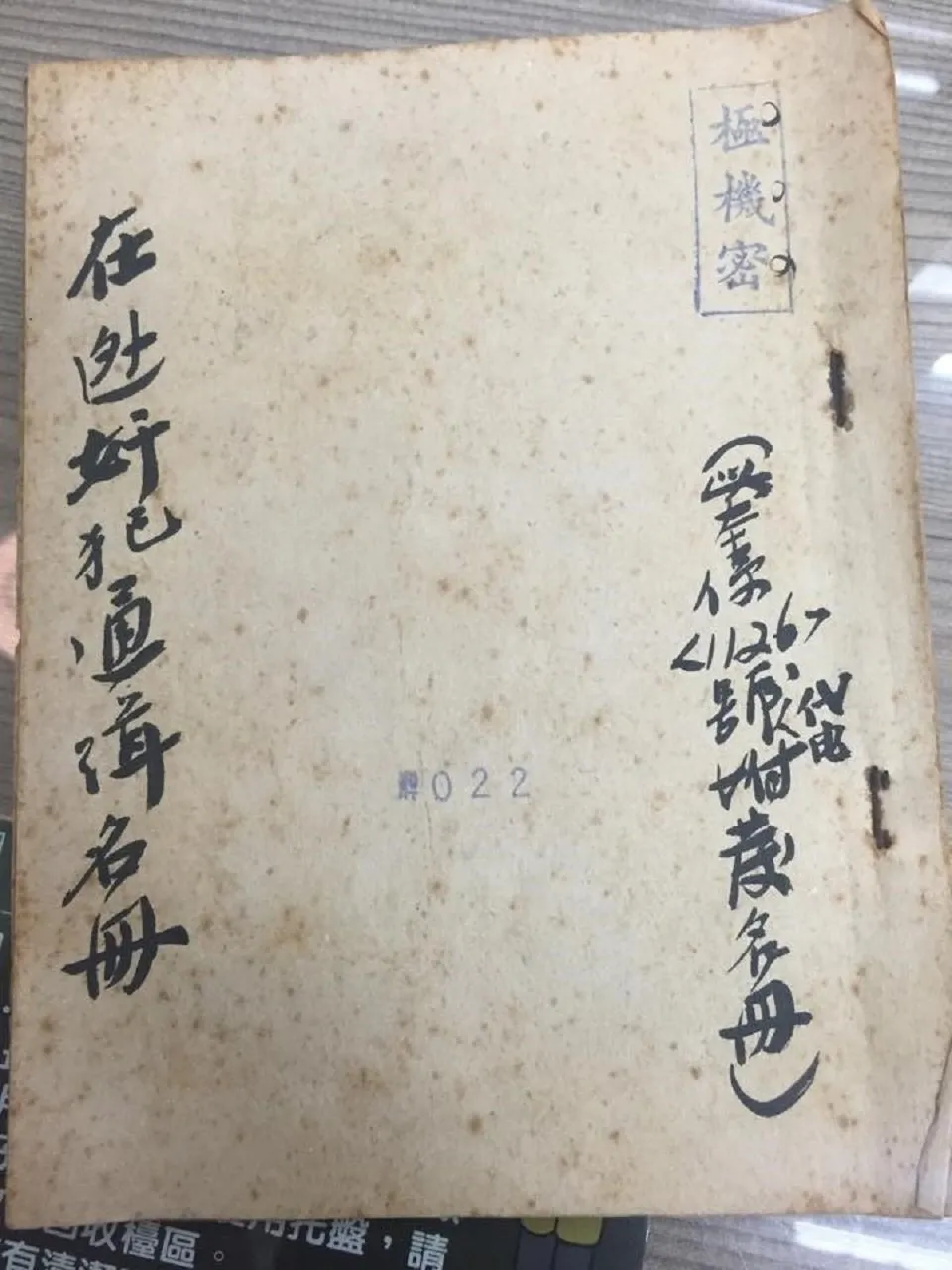
▌《學委案》後的兩次自新:
1951年9月17日,由蔣經國擔任主任的國防部總政治部宣布補正《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辦法》及《檢舉匪諜獎勵辦法》,限地下黨人於11月20日前自首,當時擔任臺灣省政府委員兼農林廳廳長徐慶鐘秘書的曾培芳,找到國防部保密局軍職轉任之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科長章和樂,勸藏匿在番婆坑山區的曾群芳向保密局投案。這是他第一次落網。他從山裡走出來時,頭髮和鬍子都長到及胸,狼狽不堪。他被羈押在青島東路3號臺灣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即現在的臺北喜來登飯店位置,大概被關了兩個禮拜的時間,被帶到林頂立家裡寫自白書,總共被要求修改了三次才定稿,乃得以自新,逃過死劫。
後來到了1952年4月,地下黨在苗栗縣三義鄉魚藤坪的最後根據地被破獲殆盡。1953年8月,曾群芳的友人同為地下黨黨員的翁木因媒說合,將與劉菊妹新婚,擔心組織關係會影響婚後妻室生活,誤信政府號召,於1954年7月,在憲兵司令部策動下請了苗栗縣前副議長王天賜陪同自首,把他的組織關係向有關單位合盤托出,曾群芳再度落網。
由於第一次被捕時,曾群芳並沒有供出竹南支部的組織關係,故遭以涉嫌「自首不誠」的罪名,由保安司令部接手查處。第二次落難,靠的也是曾培芳的奔走,透過各級長官的協助及作保,最後曾群芳以情節輕微不起訴而免去其後的牢獄之災,但直到臺灣解除戒嚴都有警察監看。
▌「歹命好運」的背後
雖然曾群芳逃過一死,然而不是每個當時的革命青年都是如此幸運,他生平需要眼睜睜看著友人們受盡苦難,甚至沒有機會活下來,心中煎熬無以比擬。他的友人翁木因良心不安和驚嚇過度而發瘋,曾群芳在1990年代曾到苗栗縣頭份鎮永和山為恭紀念醫院東興院區精神醫療中心去探望翁木,翁木望著好友們說:「曾群芳是我的好朋友,他沒那麼老。」說罷臉上流露出驚恐的表情,然後轉身逃開。
嚴格來說,曾群芳、陳廷裕和顏松樹應都屬於《學委案》,然而關於自首和判刑的標準這件事,其實都因人而異。依據當時的法律條文,自首可以減刑或免責,甚至辦理自新可以除罪免刑,但是從國民黨政府的相關判決來看,似乎沒有太明確一致的量刑標準,像曾群芳是因為曾培芳跟國民黨高官有互動,牽得上一些關係,再送點錢,所以雖然「自首不誠」,不過後果不算嚴重,但他人就沒有如此幸運了。
正如曾群芳另一個好友鄭文峰原判無期徒刑,遭蔣介石大筆一揮改判死刑。才氣縱橫、熱情奔放的他經常到曾群芳宿舍淡水寮,與其一起並肩走路上學,各抒己志。當年也是他拉著曾群芳參與二二八起義和入黨。後來鄭文峰回到嘉義發展組織,1950年6月全省大逮捕時在朴子家中被捕。他曾痛斥國民黨政府的偵訊軍官對於馬克思主義認識的淺薄,說:「你們不懂,我可以教你們」。又有誰能料到,他們那一代青年曾共同期待的共產黨,在建國後對人權的泯滅,讓世人都失望了!
曾群芳生平經歷兩次牢獄之災,也是當時代青年們的一個縮影,雖然他因為當時家族內有人援救而逃過大災;甚至也得到貴人相助,獲得當時充滿左派精神的大企業老闆林挺生賞識,後續生活無虞。但是青年時代的風風雨雨,那些他曾經一起信仰與追求的夥伴,並不是每個人都那麼幸運得以存留下來!
禁止小孩碰觸政治,是那一代臺灣青年,對於自身晚輩親屬的最大告誡!嚴格恪守不評論、不參與,是那一代人們走過凜冽寒冬後,最卑微的保身之道。而關於那曾經躍躍然,對於家國的改革希望與理想,就化為生活吧!如今臺灣已不再是當年的臺灣,《少了一個之後》團隊期盼的是讓更多臺灣人理解,現在我們所擁有的是民主的憲政體制、多元的黨派、自由的話語權,這一切並不是理所當然。或許臺灣距離完善社會還有一段路要走,但回首過去那個連言論自由都是種奢侈的時代,我們也已經跌跌撞撞地前進了一大段。也希望能夠與群眾一起,對於臺灣歷史脈絡有著多一份的關心,與感念得之不易的這一切!
整理報導:余明珠(馬克吐溫國際影像有限公司專案經理)
♦ 專文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