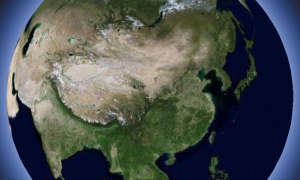♦ 本篇文章轉載自 文化縱橫。若有侵害著作權,請速告知,我們將盡速移除 ♦
2023/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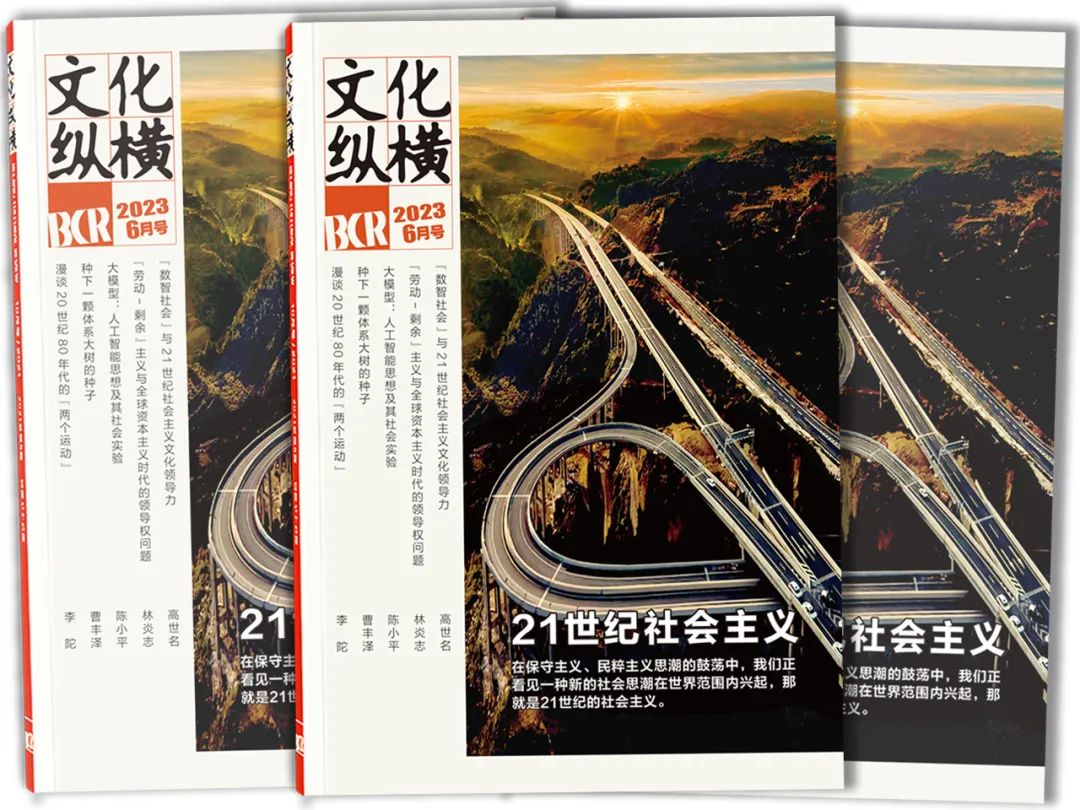
✪李磊|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導讀】近期,一場“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在北京舉行,領導人着重強調的“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引發各方關注。其中,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尤其突出。“如果不從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性來認識中國,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國,也不可能理解現代中國,更不可能理解未來中國。”那麼,如何理解中國的歷史連續性?
事實上,“中國歷史連續性”是學界長期關注的重要議題。但以往討論多從文化層面切入,歸之於中國文化傳統尤其是儒家正統思想的塑造,失之虛玄。本文作者李磊從制度層面指出,傳統體制的容納性,即體制容量,對於中國歷史的連續性有着決定性意義。傳統中國的體制容量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方面,它是在各個地方、各個族羣、多種經濟形態之上的具有統攝性的體制,能夠有效協調中央與地方關係,完成對社會勢力吸納、財稅徵納與社會事務的管理,保證政治決策理性和行政執行效率,設立儀式、禮制以塑造認同等。因此無論是漢族,還是遊牧族羣,無論是建立地區性政權,還是建立大一統王朝,均沿襲這一體制,僅做因時制宜的增減。作爲制度載體的政權或王朝會有興亡,但體制本身卻處於發展延續中。另一方面,它還包含與具有鄰接性的陸疆地區及非鄰接性的海外地區之關係的處理機制,通過提供交往條件,建立公共秩序,將各方的彼此依賴,轉化爲共同體意義上的體制性依存。這在今天,仍然是值得重視的制度遺產。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3年第1期,原題爲《傳統中國的體制容量與中國歷史連續性》。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供諸君參考。
▍宜農宜牧區與傳統中國的體制延續
自戰國秦漢農牧分界線形成以後,遊牧族羣與農耕社會的關係歷來是傳統中國政治的主軸。呂思勉先生曾對遊牧族羣的歷史作用做出過精當的論述:
先漢雖威加四夷,然夷狄入居中國者絕鮮,後漢則南單于、烏丸、鮮卑、氐、羌,紛紛入居塞內或附塞之地,卒成五胡亂華之禍。而唐代亦然,沙陀入居中原,猶晉世之胡、羯也。蕃、渾、党項,紛紜西北,卒自立爲西夏,猶晉世之氐、羌也。而契丹雄踞東北,與北宋相始終,亦與晉、南北朝之拓跋魏極相似,一矣。
關於遊牧族羣政權採用傳統中國體制的緣由,上述呂思勉先生的論述提供了地理方面的解釋線索。遊牧族羣建立政權主要在山西、西北與東北這三大地理板塊,處於司馬遷所繪農牧分界線與長城邊塞之間。按《史記·貨殖列傳》所述,“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龍門-碣石”一線是戰國秦漢的農牧經濟交界線,但非農牧族羣的分界線。秦始皇三十二年,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匈奴,略取河南地,農牧族羣的分界線北移至陰山。此後,西漢與匈奴圍繞着河套地區、河西走廊的控制權進行了反覆爭奪,農牧族羣分界線大抵被穩定在長城邊塞。隨着農耕人羣大規模移民“龍門-碣石”一線至長城邊塞的地區,該地區由遊牧畜牧經濟區轉變爲農牧混合經濟區。呂思勉先生所述遊牧族羣建政的地區,正位於這片宜農宜牧區。
農業經濟、農耕人羣在宜農宜牧區所佔的比重,以及秦漢王朝在這一地區長達四百多年的治理實踐,決定了佔據這一地區的遊牧族羣政權選擇沿襲秦漢舊制,這是在衡量治理成本與政治收益後得出的優化方案。就山西板塊(河東地區)而言,十六國時期匈奴人建立的漢國是第一個稱帝的遊牧族羣政權。儘管漢國採用了胡漢分治、胡胡分治的統治方式,但在政治體制上卻採納了官僚君主制、郡縣制、編戶齊民制等傳統體制,且在法統上以漢朝宗室自居,以“漢”爲國號,在宗廟中祭祀西漢的漢高祖、東漢的光武帝以及蜀漢後主,並尊後主劉禪爲孝懷皇帝。漢國體制爲後繼者前趙與旁出者後趙所繼承,成爲十六國的制度傳統。此後,北魏以山西地區爲核心統治區,東魏北齊與西魏北周的戰爭也圍繞着爭奪河東的統治權而展開。唐末沙陀勢力也崛起於此。與十六國時期漢國的策略相同,晉王李克用在朱溫建樑後仍然尊奉唐昭宗年號。李存勖繼立後,結束了延綿百餘年的河北三鎮跋扈之局,即皇帝位,沿用大唐國號,攻滅後梁。從法統來看,後唐否定後梁,接續唐朝,開啓後晉、後漢、後周、北宋的傳承脈絡,在唐宋之際起着承前啓後的重要作用。可以說,建政于山西地區的遊牧政權對於漢宋之間的正統性傳承關聯極大。
自張騫通西域、漢武帝設河西四郡之後,西北族羣在中國歷史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除了農耕人羣自東向西遷徙以外,羌人、氐人等宜農宜牧人羣自西向東遷徙。至西晉時,關中人口半數爲氐、羌。蒙古高原的遊牧族羣,如匈奴、鮮卑,也進入河西地區、河湟谷地、隴西及涇水上游的嶺北地區。十六國時期的西北族羣仍採用官僚君主制、郡縣制來建構政權,這是由該地區的多族羣分佈格局決定的,漢魏晉體制爲多族羣政治體提供了制度樣板。唐朝時,吐蕃雖崛起於青藏高原,但其發展態勢爲出河湟、分進河西、關隴,是影響唐朝國策的重要地緣環境。陳寅恪先生說:“李唐承襲宇文泰‘關中本位政策’,全國重心本在西北一隅,而吐蕃盛強延及二百年之久。故當唐代中國極盛之時,已不能不於東北方面採維持現狀之消極政略,而竭全國之武力財力積極進取,以開拓西方邊境,統治中央亞細亞,藉保關隴之安全爲國策也。”中唐以後,吐蕃直接統治河西地區。“迨吐蕃衰敗之後,其役屬之党項別部復興起焉。此党項後裔西夏又爲中國邊患,與北宋相始終。”
與西北相比,東北的自然環境更加有利於農業,農業潛力巨大。儘管碣石至漢長城的距離很近,但這片區域中的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玄菟、樂浪諸郡,卻成爲東北族羣轉進塞內的樞紐。他們在這裡熟悉農耕人羣與農業社會,在政治組織上完成向官僚君主制及郡縣制的轉化。西晉瓦解後,佔據這片區域的宇文氏、段氏、慕容氏均以郡縣制爲基本統治架構。更爲重要的是,漢長城以北更廣大的區域,即今日中國東北三省及內蒙古東北地區,受到農耕文明的影響,也漸次演化爲漁獵、遊牧、農耕的混合經濟形態。較之於其他地區,崛起於塞外東北地區的政權大多有王朝化的歷程。呂思勉先生將遼、金、元、清的興起視作中國文明的發展壯大。他說:
黠戛斯雖滅回紇,而未能移居其地,西方東略之力,至斯而頓,而東方之遼、金、元、清繼起焉。遼之起,由其久居塞上,漸染中國之文明,金、元、清則中國之文明,先東北行而啓發句麗,更折西北行以啓發渤海,然後下啓金源,伏流再發爲滿洲,餘波又衍及蒙古者也。其波瀾亦可謂壯闊矣。
源起東北的政權之所以能建立王朝體制,與其混合經濟形態有關。尤其是農業化,不僅成爲東北政權向王朝轉化的重要經濟基礎,而且隨着東北王朝入主中原,爲中國的多民族統一國家提供了一塊非常重要的農耕區。
▍傳統中國體制與遊牧族羣傳統的兼容
遊牧世界的政治邏輯與中原王朝的體制模板並非不相兼容。當遊牧族羣在宜農宜牧區建立政權時,中原王朝的體制爲其最優選擇。儘管山西、西北、東北族羣的發展歷程有所區別,但在體制選擇上卻大體如一。尤其是東北族羣,獲得了優於其他區域的農業地利,當其社會內部農業地區的權重增加到一定程度時,政權將向王朝轉化,幾乎是必由之路。值得注意的是,遊牧族羣選擇中原傳統體制並非無條件,前提是體制須兼容本族傳統。可以說,傳統體制的容納性即體制容量,是影響遊牧族羣是否選擇中原傳統體制的關鍵性因素。
自戰國秦漢以來,中原地區所形成的體制具有以下內容:協調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機制(郡縣制、分封制、羈縻制),國家吸納社會精英的機制(世襲制、選舉制),政治決策機制(內朝制、御前會議制),行政機構組織機制(三公九卿制、三省六部制)、監察機制(臺諫制),政治儀式(禮制),財稅徵納與社會治理機制(賦役制、編戶齊民制),軍事動員機制(兵役制、募兵制),立法及司法體制(律令制)等。這一體制雖以農業社會爲成長背景,但致力於解決的問題卻是各種社會組織所共同面對的。故而遊牧族羣的諸多社會傳統仍然能夠借助這一體制得以存續。下面依據遊牧族羣建政的幾種類型,分述中原體制與其政治傳統的兼容方式。
一、官僚君主制與遊牧族羣傳統的兼容情況。匈奴是遊牧族羣最爲重要的法統源頭,但在十六國時期,匈奴建政不再採用本族政治架構,轉而實行官僚君主制。匈奴漢國在遊牧族羣政權中是最早稱皇帝的。儘管如此,匈奴舊有的政治傳統仍在新體制中得以留存。如匈奴最高政治名號單于,漢國君主稱帝后並未廢除這一名號,而將之轉授予太子或皇子。這樣既保留了匈奴的政治傳統,但又將其置於官僚君主制中,成爲皇帝之下的一個官僚等級。再如匈奴的“四角”“六角”王制,漢國代之以封爵制,將匈奴諸王轉化郡縣王。在不損害其政治聲望的同時,將分封制下握有實權的匈奴貴族改造爲中央集權制度下領取封邑租稅的寄生貴族。匈奴的部落制也被漢國改爲編戶制。漢國設置司隸、內史管轄匈奴民戶。各內史在名義上隸屬於郡縣王,但在實際上聽命於朝廷。通過司隸、內史,漢國朝廷統一徵發兵役,完成對匈奴兵制的改革。從漢國的政治實踐可知,匈奴的政治傳統並未斷絕,它以與官僚君主制融合的方式發揮着組織協調作用。
二、門閥體制與宗王出鎮制的兼容情況。西北地區的羌、氐、巴爲宜農宜牧族羣。王莽以來羌人移居塞內,東漢時期羌、氐移居關中、益州。鄂西重慶的巴人在漢末北上漢中,曹操遷之略陽,與氐人雜處,合稱巴氐。魏、晉王朝進一步強制遷徙羌、氐入關中。可以說,漢晉之間的羌、氐、巴經歷了漫長的遷徙過程,其部族組織時常被打散重構。十六國時期分別建立前秦與後秦的枋頭集團與灄頭集團,雖然領導者一爲氐人苻氏,一爲羌人姚氏,但其集團成員卻均是氐、羌、漢等多族羣身份,形成了從下而上在盟主家族成員中推選領袖的政治傳統。前秦、後秦建立後,採用魏晉門閥體制與宗王出鎮制度,正是與其政治傳統相互配合。在門閥體制下,苻氏、姚氏以第一家族的身份凌駕於其他家族之上,家族成員以出鎮的方式分享統治權。異姓家族子弟則以出任幕府掾屬、參預軍鎮決策的方式分享地方軍政權力。苻氏、姚氏家族成員的平等性借門閥體制與宗王出鎮製得以保留,枋頭集團、灄頭集團中苻氏、姚氏與異姓家族的等級差別也經由這一體制而得以延續。
三、州郡政區及方國體制的兼容情況。河西、隴西的族羣構成較之關中更爲複雜。淝水之戰後,這一地區出現了鮮卑乞伏氏建立的西秦(都苑川),氐人呂光建立的後涼(都姑臧),鮮卑禿髮氏建立的南涼(都廉川),盧水胡匈奴沮渠氏建立的北涼(都張掖),漢人李暠建立的西涼(都敦煌)。這些政權建立時,所使用的大都是地方名號。如呂光先稱涼州牧、酒泉公,再稱三河王,最後才即天王位。乞伏國仁先稱領秦河二州牧,後被苻登署爲苑川王、金城王、河南王、樑王,最後自稱秦王。苑川、金城先後爲乞伏氏王廷所在地,河南指黃河以南的隴右之地。河西鮮卑禿髮氏先接受呂光廣武縣侯、廣武郡公之封,之後又先後自稱西平王、武威王、河西王、涼王。西平、武威爲郡名,河西爲地域名,涼爲州名。沮渠蒙遜建立政權後,自稱涼州牧、張掖公,此後後秦拜之爲沙州牧、西海公,再自稱河西王。這些政權的共同點是以郡、州地方官府爲最初的統治架構,再發展爲地域性的方國。可見地域意識而非族羣意識,是河西、隴西地區政權建構的主要政治資源,這是由該地區多族羣雜居的情況所決定的。地域意識其實是當地各個族羣意識的共同表達,在這個意義上,沿用地方官府及方國體制,仍是順應當地的民情。
四、部曲制、吏兵配屬制的兼容情況。永嘉之亂後,不少漢人流落至慕容鮮卑統治區,慕容氏以設置僑郡的方式安置流民。投靠慕容氏的漢人士族是以宗族、賓客、鄉黨爲流民組織,在遊牧族羣眼中就如同一個部落。形式上雖爲郡縣,實質上是被視作編排漢人的諸部。也正是基於屬人原則,慕容氏將其部落傳統與魏晉部曲制、吏兵配屬制兼容到一起。部曲指魏晉時期門閥士族、豪強地主的依附人口,他們平時耕作,戰時充當私兵。魏晉王朝模仿社會層面的部曲制,在州郡編戶齊民制之外,另設吏戶與兵戶,以之作爲朝廷及官府的私屬。無論是部曲制,還是吏兵配屬制的屬民形式,皆與慕容氏的部落傳統相通。前燕建立後,將之融合為營戶制度,部落制下的遊牧族羣被賦予軍籍,隸屬於軍營,從事生產與戰鬥。部分州郡民戶被劃為軍營蔭戶,爲軍營提供租賦。前者源自部落制,後者源自部曲制、吏兵配屬制。營戶制度成爲前燕的重要軍政制度,不僅能夠將先期進入華北的烏桓、丁零、匈奴、羯、鮮卑諸族納入其中,而且由於這一制度與門閥統治精神相通,因而得到河北士族的支持。雙方的合作是前燕、後燕、南燕的統治基礎。
五、賦役制、編戶齊民制的兼容情況。淝水之戰後,拓跋氏建立的北魏迅速崛起。北魏統一華北的過程,也是摧毀原有社會組織,按編戶齊民制的精神重塑政權基礎的過程。北魏對所征服的遊牧族羣採取離散其部落的政策,或強制遷徙,編制爲軍戶;或遷於平城周圍,計口授田,徵收賦役。孝文帝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便是頒行三長制、均田制、租調製。三長制旨在重建鄉官系統,目標在於取代宗主都護制,將門閥、豪強的蔭戶重新納入國家戶籍管理之下,以之作爲均田制、租調製的施行前提。均田制、租調製以一夫一婦爲單位分配土地、規定賦役,這些制度一方面根基於商鞅變法以來中原王朝的制度傳統,一方面又具有明顯的村社分配土地色彩,是拓跋氏社會公社傳統的體現。可以說,北魏以均田制爲國制根本,正是將其部族傳統融入中原傳統體制的結果。
儘管遊牧族羣與農耕人羣有着不同的經濟形態、社會組織與政治傳統,但十六國北朝的歷史實踐表明,戰國秦漢以來形成的中原王朝制度可以容納多族羣、廣地域,遊牧族羣的傳統也能爲這一體制所容納。遼朝建立以後,北方遊牧族羣的政治傳統出現了很大的斷裂,蒙古高原上自匈奴、鮮卑、柔然、突厥、回鶻以來的政治傳統,雖然參與了遼朝國制的建構,但僅爲其政治資源之一。相較而言,中原王朝體制發揮了遠超前代的作用。遼、金、元、清藉以發展為王朝體制,並在中國的王朝譜系中取得了正統的位置。可以說,傳統中國的體制容量對於中國歷史的連續性有着決定性意義。
▍對鄰接性及非鄰接性地區的體制容納
傳統體制還包含與具有鄰接性的陸疆地區及非鄰接性的海外地區之關係的處理機制。最新的研究觀點認爲:“古代中國具有貫穿內、外的普遍政治秩序,即在承認地方差序格局的基礎上,以集體主義爲導向建構共同的政治體、經濟體,並通過禮儀等文化層面的舉措強化共同的身份意識。這一政治秩序的適用空間在理論上具有無限性,不拒絕治外政權及族羣的參與。地方對共同體的體制性依賴源於中國國家體制提供了中央與地方、地方與地方、治內與治外的交往條件與公共秩序,並降低了交際成本。”傳統體制對鄰接性及非鄰接性地區關係問題的處理,正是遵循了這一原則,通過提供交往條件,建立公共秩序,將各方的彼此依賴轉化爲共同體意義上的體制性依存。
根據《史記》《漢書》記載,張騫通西域後,西域諸國使者朝貢漢朝,常常是隨漢朝使者同來,且沿途受到漢朝機構的照顧。朝鮮半島及日本列島的遣使朝貢由邊郡負責,位於朝鮮半島上的樂浪、帶方郡,既代表朝廷接受各族的朝謁,也負有將求詣天子的朝獻使者送至京都的職責。接待並護佑使者的制度爲商賈所利用,以降低其商貿成本。漢成帝時杜欽分析西域罽賓遣使的情況,說:“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爲名。”罽賓使者實爲商賈,他們之所以樂意向漢朝朝貢,實是因爲漢朝的“遣使送客”制度爲其承擔了交通運輸成本並保證其人貨安全。
儘管爲治內與治外的交流提供交往條件給王朝財政帶來負擔,卻也爲不同區域、不同經濟形態的族羣搭建了交流平臺,建立了公共秩序,這對於缺乏鐵器、布帛、糧食、手工業品生產能力的遊牧族羣尤其重要。北方遊牧社會需要從農耕區獲得必需的生活資料與生產資料。在交往不暢的情況下,遊牧族羣會以劫掠農業地區的方式獲得物資,或者以佔領宜農宜牧區來強迫中原王朝歲貢、開榷場。爲多邊交往提供條件,建立起協商機制,其實是成本最小的辦法,而且無論對於哪一方,都是最有利的選擇。正因如此,魏晉以後的歷朝歷代基本上都沿襲了漢朝的處理方式。在這一體制下,邊塞諸鎮在大部分時間裏所承擔的是通關往來的管理工作。由此一來,傳統國家體制以農業地區爲基本面,依託牧業地區對農業地區的經濟依賴與社會依賴,建立起涵蓋農牧關係的治理體系。
唐宋以後,中國與海外的聯繫日趨密切,如何將這種缺乏地理鄰接性的關係納入既存體制成爲新的治理問題。明朝前期的思路是通過官方的航海活動,將海外的非鄰接地區與王朝連接在一起。永樂三年到宣德八年(1405~1433),鄭和率領水軍七下西洋,三四十個國家和地區得以與明朝建立官方聯繫。明朝艦隊相當於流動的長城邊鎮,對於非鄰接地區而言,明朝艦隊的到來,類似於邊境的季節性出現。艦隊到達時,非鄰接地區便與明朝進行領土連接。非鄰接地區通過明朝艦隊的“朝貢”“互市”,性質上與鄰接地區經由明朝邊鎮的“朝貢”“互市”類同。與陸地的情況一樣,朝貢的海外諸國國王及使者,由明朝負責護送至京師。鄭和艦隊正承擔着這樣的任務。
通過航海活動,明朝將非鄰接地區變爲鄰接地區,將原本處理鄰接地區的體制用於這些非鄰接地區。這是在既有體制之下,通過交通方式的變革來改變地理條件,充分利用體制容量來解決實踐中的問題。明朝的體制貢獻不在於制度變革,而在於在實踐領域中創造性運用體制,由此最大限度地降低制度成本,維持了體制的穩定性。這一方略的成功建立在傳統中國體制容量的基礎上,但需要付出較高的交通成本,這成爲官方大規模航海活動最爲人詬病之處。明朝中葉以後放棄成建制的大規模航海活動,意味着治理架構的大幅調整。不僅非鄰接地區的治理被放棄,鄭和下西洋所構建的海域治理權也被放棄,邊境線大幅退縮至近海。與此同時,西歐殖民者卻沿着鄭和下西洋的航線,逆向從西洋往東洋擴張,接收了明朝的治理遺產。處理與他們的關係,則成爲近現代中國的治理難題。
▍結論
關於傳統中國的國家體制,現代學術話語常以民族國家或帝國理論爲思維框架,力圖對其法權邊界進行清晰化的描述。在這一論域中,遊牧族羣所建政權常與漢族所建政權被區隔開來。如果置於歷史的實態來看,遊牧族羣所建政權分爲兩類,一類以宜農宜牧區爲核心統治區,另一類則以牧業地區爲主要統治區。前者與漢族所建政權的體制基本相同,實爲同一類型。後者雖有自身的政治邏輯,但也在傳統中國的體制中擁有自己的位置。
宜農宜牧區主要指“龍門—碣石”一線至長城邊塞之間的地區,它分爲山西和西北、東北三個板塊。由於農業經濟、農耕人羣在這片區域仍佔據相當比重,秦漢王朝在此也形成了長期的治理傳統,因而以宜農宜牧區爲核心區的遊牧族羣常常會以傳統中國的體制來建構政權。之所以如此,除了統治成本方面的因素外,體制功能是決定性因素。傳統體制是在各個地方、各個族羣、多種經濟形態之上的具有統攝性的體制,能夠有效協調中央與地方關係,完成對社會勢力的吸納、財稅的徵納與社會事務的管理,保證政治決策的理性、行政執行的效率,設立儀式、禮制以塑造認同等。正因如此,無論是漢族,還是遊牧族羣,無論是建立地區性政權,還是建立大一統王朝,均會沿襲這一體制,僅做因時制宜的增減。作爲制度載體的政權或王朝會有興亡,但體制本身卻處於發展延續中。
建政於牧區的遊牧族羣,從農耕區獲得生活資料與生產資料爲其剛性需求。傳統中國體制直面這一需求,爲相互交往提供條件、建立公共秩序,依託彼此間的經濟及社會依賴,建立起涵蓋農牧關係的治理體系。值得注意的是,傳統中國的農牧關係問題其實是具有鄰接性地區之間的體制融合問題。唐宋以後海上通道暢通,如何處理與海外這類非鄰接地區的關係成爲一個新的體制難題。明朝的貢獻在於通過官方的航海活動,讓艦隊充當流動的邊境線,由此改變海外地區的非鄰接性質,將其視作鄰接地區納入既有體制之中。這一治理思路並不是制度變革或新設制度,而是在傳統體制內,通過技術手段的創新(如“邊鎮的流動”),來挖掘體制存量。
明朝晚期時西方殖民者東來引發的海疆危機,並非緣於傳統體制的失效。恰恰相反,它是明朝放棄體制化治理的結果。明朝結束了大規模的航海活動,致使邊境線內縮至近海。充當邊鎮的明朝艦隊不再出現後,非鄰接地區便難以維繫與明朝的體制性關係。西方殖民者乘虛而入,將全球殖民體系擴張至中國東南沿海。無論明朝是以嚴守官方貿易的方式來管控海疆,還是通過以夷制夷的策略進行防衛,都只是策略層面的自衛,而缺乏整體性的體制構想,因而並不能真正解決問題。可以說,鴉片戰爭前兩百年,中國便陷入對西歐殖民者的反侵略鬥爭之中,但不能據此否定傳統體制的有效性。傳統中國的體制生命力,仍然是今天值得重視的制度遺產。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3年第1期,原題爲《傳統中國的體制容量與中國歷史連續性》。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




♦ 專文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