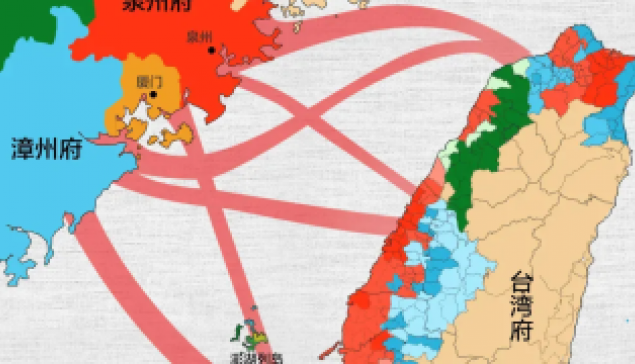王曉波與李登輝同一天辭世,雖然兩人在政治與社會影響力的規模上相差甚遠,但從本質上而言,兩人都有左派背景,惟在統獨主張上大有不同,而且色彩鮮明,不畏爭議。李參加過共產黨,王的母親據信是共產黨員在台灣遭槍決,那時曉波才九歲多。
我在台大四年當中,有三年住過不同學院宿舍,但大三時一起與同學在溫州街日本宿舍賃屋而居,有黃樹民、王中一、陳秋坤、何步正、楊濬哲與王曉波等人。有一天曉波說附近警察局要擺一桌,希望我們能去湊個熱鬧吃頓飯,原來是一位唸政治系的香港僑生甄燊港因頭髮太長,在路上被警察逮到局內,強制剪成平頭。王聞訊後大怒,一個人衝到警局找主管理論,沒想到警局竟然認輸還擺一桌消災。
又有一次我們看到他手綁繃帶,看起來災情慘重,原來是他在台大醫院看護殷海光老師時,走廊上有人大吵大鬧,他出去說老師在睡覺休養請小聲,沒想那人態度惡劣繼續粗魯不理,王一怒就揮出一拳,那人摔倒後,有點受到驚嚇就溜掉了。事後曉波發現手在流血,原來雖然氣勢原在,但太久沒打架了,一打就受傷,趕快去急診室包紮。
之後幾年因為民族主義座談會爆發衝突,衍生了台大哲學系事件,他是苦主之一,好在世新成舍我收容,一九七四年後到世新任教多年,在平反之後一九九七年才又返回台大。我在一九九三年四月繼楊國樞與瞿海源之後,擔任澄社社長,同年五月以澄社名義舉辦全天的台大哲學系事件廿周年研討會,當時台大代理校長郭光雄也來參加,邀請當事人陳鼓應、李日章、趙天儀、胡基峻、王曉波、錢永祥前來講述,會中並分送台大哲學系事件始末文件,另由楊國樞、李鴻禧、葉啟政評論,整個討論會就由澄社三位社長共同主持。在該次討論會中很多人提出應由台大主動平反,同年十月廿三日台大校務會議決議成立台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小組(陳維昭新任校長期間),一九九五年五月廿八日公布調查報告平反。我那時負責籌畫這件事,心中是有曉波影子的。他對這件事的反應與別人不太一樣,認為自己是為所當為,也知道會有難以預測的後果,與當道不合,在那個時代本就會受到迫害,現在若能回復正義當然很好。這種講法聽起來,是有一點向他母親學習的決心在。
這就是青年王曉波,我心目中充滿熱血的學長王曉波。
他後來花比較多時間參與保釣以及海峽兩岸事務、治法家研究與台灣史,成為馬英九的兄長與導師。我在教育部服務時,他從旁關心高中歷史課綱的調整,認為我們負有歷史責任,必須謹慎修訂。一直到前幾年他進一步成為馬英九的國師,實質參與高中歷史課綱微調,引起社會上與史學界學生界重大爭議,這些都已是很後面的事。他在年輕時,應該是比較有強烈台大自由派的精神,但可以感覺出他在特殊成長過程下的沉重基調;中年之後則轉移往更多的民族主義,好像情感有所釋放也變得更為自在。這中間的轉移,應有更多的詮釋,方能得其全得其平,需要有更熟悉他的人來做定位工作,就不在此強作解人。謹以此文懷念曉波,還有那一段年輕時代的過往。
我的母親叫章麗曼:一個「匪諜兒子」的自白
文◎王曉波
「從小,我不敢跟別人說母親的名字,甚至也曾在心裡抱怨過媽,害我們從小揹負『匪諜兒子』的罪名,受盡羞辱和迫害。」
一九五三年,記得那晚全家在等爸爸從台北回來過元宵節,久久等不到,我們小孩只好先睡了。第二天醒來,只見家中凌亂,外婆不知所措的在那哭,媽媽不見了,剛滿月不久的小妹也不見了,只剩下還在熟睡的大妹、二妹。經外婆解釋,才知道,昨天深夜來了一批憲兵,抄遍全家後,把媽帶走,為了餵乳,媽把小妹一起抱走。爸爸也在台北憲兵司令部被扣押了,所以,沒有回家過元宵節。
媽媽被捕後,起先關押在台中的憲兵營部,那是前不久我父親在那當營長的地方。也許是由於父親出身憲兵官階中校的緣故罷,媽關押在台中時,還准許婆帶我去面會。在媽解送台北之前,告訴婆,只當她車禍死掉,要婆帶大我們,當時小妹在吃奶,我還記得媽對婆說:「如果帶不了那麼多,就把她(小妹)送掉罷。」媽說著就哭了出來,並摸著我的頭說:「那要好好聽婆的話,幫婆帶好妹妹。」當時我似懂非懂的含著淚點了頭。從此我們就沒有再見到媽,再見到媽的時候就只剩下一罈骨灰了。
媽遇難時二十九歲,我才只有九歲多,大妹七歲,二妹六歲,小妹未滿週歲。爸爸也因「知匪不報」判處七年徒刑。我們至今沒有見過媽的判決書,只有戶口名簿上的一欄記事──「因叛亂案經憲兵司令部判處死刑於民國四十二年八月十八日執行死亡。」
料理母親後事的是當時尚在憲兵服役的表兄謝永全,是他把小妹從台北抱回來的,我們才知道母親遇難了。記得當時,婆哭天搶地的叫著:「女死了,兒不在(在大陸),叫我怎麼辦啊!往後的日子怎麼過啊!」我當時只有一個模糊的感覺:「以後我就是沒娘的孩子了」,兩個妹妹更是只知道傻乎乎的看著婆。
那時婆望著我們兄妹,想到母親的遇難和往後的日子,就悲從中來的哭泣,我最長,只有我安慰婆,「只要我們長大,一定會好好的孝順婆」。婆聽了更難過,又望著我們哭:「我的仔啊!你們什麼時候才長大啊!」婆不哭了,我又有一種說不出來的難過,但又怕再觸動婆,就只好自己跑到一條離家不遠的小河邊,獨自一個人莫名的大哭一場才回家。
我們在台灣本來就沒有什麼親戚朋友,媽出事後,更沒有什麼親戚朋友敢跟我們往來。母死父繫獄,一個外省老太婆帶著四個外孫,在人生地不熟的台灣,外婆不要說台灣話不會說,連普通話也不會講。我們是家破人亡的陷入生活的絕境。
我和大妹只好在台中育幼院掛了個院外學童的名義,每個月每人可以領到二十元的救濟金。婆要我們到市場去撿一些菜葉子回來,好一點的曬成乾鹽葉,差的就餵幾隻雞鴨,我們從來就沒有吃過婆養的雞鴨,那是逢年過節賣來換取一點現錢的。
雖然一些當年跟父親稱兄道弟的人不敢和我們往來,但是,人間還是有溫暖的,還是有些人和我們往來,例如,表兄謝永全,一些父親當年的傳令兵、司機,和幾位憲兵,幾位大舅裝甲兵裡的同學。他門偶爾經過台中,總是從微薄的薪餉中,十塊、二十塊的接濟我們。
逢年過節,別人好不熱鬧,我們只有瑟縮在家裡,但也經常有鄰居送來拜拜完了的雞鴨、肉粽,那是我至今猶記得的最美味的食物。那些鄰居,一位是長期患肺結核而賣女兒的洋鐵匠,另一位是經營冰店失敗也賣女兒的黃老闆。父親是軍人,有配給的眷糧、食鹽,母親生前常把一些我們吃不完的糧食和鹽分給他們。後來,我進台大回台中省親,有次遇見洋鐵匠太太,還拉著我的手訴說著母親,「你媽媽真正是好人,真冤枉,你都愛卡打拚,嘸好讓你媽媽失望。」
媽媽去世後,我成熟了不少,看到了人世的涼薄,也感到了人間的溫暖。有幾件刻骨銘心的事,至今仍不能忘懷。
爸爸媽媽相繼扣押後,全家慌亂成一團,居然還有爸爸的憲兵同袍來找婆,說是要替爸媽活動,向婆索取活動費。父親在軍中一向清廉自持,家中並無積蓄,婆在六神無主中,只有把她老人家帶來台灣的一些陪嫁首飾變賣支應,沒有,還兇婆婆,最後當盡賣光,那位「善心」的叔叔也就一去不回了。全家陷入絕境,這一來更是雪上加霜。
除了到市場搶菜葉,家中沒有糧食,有次婆要我到收成完了的番薯田裡去撿剩下的一些番薯頭,被主人發現,一腳踢翻在番薯田裡,灰頭土臉的爬起來,舉首望蒼天,即使媽有罪,我們又何辜?我只要像一條野狗般的活著,但我不如一條野狗!
母親死後,從小揹負著「匪諜兒子」的罪名,而常常因此和同學打架,雖然每次都是瘦小的我被打得頭破血流,但是,老師追究起來,被處罰的都是我。
我因為是育幼院的院童,在學校一切費用都免繳,小學五年級,我選擇了「投考班」,「投考班」的補習費也免了。但由於幼稚的「虛榮心」,我從來不敢跟同學透露我是「免費生」。有次中午,老師宣佈要大家回去拿補習費,我為了怕一個人留在教室而「曝光」,就陪著隔壁同學回去拿補習費,回到教室時遲到了,那位同學交上二十元補習費就回到座位,老師則要我伸出手來,用竹掃把的竹支抽我,一面抽一面說:「你這個匪諜的兒子從來不交補習費,還跟別人回去拿補習費!」當時我感到像是在大庭廣眾前被剝光了衣服般的被羞辱,我咬緊了牙根忍住了眼淚,不知被抽了多少下,老師才要我回座,我實在忍不住的向他說:「老師,您好狠,我記得。」結果又換來一頓毒打,抽得兩隻手鮮血淋漓,但我一直沒吭一聲,也沒掉一滴眼淚。
有次大妹高燒已神智不清,婆帶我把大妹抱到台中醫院求醫,醫生說要住院,但交不起三百元保證金。從南昌鄉下來的婆只會拉著我跪下向醫生叩頭,請醫生救大妹一命,為了救大妹的命,我拚命的在水泥地上叩頭,只見醫生起身出去,碰然的把門關上。我們只好悵然的把高燒中的大妹又抱回來。後來,是好心的里長幫我們證明辦了貧戶就診,才挽回大妹。
念中學,離家比較遠,同學間有時問起母親,我都說是病死的,但「匪諜兒子」的陰影還是擺脫不了,有次跟教官抗辯,教官無以為辭就在同學面前脫口而說:「你是匪諜的兒子,不要以為我不知道。」一九七三年,「台大哲學系事件」,我被警總約談,被關在警總地下室偵訊,偵訊員也劈頭就說:「你不要像你母親一樣,子彈穿進胸裡的滋味是不好受的。」
從小,我們家就是列管戶,常常在半夜睡眠中,被查戶口的手電筒照醒。後來,在台北教書,戶口轉來台北,警察還是每半個月要來查一次戶口,直至前幾年解嚴為止。
爸爸出獄後,失業了一陣子,後來在台中地方法院當一名執達員,類似抄寫員,以微薄的薪水維持著一家六口的生活。
大妹初中畢業後,被爸「哄」去念嘉義師範,畢業後在新竹一家天主教小學教了幾年書,辭職回台中後就找不到教職了,後來才找到台中啟聰學校。大妹從小能詩能文,才華橫溢,但由於從小營養不良病痛纏身,及諸事鬱鬱,而於一九七一年,自殺身亡,遺有一子,而使我深深自咎,對不起媽,沒能好好照顧妹妹。
二妹在高中畢業後,考取私立大學,爸要負擔我念台大,二妹只好輟學,在鐵路局當過觀光號小姐。二妹在火車上受到欺負,經常到台北來看我,兄妹二人只有抱頭痛哭,我也只好頻頻的安慰二妹,「都是哥哥不好,為了哥哥念台大,害妳在車上受欺負。」二妹後與一位美國教授結婚,移居美國,生育後,因長期病痛而於一九八七年去世,遺有一子。
外婆於一九八五年回南昌定居,逝世於今年三月。二妹的死訊,我們一直不敢讓外婆知道,而讓外婆臨終還在叨念,為什麼二妹好久都沒有信來。
小妹五專畢業後,也是與美國人結婚,移居美國後,小妹還給我來信說:「從小我們就揹著『你媽是匪諜』的罪名,來到美國後,不再怕有人指責我,『你媽是匪諜』了。」小妹婚後育有一子,並繼續念書,直到今年才拿到學位。
我們從來沒見到過母親的判決書,也不知道母親是怎樣遇害的。直到我台大研究所畢業後,那年料理母親後事的表兄來家過年,而拉著我到戶外去,跟我說:「你已經學成畢業了,應該知道你媽是怎麼死的。」他才把將近二十年前,他在憲兵部隊裡四處打聽母親逝世的經過告訴了我。
媽被捕後,曾自殺二次,一次是吞金項鍊,一次是吞下一盒大頭針,但都沒有成功。我們已無法知道,媽是處在何種境遇,而必須以自殺來保衛自己。臨刑前,要她喝高梁酒,她拒絕了;她說,她是一個清清楚楚的人,死作一個個清清楚楚的鬼。要她下跪受刑,她也拒絕了;她說,她對得起國家,對得起民族,上對得起天,下對得起地,她是無罪的。最後,她是坐著受刑的,臨刑前還是一直高呼口號,口號聲是被槍聲打斷的。
表兄告訴我,他這番話從來沒跟任何人講過,也要我不要告訴任何人。為了怕婆婆和爸爸聽了難受,我也從來沒有說過,直到一九八○年,我到美國第一次給大陸的大舅通信,才不能不告訴大舅母親逝世的經過。
也許是由於幼年生活的經驗,使我對社會底層生活的民眾充滿了「我群感」和溫馨的同情,並曾矢言:「我來自貧窮,亦將回到貧窮。」經過「自覺運動」、「保釣運動」,和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更我理解到,我們家庭的悲劇僅是整個民族悲劇的一部分。
我的外曾祖父章子昆曾支持北伐,是陳布雷的好友;外祖父章壯修在北伐軍未進南昌城時,已是國民黨地下黨員,後在「七三一事件」遭土共綁架,把人贖回來後,但因酷刑而病死。父親因受到鄉前輩何應欽的感召,從軍閥周西成統治下的貴州,與同學結伴步行經?江(註一)到南京投身國民革命軍,參加抗戰,在「南京保衛戰」中倖存下來。大舅在抗戰時響應「十萬青年十萬軍」,勝利後考取清華,但因曾任「國民黨軍官」,在大陸勞改十八年。祖父在「土改」時,活活被打死在鬥爭台上;祖母遭掃地出門,而餓死於一九六○年。
所以,八○年我在美國給大舅的信上就說到:「舅舅,您可聽見我們的呼聲!您可聽見婆的聲聲喚兒聲?我們家族的悲劇,也是中國悲劇的一部分,我們不怨天也不尤人,我們只恨中國為什麼不強大,自己為什麼不爭氣。我們只應抹乾眼淚為中國的明天而奮鬥,希望我們的悲劇不要在我們的子孫身上再重演。」
在「白色恐怖」的陰影下,從小,我不敢跟別人說母親的名字,甚至也曾在心裡抱怨過媽,害我們從小揹負「匪諜兒子」的罪名,受盡羞辱和迫害。今天,我必須大聲的告訴大家,我的母親叫「章麗曼」,我就是章麗曼的兒子,我以母親的誓死不屈而感到光榮!
(註一)原文影像不清,無法判斷。
(原文刊於《中國時報》,1991年6月3日,第27版「人間副刊」)
(2009年1月19日,張鈞凱重新謄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