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有侵害著作權,請速告知,我們將盡速移除 ♦
2021/1/21
—我為什麼寫這本書
這本書是我對中國如何成為世界變革力量的看法!
我既不是一名經濟學和社會科學研究者,也不是政治學研究者,僅僅是一名理論物理科研人員和大學管理人員,或許有上百上千種理由可以不該寫,或者說不能寫這本書。但是,我之所以寫此書的唯一原因就是我骨髓中流淌的炎黃子孫血液,我的腦海中不可能忽視“一帶一路”這偉大的倡議。
我小時候在新加坡長大,並且中小學就讀中文學校。那時,我就認識了中國的一個歷史人物,大漢的外交家和探險家張騫。但是直到2013年,我對“一帶一路”產生了濃厚興趣的時候,才開始更多地瞭解他。他生活在西元前164年至西元前114年,在百度對他的簡介中有一段話深深震撼了我:張騫被譽為偉大的外交家、探險家,是“絲綢之路的開拓者”、“第一個睜眼看世界的中國人”。

張騫雕塑(來源於百度百科)
我是在2016年春季的一天讀到上面這段文字的。我感到震驚和意外的原因不是因為他是偉大的外交家和探險家,甚至也不是沒有因為他被稱為“絲綢之路的開拓者”,而是被認為“第一個睜眼看世界的中國人”。我突然意識為什麼我自己可以被“一帶一路”深深地吸引。因為“一帶一路”是由一個擁有數千年悠久歷史、“東方文明”發源地的泱泱大國發起的第一個深刻而廣泛的全球倡議,使得14億中國人在21世紀能夠真正的“睜開”眼睛“看世界”。
中國是佔據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和擁有五千年悠久歷史的國家,因此中國不得不努力地“看世界”,也可以說時至今日仍在努力的過程中。自漢朝之前,中國已經有了幾千年的歷史,但是儘管如此,張騫仍是中國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自從張騫出使西域以來,中國又過了幾千年。我不禁問自己,中國或者說中國人民現在睜開眼睛看世界了嗎?我認為如果“一帶一路”能夠實現中國“睜開眼睛看世界”的巨大成就,這將不僅僅是中國的轉變,更加是全人類的進步。
這本書也恰恰是我對中國如何成為世界變革力量的拙見!
就像我前文提到,在2016年之前,這是一本我不僅從未想過,甚至無法相信可以完成的書籍,這可能與我沒有寫這本書的傾向和願望有關。大約在那個時候,我有了一次職業轉型的經歷。而恰恰是那次經歷讓我意識到,“一帶一路”曾經使得中國是多麼的現代化,並且直到現在仍在影響著中國。我自身深受中華文化中與人行善的影響,無法割捨我所繼承的中華文化傳承。
2013年秋,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同志發表了兩次重要講話。其中一次是9月在哈薩克納紮爾巴耶夫大學發表的題為“弘揚人民友誼、共創美好未來”的演講,另外一次是10月在印尼國會上。在這兩次講話中,習總書記首次提出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概念:“一帶一路”倡議。
習總書記在哈薩克和印尼的講話中提出重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來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
據中國外交部網站報導,2013年9月習總書記在哈薩克斯坦表示2100多年前,中國漢代的張騫兩次出使中亞,開啟了中國同中亞各國友好交往的大門,開闢出一條橫貫東西、連接歐亞的絲綢之路。哈薩克是古絲綢之路經過的地方,曾經為促進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交流和合作做出過重要貢獻。千百年來,在這條古老的絲綢之路上,各國人民共同譜寫出千古傳誦的友好篇章。習近平指出,兩千多年的交往歷史證明,只要堅持團結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鑒、合作共贏,不同種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完全可以共用和平,共同發展。
根據《ChinaDaliy》報導,2013年10月習總書記在印尼國會上講話中表示“幾百年來,遙遠浩瀚的大海沒有成為兩國人民交往的阻礙,反而成為連接兩國人民的友好紐帶。滿載著兩國商品和旅客的船隊往來其間,互通有無,傳遞情誼。中國古典名著《紅樓夢》對來自爪哇的奇珍異寶有著形象描述,而印尼國家博物館則陳列了大量中國古代瓷器,這是兩國人民友好交往的生動例證,是對“海記憶體知己,天涯若比鄰”的真實詮釋。”
正是這兩次演講,習總書記向中國和世界人民宣佈了“一帶一路”倡議。
在習總書記這兩次講話的四年後——2017年5月14日至15日,首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北京成功舉辦,此次論壇有來自160多個國家的29位國家元首和代表團出席,但是基本上沒有西方國家的領導人出席。
2019年5月24日至27日,“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再次在北京舉辦,這次共有37位國家元首出席。更重要的是,每個國家的元首(包括缺席首屆論壇的新加坡總理李顯龍)以及東南亞國家聯盟(ASFAN)的代表(印度尼西亞由副總統優素福·卡拉代表)都參加了本次論壇。另外意大利、瑞士和奧地利的領導人也參加了會議。我很榮幸參加了這次論壇並發表了演講(見附錄A)。不得不承認,我與中國和中國事物的聯繫並不是簡單的,而是非常深刻的。與來自世界各地的許多中國朋友不同,我並未在中國任何一個地方讀過書。然而我接受的關於中國的教育,是在新加坡讀的小學和中學的一部分,期間我對中國文字、歷史和文化有淺顯的瞭解,但是遠遠不足。回顧過去,我是從零碎的閱讀中學到了大部分的中國歷史知識,並非是從系統的教育中。我在美國生活了幾十年,尤其是在東北部的新澤西州讀了四年大學,也許正因如此我在美國最好的一個南方人朋友曾調侃我“比北方佬更像北方佬!”

攝於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我在該論壇上發表主旨演講
非常有趣的是,我很有可能是擁有最多國家公民資格候選人的吉尼斯世界記錄保持者。我出生在印度,是一個英國公民。但是搞笑的是,我的第一個旅行證件的封面上竟然寫著“持有人無權在不列顛群島居住”。恰恰是這個話,引發了1972年居住在烏干達的印度人發生了一場大規模的國際事件。
我於1964年離開新加坡前往美國。正是這一年,新加坡為了脫離英國殖民統治,與馬來西亞組成一個聯邦國家。因此我當時持有的護照是馬來西亞護照。在美國生活了一年之後,新加坡從馬來西亞分裂出去,我也從此不再是馬來西亞公民。
從1983年開始,我在美國生活工作了19年之後,成為了美國公民。由於新加坡不允許雙重國籍,我非常不捨 地放棄了新加坡國籍。我曾經和一個猶太友人交流中得知,以色列允許雙重國籍,因此他可以同時持有美國和以色列護照。當我得知這個消息的時候,我有點嫉妒。為什麼新加坡不能更寬宏大量一點呢?這樣就可以多與我的“家鄉”多一些聯繫了!1983年我放棄新加坡國籍後,這是我第一次理解“地緣政治”這個詞的含義!
1977年對我而言,無論是在學術還是專業上都是非常重要的分水嶺。這一年,中國開始打開國門與外界聯繫,並且開展轟轟烈烈的改革開放。1981年4月,應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邀請,我訪問了中國。這是我們家族自從1949年匆匆離開中國後的第一次回國。在三周的訪問時間內,我親眼看到了那時候的中國。我去過很多地方,從北京到長春,再到武漢,最後到上海。我既興奮又難過。我記得在上海的時候,我聽到每個人幾乎都在說我在家裡說的語言。我的母親、妻子和在英國出生的女兒都是上海人!那裡許多住在破舊的房屋稱為筒子樓,我看到朋友和親戚的生活條件很落後,我內心非常沮喪。在1981年的三個星期裡,我真實見證了一個國家如果將自己與外界隔絕會後的景象——貧窮落後!
在過去的四十年中,我曾多次前往東亞參訪,尤其是中國內地,但是從未在內地真正生活過。直到2019年的四月份,我以海南大學國際顧問委員會主席、一帶一路研究所名譽院長的身份在內地生活了整整一個月。海南大學校園地址位於海南省海口,借此契機我開始深入瞭解中國的高等教育體系。然而有趣的是,在此之前我從來沒有真正在中國居住一段時間和體驗中國的風土人情。

攝于海南大學
我最接近“住在中國”時間的是在澳門特區工作三年。澳門是中國的領土,但施行的是“一國兩制”的政治制度。我在澳門的住所距內地僅僅一牆之隔,大概50英尺。每天早上,我都能從住所看到內地公安局飄揚的五星紅旗,而晚上,我從住所中能夠聽到的聲音就是內地公路上的汽車往來行駛的聲音。

參觀澳門濠江中學。這是澳門最著名的“紅底”高中之一
即便是只能生活在澳門,我也能夠有意識地“看”中國,同時作為一個外來人與本地人進行交流。由於我的父母是中國人,同時我在成長過程中一直在新加坡接受中文教育,中華傳統文化深深地融入了我的潛意識中。正是這種潛意識,也是我寫這本書不可避免的另一個原因。
如前所述,兩年半前,我都不可能會有著作這樣一本書的想法。畢竟在美國的大部分工作生活中,我只是一個單純的理論物理學教授。我不是經濟學家,更不是政治學家。隨後我擔任美國高等教育機構管理職務,之後又在工業領域工作了幾年。在亞洲擔任高級別高等教育管理人員的10年中,我深度參與了三所高校的運營發展:國立成功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和澳門大學。我擔任的每一個職務中,主要任務就是盡最大努力地提升高校教育水準、落實高校育人使命。有悖於這個出發點的任何國內外事件,哪怕是關乎這所高校存續發展,我同樣沒有時間和興趣關注。
對於我的背景而言,2016年我對一帶一路的瞭解還僅僅是皮毛。直到我為了去新加坡演講的時候,而不得不坐下來開始認真地研究,誰知我一下就沉浸其中,可以說這似乎是一種改變我人生的經歷。我自從聽聞瞭解“一帶一路”之後,我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內心深處的某種東西在無限地激勵著我。

2017年6月16日,我和兩位領導在臺灣拍的一張合影:他們是分別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分子生物學博士和物理學博士,均是各自領域傑出的世界知名學者和高等教育領域專家。能夠這兩位優秀的專家一起共事就是一種純粹的快樂,是任何人都嚮往的特權。
前文提到,二戰結束後不久,在1945年我在印度出生。我出生後不久,家人們回到了中國,恰恰經歷了四年艱苦的解放戰爭。雖然沒有印象有人告訴我,但是我也記得由於戰爭全家經常在中國各地搬家。所以在1950年左右,我們家庭不得不離開了中國大陸,在澳門和香港暫居了一段時間。後來我父親保羅·馮(PaulFeng)在當時新加坡英文報紙《虎旗報》編輯部找到一份工作後,全家從中國搬到新加坡。
我在新加坡生活的14年是我的性格塑造期。新加坡在這段時間內大部分是英國的殖民地,但它還是我的家。用一個老生常談的話來講,這座城市也將永遠是我的“家鄉”!我在新加坡從小學到中學都是在中文學校讀書。我的小學——養正小學,對我的印象遠比其他學校更加深刻。

維基百科中所述,“虎標”又稱新加坡標準或新加坡虎標,是由吳文虎先生創立的,吳先生也是著名“虎標萬金油”的創始人。
養正小學是新加坡廣東同鄉會在1905年建立的,這個年份甚至還早于民國成立(1911年)的時間。眾所周知,,在1963年前(除了世界第二次大戰中的3年8個月),新加坡被日本軍隊殘酷佔領了將近144年。直到1963年,新加坡成為了英國的殖民地。養正小學實際上是當地廣東人為了後代教育而建立的,他們想要他們的孩子去盡可能多的接受具有廣東傳統的中式教育。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在學校大禮堂中懸掛著一塊很大的孔夫子牌匾。
另外,二戰後中國很多人來到養正小學任教,桂承平老師也是其中之一。她說著一口非常純正的普通話,言談舉止非常優雅,這樣的老師在新加坡當時非常少見,令人非常悲傷的是她已經永遠離開了我們。後來我才發現桂老師是一個很有才華的藝術家,並且找到了90年代她的相片。

桂承平女士(右一)
桂老師是一位具有魅力和愛心的老師。她過去常給我們講在中國的經歷。其中她多次提到的一個情境,我至今難忘。那時候的黃河充滿泥沙,渾濁的河水看起來非常黃。她卻會非常激動的講到,這條河看起來真的是黃的!現在回想起來,她對祖國的想念是溢於言表的!
桂老師提到的黃河,就是那首由著名作曲家冼星海譜曲的“黃河大合唱”中描述的河流。冼星海也是養正小學的校友,這首歌是他在1939年初抗日戰爭期間于延安創作。

冼星海照片
小學六年時間中我周圍充滿了中國的氛圍。這也清晰展示了這所學校的靈魂,而我也有幸能夠繼承發揚。6歲的冼星海去新加坡之前也很巧合地住在澳門,儘管他在澳門居住的時間很短,但是由於他在中國音樂的顯著成就,澳門有一條街道命名為“冼星海大馬路”。

澳門冼星海大馬路標誌
所以我和冼星海的經歷也有很多相似之處,現在我聽朋友開玩笑說養正小學至少有一個世界知名的校友,但是可惜的是那肯定不是我!
此外在新加坡期間還有一件事,給我留下了終身難忘的記憶。這件事發生在我高中一年級,教文學課的老師給我們留了背誦《琵琶行》的作業。這首詩是由唐代著名詩人白居易(西元772-846)所作。
由於中文老師經常佈置背誦的作業,同學們都不太喜歡他,所以他的名字已經被我們所遺忘了。琵琶行共有七百餘字,不僅字數多而且晦澀難懂,我和同學們都非常煩惱。背誦記憶的過程非常艱苦難熬。我不得不在家裡踱來踱去,一個小時又一個小時反復記憶它,讓它刻進我的大腦細胞裡。
但是當我最終成功背誦它的時候,令我非常自豪。至今我腦海中仍然記得這首詩。五十年後我再次讀了這首詩,其中有一些漢字比如篦(發音為bì),單純在書本上寫著這個字,我確信我無法準確讀出來。但是在詩詞中,以鈿頭雲篦擊節碎為例,詩句只是暫時在記憶中隱藏著,遇到的時候可以輕鬆地讀出來。

白居易的畫像
我還記得當時記住這首詩時特殊的心情。我不僅僅高興于能夠成功記住了一千年前如此優美的詩句,完成了這項艱巨的任務,還明顯產生一種感受,那就是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嚮往與歸屬。那時候的我還太小,並沒有這麼強烈的感覺。直至我理解“一帶一路”倡議內涵之後,此時距離那時已經過去六十年!
回顧過去,我不得不承認,在新加坡所接受的中國文化教育內容無論在廣度還是深度,均無法與在中國內地和港澳臺相比,但是也為我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從而我也增強了對於中華文化的歸屬感。.
我在曼徹斯特大學理論物理系從事博士後研究和哥本哈根的尼爾斯·玻爾研究所從事訪問教授的時候,與中國大陸同胞建立的深厚友誼,至今難忘。
1964至1972年,我在美國攻讀本科和研究生。這八年時間內,我對於中國的科學研究並無任何認知。因此當我在曼徹斯特大學理論物理系的圖書館內,讀到《物理學報》雜誌上關於中國內地的理論物理前沿研究時,我內心感到非常震驚。
作為一名理論物理學家,我對何祚庥一篇關於量子場論的文章產生濃厚的興趣。雖然我的研究領域與他的主題關系不大,並且我閱讀中文文章是非常困難的,但因為他是第一個我遇到的來自中國內地的理論物理學家,所以我努力將它從頭到尾一字一句讀完。我後來多次到中國科學院理論物理研究所訪問,有幸見到了何教授本人。
曼徹斯特大學求學期間,我對很多事印象深刻。但是提到最深刻的一次,也許就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遇到了來自中國大陸的學者。他就是吳祖澤博士,一位世界上著名的血液專科專家,後來他擔任了軍事醫學科學院院長。我記得他來自上海,由於我和我太太也都能說一口流利上海話的緣故,我們很快成為了好朋友。因此我從吳教授那裡對於中國的一般狀況也有了一些膚淺的瞭解。

一幅充滿美好回憶的照片。圖為曼徹斯特大學理論物理系1973至1974年的委員、教師、博士後和學生。這張照片拍攝位址位於舒斯特大廈外,離曼徹斯特的普陸士街不遠。我是第三排第二個人。

吳博士照片

尼爾斯·玻爾研究所。我在照片右邊的一間辦公室裡居住了兩年
1979年,我來到丹麥哥本哈根的尼爾斯·玻爾研究所(NBI)做訪問學者的時候,明顯增深了對中國的瞭解。尼爾斯·玻爾研究所是世界著名的理論物理研究中心,是量子力學的發源地。眾所周知1977至1978年對於中國發展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新時代,因此大批的中國科學家出國交流學習。在玻爾研究所,我非常幸運地結識了一批中國最傑出的核子物理和粒子物理學家,比如吉林大學吳成禮博士、清華大學楊福家博士、清華大學徐湛博士、原子研究所(401研究所)陳永壽博士和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冼鼎昌博士(已故)。
這些來自中國的青年才俊,後來都成為了海內外各自領域知名專家。從他們身上,我瞭解許多中國的文化、曆史、特徵等知識,從此之後,我對中國的瞭解和感受,不再那麼神秘和未知。

這張照片於1979年在哥本哈根拍攝。我是左邊第二個。在我旁邊的是吳成禮,站在這位女士旁邊的是陳永壽,坐著的是徐湛,最後是冼鼎昌。
2007年至2014年,我先後在臺灣擔任國立成功大學和國立清華大學的常務副校長。在臺灣七年裡,我對中國社會的風土人情有了更為透徹的瞭解。這段時間是我第一次在中國體制裡(儘管是中國臺灣省)工作,我更加深刻了解了什麼是中國的生活。
按照馬英九先生對於在台“長期居留”標準的定義,我在臺灣“長期居留”中結識了許多親密的朋友,比如台灣大學教授陳嫦芬女士和她的丈夫古台昭,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的教授比如王偉勇教授和陳益源教授,他們都讓我確信了那句話“臺灣比中國更加的中國”!
另外非常有趣的是,位於北京的清華大學和位於臺灣的國立清華大學有著相同的校訓和校歌,而且他們的校徽在本質上也相同,只是細微之處稍有區別。國立清華大學的校徽是20世紀初在北京建校的時候創立的。
閩南和臺灣在歷史文化和語言上的同源聯繫,以及清華大學和國立清華大學之間的歷史淵源和學術交流等等,都成為了我和中國之間無法割捨的聯繫。
見證到中國在21世紀的飛速發展,我不禁產生一個疑問。為什麼中國沒有在粉碎“四人幫”之後而產生巨大的動盪?直到2000年左右,我在給南京大學的好友陳金全教授的訃告中,提出了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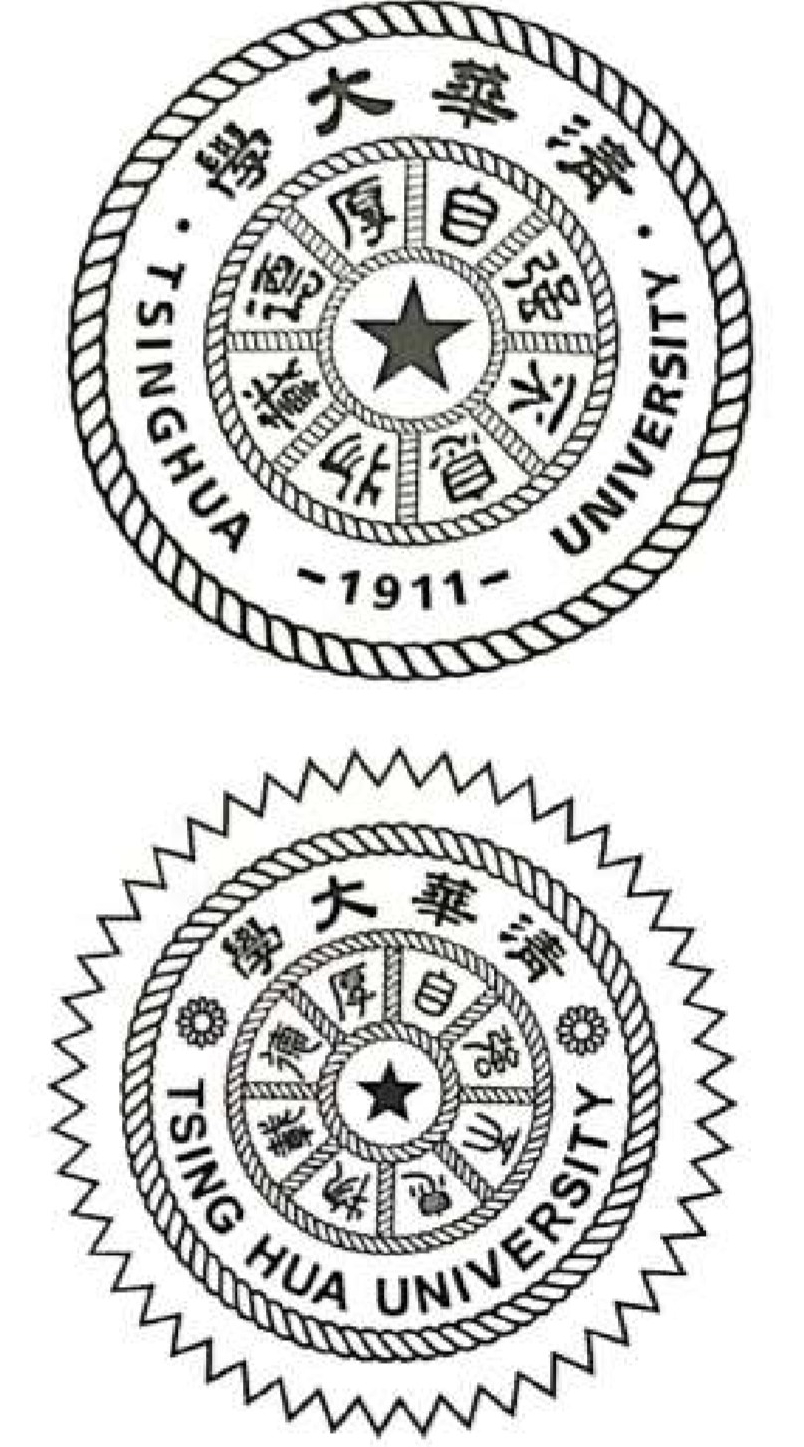
北京清華大學和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的校徽

清華大學校長陳吉甯和國立清華大學的校長陳力俊分別帶領各自的團隊於新竹墓園,弔唁共同的前校長梅貽琦
我寫道:
“我的朋友,世界著名的數學物理學家陳金全教授,在1999年不幸地離開了我們。為了紀念他,這本由陳教授的朋友和同事們共同完成的科學著作被出版了。
陳教授的生平是中國這一代知識份子的寫照。這一代人生活雖然令人感到惋惜,但另一方面也令人感到非常振奮。
1976年對於現代的中國來說是至關重要的一年。這一年的9月9日,毛主席逝世,緊接著“四人幫”被粉碎,十年痛苦的“文化大革命”結束了,從此中國開始進入了一個新時代。我相信將來肯定有一天,歷史學家會把這個新時代視為“20世紀的世界奇跡”。
在經歷了十年的徹底毀滅之後,1976年的中國在經濟上、科技和文化上都處於完全“崩潰”的邊緣。對佔據人類人口四分之一、占亞洲近一半面積土地的泱泱大國而言,這樣的災難可能會對全球做成非常可怕的影響!
然而,這樣的後果並沒有發生。
沒有崩潰的一個根本原因是,數以千萬計的中國知識分子做出了巨大貢獻。在那個時代最黑暗的時刻,他們忍辱負重,無懼對身體和精神的痛苦折磨,一直對自己、家庭、職業和國家充滿著希望。他們即使失去人身自由也一直與國家站在一起。他們是國家的重要支柱,支撐起了國家的尊嚴。中國在21世紀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這一群體。
”正如前文所述,由於客觀原因我曾有過四個“國籍”。即使我對每個國家的感情都非常濃厚和忠誠,但是我血液中傳承的中華文化,卻像是一根針,編織了我對中國的熱愛並且將我對中國的感情深藏於心,不可遺忘。如果2016年潘教授從新加坡打電話邀請我去新加坡探討“一帶一路”時,我沒有上文提到的經歷,可以確信我極有可能會拒絕他。

《科學中的數學之美:陳金全的智慧之路》
封面資料來源: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worldscibooks/10.1142/5163
我從未接受過“中式”教育,因此我對於“我是誰”總是產生困惑與不安。我曾經和猶太裔美國朋友深入交談,當我向他提到我對自己的文化傳統和國籍的差異感到深深的不安和困惑時,他深深地產生了共鳴。他毫不猶豫地回答:“我完全理解你的感受,也非常感激你的分享。無論猶太人擁有哪個國家的國籍,但是我相信大多數猶太人同胞都會深刻體會到我們的猶太傳統是永遠植根於我們血液之中的!”從此,我內心的不安終於得到了緩解。
我對“一帶一路”倡議癡迷研究,並非刻意迎合,而是我過往經歷感受和繼承的中華文化。進而逐漸深入探索“一帶一路”倡議對於我個人的深遠影響,從而希望能夠探尋它對於中國乃至整個人類的重要意義!
由此編著此書。
♦專文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