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內容轉載自 《文化縱橫》微信:whzh_21bcr ♦


CSSCI核心期刊《文化縱橫》2020征訂火熱進行中
享半年免費暢讀所有出版電子雜誌VIP(僅余200席)
點擊文末閱讀原文可在“文化縱橫”微店訂閱
亦可搜索“文化縱橫”淘寶店訂閱
✪ 孔元 | 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
《文化縱橫》微信:whzh_21bcr
【導讀】要理解今天美國政治的複雜生態,“保守主義”是一條必須抓住的主線。本文系統全面地梳理了美國當代保守主義從冷戰時期到全球化時期再到逆全球化時期的歷史源流與演變過程,認為美國當代保守主義既是一場觀念運動,又是一場政治運動。它產生於冷戰時期,目的是為了應對蘇聯的挑戰。在蘇聯解體後,它發展成推動全球化的重要思想觀念。全球化造成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問題激化了美國的社會矛盾,並最終導致特朗普上臺。這一政治動向在思想上表現為保守主義陣營的分裂,民族保守主義成為一股新的思想和政治力量,它為民族主義辯護,試圖借助國家力量解決美國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問題,並因此成為支撐特朗普執政的重要思想來源。作者深刻地指出,當代保守主義是美國在對自由霸權的幻滅之後,期望將西方從物質主義、科技主義、資本主義的平庸中拯救出來,從歷史終結的“末人”世代中拯救出來的一場古典式的靈魂救贖。本文對保守主義的理解,對於把握美國乃至西方世界的思想走向,具有重要意義。
本文原載《國外理論動態》2020年第1期,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美國當代保守主義的民族主義轉向
▍導言
2019年3月,美國保守派期刊《首要事務》(First Things)刊發了一封宣言式的聯名信——《反對過時的共識》,引發美國保守派陣營內訌。該宣言指出,2016年的美國總統選舉充分暴露出美國保守主義陣營的內部分裂,保守派在特朗普競選問題上分化為不同的派系。在特朗普上臺之後,經過兩年多的分化重組,新的保守主義立場開始明晰化,各方逐漸意識到,隨著2016年特朗普的勝選,舊的保守主義共識已經瓦解,任何試圖復興前特朗普時代的保守主義共識的努力不僅有誤導性,而且甚至是有害的。宣言呼籲,承認冷戰期間舊保守主義共識在對抗共產主義方面的貢獻,不意味著要守著僵死的教條,而是應當在政治時變中尋找新的共識。
無獨有偶,2019年7月14—16日,在艾德蒙·伯克基金會的贊助下,一群對現狀不滿的保守主義政客和評論家聚集在美國華盛頓,召開了一場“民族保守主義會議”。在會議演講中,以色列哲學家、艾德蒙·伯克基金會主席約拉姆·哈紮尼(Yoram Hazony)宣稱:“今天是我們的獨立日。我們宣佈跟新保守主義決裂,我們宣佈跟新自由主義、經濟放任主義決裂,跟人們所稱的古典自由主義決裂。有一樣東西聯合了我們所有人,那就是民族保守主義。”
在這群政治家和知識份子的推動下,美國保守主義在民族主義的旗號下出現了強勁的復興。伴隨著這一思想復興運動,在二戰之後勃興的美國當代保守主義也進入新一輪的思想轉換期,並在後冷戰時代的全球化枷鎖中發展為一場具有強烈批判性和革命性的新的思想和政治運動。
▍戰後的保守主義共識及其演變
美國當代保守主義是在極端左翼與極端右翼的思想夾縫中發展起來的,並在對蘇聯的全面鬥爭中獲得一種自覺性,它在思想上表現為從“新右翼”向“新保守主義”發展的狂飆運動。美國新右翼產生于對美國新政自由主義的反動,表現為商業精英和社會保守人士的觀念運動,融合了經濟和文化保守主義兩股思潮。1960年代之後,美國左翼運動在蘇聯的影響下趨於極端,而新右翼思想在強調放任主義與社會保守主義之間搖擺不定,無法在觀念上形成一股連貫的保守主義思想,包括歐文·克裡斯托(Irving Kristol)等在內的公共知識份子發展出一個“新保守主義”陣營,它在經濟上主張資本主義與國家控制相結合,在文化上主張尊重傳統與接受社會進步相結合,在政治認同上宣導自由公民權。經過這種改造,新保守主義在內部問題上形成一種節制的道德觀,通過一種“中道政治”凝聚了國內社會各階層的訴求,然後將這種共識外化為一種普世主義,形成對抗各種革命和激進觀念的強大思想力量。

(訂閱《文化縱橫》2020年雜誌,享半年免費暢讀所有已出版雜誌電子版VIP,僅剩最後200席)
蘇聯解體後,新保守主義者沉浸在全面勝利的樂觀信念中,在失去一個可以對峙的敵人之後變得更加激進,開始試圖按照美國模式塑造全球秩序,並進而發動一場全面而系統的經濟、政治和思想運動,這就是全球化運動的肇因。後冷戰時代唯我獨尊的優越意識讓美國人相信,自己是負有天命的世界民族,承擔著實現經濟繁榮和政治和平的歷史使命。要兌現這種承諾,就必須將美國的經濟增長潛力與世界的經濟繁榮同步起來,在全球配置經濟生產的要素和資源,從而得以讓其他國家和地區分享美國經濟增長帶來的利益。受此驅動,自由放任主義成為美國經濟決策的底色,它試圖在勞動分工和價值規律的基礎上,構造一個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市場,通過經濟全球化,推動貨物、人員、資本的自由流動,實現資本、貨物等生產要素的最佳配置。奧地利經濟學家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在自己的一系列著作中對該理念做了系統闡釋,他指出:
分工早已超越了政治聯盟體的界限。今天,沒有一個文明國家直接通過本國的生產自給自足地滿足了自己的需求。所有的國家都指望從國外進口商品,並用出口本國商品來支付進口。禁止國際商品交流會對人類文明造成嚴重損害,將葬送成千成百萬人的福利,甚至其賴以生存的基礎。
依照這一理念,只要保證完全的貿易自由,資本和勞動會被投放到能提供最佳生產條件的地方,從而實現生產要素的最佳配置。這在實踐中要求美國在全球配置產業鏈,通過將美國本土打造為金融和科技中心,保留其在產業價值鏈的頂端優勢,並將製造業等勞動力密集型產業轉移到較為活躍的亞洲。通過消除國家邊界,建立全球物流和供應鏈,建立世界範圍的自由市場,美國資本家可以充分利用當地熟練工人,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生產效率,源源不斷地為美國和全球供應廉價商品,而亞洲等地區的國家也可以通過利用美國的資本和技術,擺脫貧困,實現經濟發展。如此一來,既打造了一個美國及其交易夥伴互利雙贏的貿易體系,也擺脫了民族國家鼓動下的戰爭陰影,實現了一個經由貿易打造的自由、繁榮與和平的世界秩序。
這種經濟邏輯的實現要求對民族國家的政治和社會結構進行改造。政治結構的改造表現為全球治理對於民族國家主權原則的約束。為了適應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形勢,就需要建立全球治理的制度機制,從而一方面確定全球自由市場的法律規則,另一方面監管民族國家的經濟政策,避免它走向貿易保護主義。這一原則的邏輯後果意味著社會的政治組織向外延伸,直到形成將所有民族平等地統合在一起的世界國家。由於主權邊界的頑固性,這種邏輯在實踐中發生蛻變,世界體系成為一個霸權國家、國際組織、民族國家和各種非政府權力共同開展行動的大舞臺,在這方面,世界政府和民族國家都成為理想型的單一政權形式,而現實政治則表現為融合了君主、貴族和人民因素的“混合政體”,從而形成了充斥著多元混合層級的新帝國體系。
處於這一治理體系頂端的美國政府不得不根據全球化的邏輯發生轉變,從作為民族國家的美國政府擴展為作為世界帝國的美國政府,以便更好地管理世界經濟、保證政治穩定和和平。為了適應這一新角色,美國的政治結構發生轉變,代議制政府轉變為宣告制政府,政治正當性原則轉變為政治治理的績效原則,政治立法權從國會轉移給由官僚和司法機構控制的專家政府,國會成為權力的橡皮圖章,用漫長的政治爭吵來掩蓋其失去決策權力的尷尬現實,並在這種程式性偽裝中掩蓋民主赤字的政治真相。
儘管邁克爾·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東尼奧·奈格裡(Antonio Negri)仍然將人民視為全球混合政體的一個環節,但他們也意識到,全球資本主義的力量已經發展為滲透到毛細血管的控制機制,從而使得任何組織化的人民反抗變得不可能,政治意義上的人民蛻變為一盤散沙的大眾,他們作為無組織的群體游離於全球政治空間中,腐蝕著本已朽化的民族國家邊界。
人口的大規模流動形成了兩個超越於民族國家之上的新社會階層,一個是巨富階層以及作為其財富管理者的政府和社會精英,一個是社會底層的移民階層。
巨富階層通過各種有形或無形的俱樂部,操控著全球經濟的走勢,而那些駐紮在大學、政府、媒體、銀行和智庫的知識精英則不斷為這些巨富階層提供資本增殖、法律賦權和話語生產方面的專業服務,並憑藉精幹的職業素養躋身於“達沃斯階層”的精英俱樂部中。由於民族國家邊界控制的失效和全球化的利益驅動,大量移民和政治難民告別家園,成為追隨經濟機遇和尋求政治庇護的流浪者。這些人進入發達國家內部,尋求更好的生存和發展機會。在發達國家中的一些人看來,他們形成了搶奪就業機會、侵蝕社會凝聚力的外來部落,但被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驅逐所帶來的受害者身份又為他們在資本體系的核心地帶生存賦予了正當性。為了為移民群體提供必要的生存救濟,民族國家政府不得不承擔起更多的社會福利職能,從而同時承擔起巨富階層的財富管理者和移民階層的福利保障者的雙重角色。
對於民族國家的政治和社會結構的全面摧殘促使新保守主義逐漸放棄在經濟與社會之間妥協的中道政治,而不斷普世化為作為世界帝國的美國的意識形態。為了迎合巨富階層的經濟訴求和道德趣味,新保守主義開始放逐陣營內部的文化保守主義,為了安撫移民階層的道德焦慮,它開始吸納左翼的文化多元主義,從而形成一個超越左右的新同盟:
它在經濟上追求超級全球化,鼓吹基於競爭的市場邏輯和效益原則——“能者多勞,適者生存”;
它在政治上通過行政吸納政治,進而發展出專家治國的賢能政治,以滿足市場體系對於理性和效率的追求;
它在文化上發展出一種複合的普世主義文化,一方面鼓吹膚淺空洞的自由民主觀念以及由它引導和塑造的世界公民生活,另一方面鼓勵在自由民主體制內部尋求差異的多元文化主義,通過承認和保護少數族群的權利,來洗滌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原罪。
新保守主義相信秩序,認為只有依靠美國的絕對軍事力量,才能保證世界的安全,為此,他們促使美國政府擔當起“自由國際秩序”守衛者的角色,並通過積極的外交政策,來阻止核擴散和恐怖主義威脅等,從而實現普遍的自由、和平與繁榮。
▍民族保守主義理念及政策
後冷戰時代的進步願景讓人們沉浸在全球大同的美夢之中,並促成了新保守主義的全面勝利。但隨著事態的進展,人們很快發現,新保守主義的承諾都沒有兌現,全球化不僅沒有帶來普遍的繁榮,反而加劇了美國國內的經濟不平等;不僅沒有帶來普遍的自由民主,反而加速了美國國內政權的集權,並形成新的壓迫;不僅沒有實現普遍的和平,反而讓美國陷入到無休止的軍事衝突中。超級全球化締造了全球市場和世界經濟,卻又無法完全摧毀民族國家,建立真正的世界政府。這使得它無法在全球層面解決經濟失衡帶來的社會問題,為民族國家的社會保護埋下了伏筆,從而彰顯出全球化進程的悖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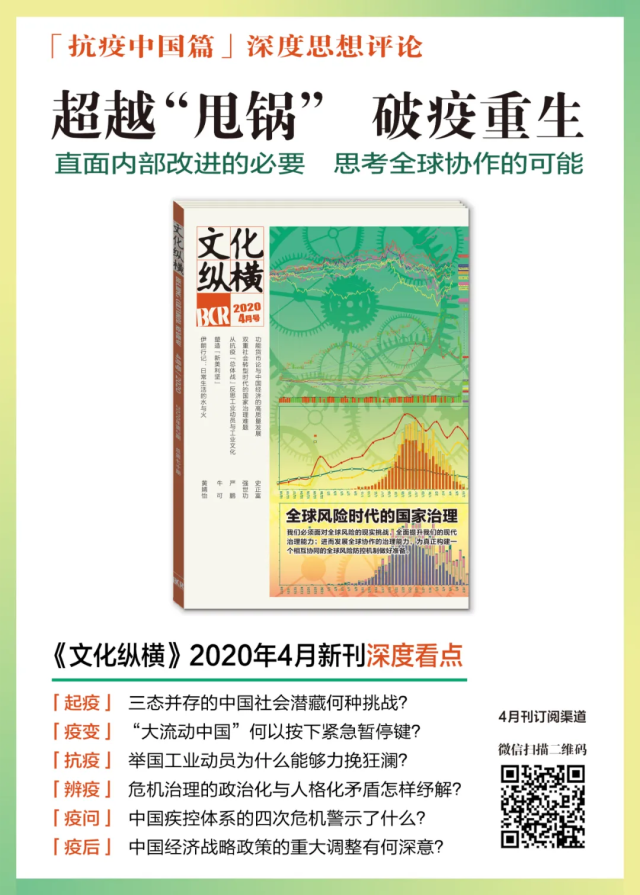
後冷戰時代美國新、舊保守主義的爭論充分暴露了經濟全球化與社會保護之間的張力,但由於彼時全球化尚處於盛期,美國的社會矛盾尚不足以全面激發舊保守主義的戰鬥力。2008年之後,隨著美式全球化弊病的全面凸顯,美國的階級鬥爭和種族衝突逐漸白熱化,最終促成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並帶動了另類右翼運動在美國的興起。作為一場雜亂運動的集合,它融合了歐美多個保守主義傳統,並具有更多的自發性和草根色彩。在特朗普就任總統的這三年之中,這場來自草根的群眾和思想運動漸漸成為保守派精英的政治自覺。為了為特朗普的政治戰略和政策提供觀念支撐,也為了發展更為系統連貫的保守主義原則,這些人開始承認戰後保守主義的脆弱聯盟已經瓦解,保守主義需要新的旗幟、理念和政策,它的核心就是為民族主義辯護,這在理念上表現為對世界主義共識的批判,在政策上表現為動用國家力量,全面介入經濟社會生活,重塑公民政治。
(一)民族保守主義的理念
- 批判世界主義共識
民族保守主義指出,新保守主義與文化多元主義結盟後,形成推動全球化的普世主義力量。相應地,被新保守主義放逐的文化保守主義勢力被迫通過民族國家內部的文化戰爭表達自己的不滿。普世主義與民族國家之間的張力所揭示的思想圖景超越了冷戰背景下的左右對立,形成了世界主義與本土主義的新對立。世界主義一方面承認普遍人性的價值,從而追求世界公民的最高力量,但另一方面提倡對合理差異的尊重,從而陷入到兩種價值的衝突之中。這種張力恰好同時滿足了巨富階層、移民階層以及憑藉專業知識充當這兩個階層的管理人角色的政治和文化精英的價值理想,從而成為跨國階層的思想共識。
由於打破了民族國家的邊界,世界主義者成為在任何地方(anywhere)生活的人,他們或者享受著精英教育所帶來的體面生活,或者為躲避戰火而被迫過著全球遷徙的流浪生活。與之相應對,本土主義者則是必須在某個地方(Somewhere)生活的人,他們的認同更為確定,往往是建立在對某片土地或某個群體的歸屬之上,因而對於快速轉變的時代和社會更容易感到不安和沮喪。當他們感到被自己國家和時代所拋棄的時候,往往會因為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落差而產生憤怒,抵制社會變遷。
對美國而言,前者主要是在美國東西沿海大城市生活的巨富階層和移民階層,後者則主要是生活在美國中部、體現著美國中產階級價值觀的白人勞工。這些憑藉二戰之後的經濟繁榮迅速躋身為美國中產階級的白人工人沒有受過多少教育,大多在中西部地區傳統的製造業行業或者大城市從事勞力和服務工作,由於經濟全球化帶動的產業轉移和人口流動,他們先是面臨去工業化帶來的失業壓力,然後又在再就業過程中面臨廉價移民的競爭和排擠,體面工作變成維持生計的廉價勞動。經濟處境惡化滋生一系列社會問題:家庭衰落、童年創傷、毒品氾濫、社區凋零、工作尊嚴喪失。
由於行政過程和專家治國壟斷了幾乎所有的決策過程,他們無法通過傳統的代議制表達自己的政治訴求,政治代表性的喪失使得他們成為沉默的大多數。而日益空洞和多元的普世主義又壓制了傳統基督教所能給予的心理慰藉的空間,從而帶來一種虛無的人生態度。在一種講求競爭和個人成就的精英文化理念的主導下,他們的失敗不再被視為國家和社會的責任,而是自己的無能。面對著日益窒息的生存空間,他們只能通過毒品、暴力和自殺尋求自我安慰和救贖。
在這個意義上,全球化不僅沒有實現人的徹底解放,反而製造了新的壓迫,它不但激化了全球範圍內的不平等,而且將這種不平等引入到美國內部,帶來發達國家內部的兩極分化。由於後殖民研究的強大力量,第三世界被經濟殖民的命運能夠通過文化抗爭的形式得到緩解,從而為它們進入歐美主流文化提供了空間。但全球化引發的內部殖民卻無論在經濟上還是話語上都被世界主義敘述所遮蓋。對那些被拋棄的本土白人而言,世界主義對陌生人的普遍尊重恰恰包含了對他們的忽視、遺忘甚至排斥,它對多元文化的寬容恰恰包含了對於本土白人文化的壓迫和歧視,充斥著精英的虛偽、矯情和做作,它的普遍性形成了一個新的鐵籠,帶來了一種新的獨裁和暴政統治,因而不啻為一種帝國建構的政治哲學,而它以自由之名所施加給世界的不寬容和暴力使得它成為一種新形式的帝國主義,從而為 “中部美國激進主義”(Middle American Radicals,MARS)的泛起提供了土壤。
- 為民族主義辯護
隨著保守主義向世界主義的演化,一個本來旨在保存美國社會文化價值和生活方式的理念發展為一個旨在發動全球性“革命”的思想理念。在美國“改造”世界的過程中,世界也在改造著美國,到最後美國文化的精髓蛻變為一個空洞的普世主義外殼,它遮蔽了文明之間的差異、公民與外國人之間的差異,甚至男人與女人之間的差異,大同世界成為西方社會的警鐘和喪鐘。為了讓美國從全球化的枷鎖中“解放”出來,更是為了“拯救”西方文明瀕於崩潰的命運,民族保守主義祭出了民族主義的大旗,試圖從新的政治囚籠中實現解放。
在這些人看來,民族主義的優越性可以從自然、歷史和當代政治三個維度予以解釋。從自然的維度看,民族是人類自然感情的載體,是人類認知和感情的制度體現,民族構成人類群體活動的自然場所,反對它就是反對人類本性。歷史地看,民族主義是最好的政治秩序理念,它是古以色列人在出埃及尋找神的應許之地的艱難路途中,發展出的一種心靈的力量。它之所以被人誤解,源于二戰期間納粹政權的歷史污點。由於納粹德國的歷史暴行,人們對民族主義產生一種深刻的恐懼,從而在二戰之後力圖通過自由主義和全球化來消除民族主義產生的土壤。但事實上,納粹的罪行不是民族主義帶來的,而恰恰是因為沒有堅持民族主義的政治原則,“儘管德國國家/民族社會黨(German National Socialist party,也即俗稱的“納粹黨”)掛著‘民族的’頭銜,希特勒絕不是民族主義的主張者。為了取代民族國家秩序,他從德國第一帝國受到啟示,試圖建立一個第三帝國”,從而走向了對外擴張征服的帝國主義道路。因此,納粹的歷史不僅沒有駁斥,反而更加確鑿地證明了民族主義的歷史價值。
只有意識到這一點,才能理解當代西方的民族大覺醒跟壓制少數族裔或者入侵國外領土沒有關係,而是對於現代民族國家的失敗和弱勢的一種反動,它來源於政治和社會制度的衰落,因而是防禦性的。在美國,民族主義認為,聯邦政府放棄了基本的看護職責,從而破壞了多數公民的信任和感情。它沒有確保邊界安全,沒有為管理和同化移民提供必要的手段和措施;它將立法權授予國外組織、國際機構和國內的官僚階級,對於公民的利益和價值缺乏照顧;它默認甚至積極促進了民族的碎片化,從而分化出種族、宗教和其他多種群體,並且顧此失彼。
民族保守主義者的民族主義立場非常微妙,要理解它,關鍵在於區分三種民族主義立場:
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大多數堅持信經民族主義(Creedal Nationalism)的看法,它將國家認同理解為一些抽象的政治原則,具體到美國就是人權、財產權、法治、資本主義等觀念,一個人只要宣告忠誠於這些信條,就能夠成為美國民族的構成部分。這些信條就如同宗教中的教義那樣,構成世俗主義者的政治信仰。極右翼的民族主義多從血緣和種族出發,認為美國民族主義的核心是白人血統。在民族保守主義看來,第一種立場太膚淺,在建構國家認同、組織共同行動方面不夠深刻和有力量,而第二種立場又太極端,很難為日益多元的美國社會所接受。作為一種折中,他們認為一種健康的民族主義力量必須堅持民族構成的文化因素,但又不能讓它泛化為白人種族主義。美國的民族理念不是幾條抽象的原則,不是只要讀懂和理解了這幾條原則就能消除文化融合的障礙,但也不是憑藉血緣維繫的生理規則,而是在代際之間傳承、在人際交往中塑造出的一種文化意識。要獲得這種文化意識,就必須在真實的美國大地上,在美國家庭和社會的紐帶中,吸收一種屬靈的神秘力量,並通過它的啟示,來完成自己身份的轉化和皈依。
(二)民族保守主義的政策導向
將民族主義從它的歷史污點中解脫出來,承認它的正面價值,目的是為了重建被全球化所撕裂的美國社會和政治制度,讓美國回歸民族國家的政治原則,它對內要求用國家干預取代自由放任主義,通過對困難群眾的幫扶,再造公民政治的社會基礎,對外要求放棄陷入軍事衝突的帝國冒險,回歸以現實主義為基準的外交政策。其具體內容可概述如下。
- 產業政策
回歸民族國家,首先要樹立國家相對於經濟全球化力量的自主性,從而讓它有能力保護本國的經濟和社會制度。經濟重建要求發揮政府的能動作用,不再放任市場機制的全球配置能力,而是通過積極的政策引導,實現全球產業鏈的重新佈局,通過美國的產業復興,解決美國公民的就業問題,通過幫助公民保持生活獨立,讓他們有能力撫養家庭、參與社區、自由選擇。由於美國主流保守主義都不贊同積極政府的主張,民族保守主義的這一倡議在保守主義內部引發了一場到底是要自由市場還是要產業政策的大辯論。
“法律與自由”網站編輯理查·雷因施(Richard Reinsch)信奉哈耶克主義,相信市場萬能,認為產業政策不僅有悖於美國的立國精神,而且將導致美國更加貧困。他指出,美國的憲法精神就是商業精神,國父們將財富視為勞動的結果,而不是國家授予的恩惠和特權,儘管財富的生產和創造需要國家提供的規則保障,但它最終將在市場原則的驅使下,在企業家精神的激勵下,從國內市場走向國際貿易,以便追求要素的自然流動,從而實現財富的最大化。在此基礎上,理查反對經濟民族主義者的論斷,他們認為美國的社會問題只能通過回歸製造業加以解決,為此要通過關稅和其他保護措施來干預市場。他認為,民族主義的貿易政策只會讓美國變得更加貧困,美國服務業創造的新就業機會足以消化過剩的失業人口,回歸製造業的口號混淆了美國真正的問題所在。根據聖路易斯聯邦儲備銀行(St. Louis Federal Reserve)的資料,從1953年至2015年間,美國製造業在名義GDP中的比重一直在下降,但在實際GDP中的比重卻一直很穩定,這意味著在過去70年間,美國製造業一直跟隨美國經濟保持同步增長。其中的原因是,隨著自動化設備的引入,美國逐漸淘汰了低技術含量的勞動密集型製造業,這樣做雖然增加了失業率,但是提高了生產效率,優化了美國的資源和要素配置。
由此可見,美國就業流失的原因應該歸咎於技術改進,而不是貿易政策。由於美國製造業的生產效率較高,通過關稅或者其他干預措施人為地實現製造業回流,違背了生產要素的流動規律,將不利於生產效率的最優配置。更糟糕的是,美國從中國進口的一半以上產品都被投入到國內生產流程之中,這些關稅成本將被使用這些產品的美國本土企業負擔,並最終被轉嫁到美國國內消費者頭上。美國工人階級是自由貿易的最大受惠者,因為他們的絕大部分收入都被用於購買衣食住行等基本消費品,關稅提高後,他們不得不承擔這些額外的成本。最終的後果就是,保護主義讓美國人變得更加貧困了。
歐倫·卡斯(Oren Cass)認為,美國應該採取產業政策。他指出,市場經濟不會自動實現要素的最佳配置,如果遵循經濟學理論,將製造業全部轉移,最終將摧毀國家經濟的根基。為說明製造業對於經濟的重要性,歐倫羅列了三個層次的理由。第一,如果決策者只關心分配結果,那麼他只需要對科技和金融領域從業者徵稅,然後通過政府的再分配措施即可實現其想要的結果。但如果他認為每個人、家庭和社區都應為社會貢獻生產價值,那麼國家經濟就必須為不同地域和不同能力的就業者提供就業機會,通過創造一個健康的勞動力市場來滿足社會的長期需要。第二,製造業對於經濟的長期健康發展更為重要。包括傳統製造業、資源提煉、能源生產、農業、建築業等在內的製造業提供了穩定、報酬豐厚的就業機會,尤其是對那些沒有受過正規教育的人而言。因此,如果一個社區將製造業轉移走,它將失去可進行對外交換的生產物品,從而陷入資源枯竭,最終走向生存性危機。第三,製造業對於完整供應鏈不可或缺,並在生產和創新互動中起著關鍵作用。有一種謬見認為,創新和生產構成供應鏈的兩個環節,可以各自依其要素稟賦尋求最優的資源配置區域。但在歐倫看來,二者不能輕易剝離,技術創新只有依託完整的產業鏈才有可能保持活躍,沒有製造業支撐的技術創新必將成為無源之水。
歐倫認為,為扭轉不平衡產業結構以及解決要害部門的投資不足問題,美國政府應該模仿德國和日本政府,制定產業政策,具體方案包括資助基礎科學研究;資助先進材料、機器人等應用科學的研究;通過補貼和特定機構為私營企業的研發和商業化提供支持;強化職業教育,為高等教育中的工程學等學科提供更多支援;增加基礎設施投資;簡化規制負擔,為能夠增加工業能力的專案提供快速審批通道;為生產性勞務所獲得的利潤提供稅收優惠;瘋狂報復破壞市場競爭的重商主義國家;對美國資產的境外所得徵稅,以便使美國商品更具吸引力;對諸如通訊業等涉及關鍵性供應鏈的行業強制提高國產化率等。
由於美國政治體制的局限,政府決策難免受制於政治過程而無法趨於完美,決策過程會被利益集團捕獲,產業政策也存在扭曲市場的風險。但歐倫將實行產業政策視為改變現狀的一個機會。在他看來,在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的教唆之下,中美日益形成一個互補的自由貿易聯合體,並因此嚴重扭曲了美國國內市場,被拋棄的美國工人被迫孤獨地與貧困搏鬥。為拯救這些人的命運,他呼籲經濟民族主義者們挺身而出,通過大膽地干預市場,為美國工人的利益而戰。
歐倫在其著作《工人的過去和未來:美國工業復興願景》中對該問題做了進一步闡明,指出產業政策的實質涉及美國經濟增長模式轉型問題。他指出,美國戰後經濟思想的兩個支柱是做大蛋糕、增強消費,這具體落實為以私營經濟為驅動的經濟增長和以福利國家為保障的社會再分配措施,其消極影響是忽略了對生產者的培訓和教育,從而不利於發展健康的勞動力市場和維持長期經濟穩定。在此背景下,產業政策被視為政府調整經濟增長模式,即從以債務驅動或者以消費為主導的經濟模式回歸以工人為中心的經濟增長模式的必要之舉。
- 社會和移民政策
經濟重建的目的是為了社會重建,它一方面要求糾正經濟不平等產生的各種社會問題,另一方面要求抵抗各種亞文化對於傳統基督教文化的侵蝕,通過提高社會凝聚力,塑造有歸屬感的政治共同體和公民政治,通過重建家庭、社區、國家環環相扣的同心圓結構,實現道德秩序在多元與凝聚、動態與穩定之間的平衡,打造個人主義時代下的新社會契約。
這一初衷對內體現為兩個方面,其一是放棄政府在文化事務上的中立角色,通過積極參與文化戰爭,反擊自由派對於美國社會的毒害;其二是通過各項積極的社會政策來醫治美國的社會弊病。就前者來說,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彼得·蒂爾(Peter Thiel)對左翼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確的批評,比較激進的是宗教右翼分子蘇赫拉布·阿馬裡(Sohrab Ahmari) 提出的取消政教分離的主張,他認為自由派敵人將精英機構變成了自由放任主義者和異教徒的大本營,在應對這些敵人時,以德報怨不是正確的應對態度,以直報怨才是更可取的路徑,為此,他主張拋棄國家在宗教事務上的中立態度,積極利用國家力量來擊敗自由派敵人。就後者來說,民族保守主義者們認為,國家的作用是要促進美國社會的健康和和諧,他們要求利用國家的力量來應對毒品危機、青少年沉溺色情的問題,並解決美國產業空心化、城鎮人口流失帶來的社會問題。他們的政策主張包括帶薪家事假(paid family leave)、兒童稅收抵免(child tax credit)、聯邦資助的孕期護理和產前護理、多子家庭減免所得稅等一系列措施。
民族保守主義者在對外方面的主張主要涉及移民問題。他們認為,美國需要一種更加現實主義的移民政策,從而能夠保存自己作為西方國家和第一世界國家的特質。在這方面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來自賓夕法尼亞大學法學院教授埃米·瓦克斯(Amy Wax)。在其近期發表的相關論文中,她從民族主義立場為限制移民提供了系統辯護。她指出,美國需要更加平衡和成熟的移民改革方案,並將它轉化為具體的法律和政策,實現這一點要求將移民話題從左翼的道德話語裹挾中解脫出來,認真考慮美國本土白人的民族主義感情。
瓦克斯從經濟因素和文化因素看待這種民族主義感情。經濟因素包括兩個方面。第一,移民政策的後果並不是皆大歡喜,而是有輸有贏,它的後果並沒有被平均分配。精英階層是移民政策的受益者,因為大規模湧入的移民使得美國生產的產品和提供的服務更加便宜。相應地,底層的普通美國工人成為移民政策的受害者。大量廉價移民的湧入迫使美國本土的適齡勞動力離開了就業市場,由於來自拉丁美洲和亞洲的移民更願意從事那些本地人不願意從事的工作,所以他們為雇主所青睞,並替換了那些受過更好教育的美國人。第二,由於教育程度較低的移民佔用了大量的政府服務和福利,因而為美國納稅人額外增添了很多負擔,這些花費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移民帶來的收益。

文化因素主要指移民的政治認同問題。在這方面,瓦克斯認同文化差異型民族主義的觀點,認為抽象的信條無法實現對移民的真正吸納,如果再承認他們追求差異的權利,他們將成為美國社會難以消化的病毒,從而侵蝕美國健康的制度和公民體系,加速美國社會的極化,因而是不道德的。
考慮到這些經濟和社會條件,瓦克斯認為將移民的數量和增長速度維持在較低水準上是比較穩妥的方案。根據這一邏輯,對於移民就要進行選擇性接納。來自西方世界或者第一世界的移民共用著美國的價值觀念和文化傳統,因此應該受到歡迎;大部分來自第三世界的移民要麼不理解,要麼不認同美國的價值觀,這些人很難被同化。他們獲准進入美國後,將把原生社會的腐敗制度、無能政府、無法無天的行為和社會惡習帶進美國,長久下去將顛覆美國的公民道德和社會團結。
- 外交政策
由於理論與現實、外交與內政路線之間的差異,民族保守主義圍繞外交政策的討論具有模糊性和不確定性。我們可以從哈紮尼的理論視角出發,對該問題展開分析。他在其著作中建構了兩種世界秩序的願景,一種是民族國家秩序,一種是帝國秩序。哈紮尼將清教徒建構的秩序置於後羅馬帝國的政治空間中,將其視為歐洲民族國家的原型,將洛克以降的自由主義學者建構的秩序視為帝國秩序,指出二者的差別在於,前者承認政體的多元性,奉行尊重主權、不對外擴張的外交政策,後者奉行自由意識形態,並為了自己的大同理想,不惜干涉它國內政。
從這一視角出發,作為反抗自由帝國的一種努力,民族保守主義的外交路線應該是保護美國人民的安全、主權和獨立,這意味著美國政府要結束在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亞、敘利亞等地的帝國冒險行動,放逐任何參與這項事業的共和黨人,彈劾對國會的宣戰權視而不見的總統,將駐外軍隊召回美國,確保邊境安全,重建美國。這使得民族保守主義的外交路線帶有孤立主義的色彩。
但另一方面,放棄自由霸權的理想主義,也意味著回歸美國外交的現實主義傳統,它要求不再從理念出發,而是基於對國家利益的判斷,實施多樣的外交政策,因而它既可能是防禦性的,也可能是進攻性的。放棄了道德主義的偽裝後,民族主義有時候會變得更加赤裸和殘酷。從美國政府和公共輿論關於中美貿易戰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真切地嗅到它的火藥味。從民族主義視角出發,關稅戰當然是民族保守主義反抗跨國公司的階級戰爭,它試圖通過人為抬高跨國企業的生產成本,促進資本回流,加速本土製造業回歸,從而解決白人的就業問題。但與此同時,關稅戰也是一場國家安全方面的較量,當美國的國家利益和霸權地位受到威脅的時候,民族保守主義者壓制的爪牙可能變得更為猙獰。這也意味著,民族國家秩序看起來很美,但它並不太平,民族主義和世界主義到底誰是通向永久和平的通道,答案仍然是開放性的。
▍結論
二戰期間民族國家之間的殘酷鬥爭留給人們的教訓,加上冷戰塑造的普世化意識形態遺產,共同造就了後冷戰時代的全球化進程,它試圖通過對民族國家秩序的全面改造,實現普遍的自由、和平與繁榮。作為一種觀念話語,美國當代保守主義始終與這場運動保持同步,為了對抗蘇聯,它在冷戰時期發展出系統的新保守主義的觀念,並在後冷戰時代發展為主導美國政黨和全球政治的思想觀念。全球化自身包含的悖論最終引發了民族國家的反抗,它在美國表現為保守主義思想陣營的內部分裂,並分化出民族保守主義的保守主義立場。
民族保守主義在理念上擁護民族主義,在政策上主張國家干預,從而全面重建民族國家的政治秩序。它既是一場觀念革新,也是一場政治運動,試圖通過對保守主義理念的改造,為特朗普執政提供系統的思想引導。而作為一種回應,特朗普在總統就職典禮上怒斥全球化造成的“美國浩劫”、驕傲地宣傳自己的“民族主義”立場、在聯合國大會上為國家主權和民族主義所作的辯護都毫無疑問地展現著民族保守主義觀念的影響力。可以說,這場思想運動已經內化為特朗普的執政理念,並將對美國保守主義的發展和共和黨的綱領調整帶來深遠影響。
另一方面,美國保守主義的民族主義轉向並非是一個僅限於保守主義陣營的議題,而是反映了美國政治的一般走向。比如,2020年美國大選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伊莉莎白·沃倫(Elizabeth Warren)所提出的經濟愛國主義(economic patriotism),在內容上就與民族保守主義的立場高度重合。這意味著,為了解決全球化給美國造成的財富分化、民主赤字、國家認同危機,重建民族國家將成為美國政治的當務之急,因而民族主義政治可能成為一個跨黨派的共識性議題,民族主義復興將成為影響全球政治走向的深遠議題。
新共識的形成使得民族保守主義超越了簡單的“反動懷舊症”(reactionary nostalgia),而是蘊含著一股革命、解放的力量,它通過將自己的訴求建立在對自由霸權的幻滅之上,並試圖通過對它的壓迫性後果的反抗,來實現美國人民的整體自由。但這仍不能抹殺保守主義的民族主義立場本身的曖昧性,這種曖昧性鮮明地體現在它對“民族”的獨特理解方式上。它批判經濟不平等,主張社會公正,因而有社會主義色彩;它批判政治官僚化,主張人民的權利,因而有民粹的成分;它批判過度個人主義的美國文化,主張集體認同。這一認同鏈條從家庭出發,經過社區到達國家/民族,環環相扣,憑藉其深刻的文化內涵維持其完整性。這種部分與整體的統一,以及對同一性的追求,最終將落腳于美國的白人基督教文化。
在這個意義上講,民族保守主義的復興反映的是美國乃至西方文化所面臨的一場生存危機。它當然有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訴求,但它最深刻的地方是期待一場靈魂救贖,從而將西方從物質主義和科技主義的精神荒漠中拯救出來,從資本主義的平庸生活中拯救出來,從歷史終結的“末人”世代中拯救出來。當歷史從目的論結構中解脫之後,它重新開始了古典世代的大循環,在解放人的同時,也把人重新拖入與時間的緊張關係中。為了緩和這種緊張關係,民族保守主義重建了一個虛假的“人民”的精神偶像,並甘願通過這種集體性的狂歡甚至犧牲來追尋世俗生活的神聖意義。或許,它最終是想製造一個新的幽靈,它通過返回過去,構造一個面向未來的新圖景,從而通過超越時間達至永恆。

— 《文化縱橫》4月刊目錄 —
▍特稿
01.功能貨幣論與中國經濟的高品質發展
史正富
中國經過約 10年的經濟增速下行,持續地努力化解前期形成的種種失衡;時至今日,轉入新增長通道的機會已經出現。有錢:因為儲蓄率還處於高位;有物:巨大的過剩產能和迅速擴大產能的超強能力;有市場需求:大約10億農民及低收入階層進入中等收入水準的巨大消費潛力;有投資機會:五大發展理念中蘊含的基礎性戰略性資產積累以及富有活力的民間投資。
▍封面選題:全球風險時代的國家治理
在這場全球性公共衛生危機中,中國政府率先以強有力的防控手段,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在3月底逐漸控制了國內的疫情。中國的疫情防控,既保障了中國人民的生命健康和中國經濟的發展格局,也為世界各國的防疫爭取了寶貴的時間。但是,我們一方面要看到社會主義舉國體制在這場防疫人民戰爭中發揮的巨大功效;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應對這種現代社會突發風險的過程中,當前中國的治理體系仍然存在著一定的結構性短板。
02.雙重社會轉型時代的國家治理難題|強世功
03.從抗疫“總體戰”反思工業動員與工業文化|嚴 鵬
04. 高流動性與低組織化——中國社會危機治理的雙重挑戰|劉炳輝
05. 公共衛生專業化治理如何可能?——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談起|曹東勃、葉子輝
06. 預防必須為主——中國疾控體系的四次危機及其教訓|王紹光
▍歷史觀
07.商人治國——從貿易到戰爭的邏輯|殷之光
▍世界觀
08.塑造“新美利堅”——美國現代國家構建的社會歷史根基|牛 可
美國世界地位的升進是19世紀末以來最重大的世界歷史事態之一,其中的核心環節正是美國國家(state)的轉型和擴張——這也經常被表述為美國大政府的創生。冷戰史家也認為,美國之所以打贏冷戰,大可以歸因於它的“國家”的成功變革。這本是一種常識論斷。但“二戰”以後美國社會科學和歷史學的主流卻是:美國國家的研究議題,一直被政府、政治體系和政策過程之類的議題所替代和擠壓,也被廣為流行的社會中心觀和反精英主義所消解或遮蔽。
09.美國工會怎麼了?|閻 天
▍後發國家發展道路
10.國家資本主義在摩洛哥|張玉友
國家干預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摩洛哥發展模式兩大核心要素。在摩洛哥語境下,國家更多的是指代以國王代表的王室集團。在發展模式上,國王哈桑二世在獨立後就選擇了受西方國家認可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同時通過特權階層充分干預經濟活動,集中國家有限資源發展經濟。進入21世紀,隨著國際資本的湧入和全球化的深入,穆罕默德六世將國家資本主義模式擴大化,採取了限制性的自由化改革,創造了大量國家冠軍企業來管理國家經濟。
11.伊朗行記:日常生活的水與火|黃婧怡
▍新國史
12. 從“猓猓”到“彝族”——龍雲身份變遷的歷史過程與現代啟示|趙 崢
在“現代國家”的眼光和視野之下,“民族”不僅僅是用來編戶齊民、徵收賦稅的輔助性符號,更是對民眾進行組織、對社會進行改造的重要動員工具,族群身份也勢必要隨之經歷由模糊到清晰、由流動到固化、由個人選擇到國家設定的轉變歷程。而中國對現代國家觀念衝擊的吸收和轉化,至今仍處於進行時。龍雲的族群身份與角色變遷,正可看作這一歷史進程的一個縮影。
▍觀察
13. 文明對話應在開放的語境下展開——對“一帶一路”沿線文化交流的反思|管世琳
文明對話必須在開放的語境下展開,不能讓維護本土意識和自我認同的初心走向狹隘乃至封閉。那樣的話,文明對話就變成了徒有其表的自說自話,人文交流也將陷入“內卷化”的泥淖,重蹈西方的覆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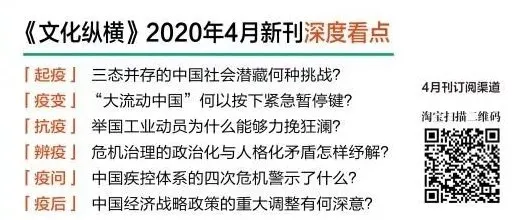
本文原發表於《國外理論動態》2020年第1期,轉自“法意讀書”,原題為“美國當代保守主義的民族主義轉向”。圖片來源於網路,如有侵權,敬請聯繫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

(訂閱《文化縱橫》2020年雜誌,享半年免費暢讀所有已出版雜誌電子版VIP,僅剩最後200席)
♦ 專文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