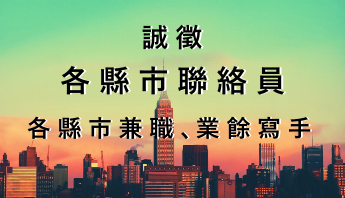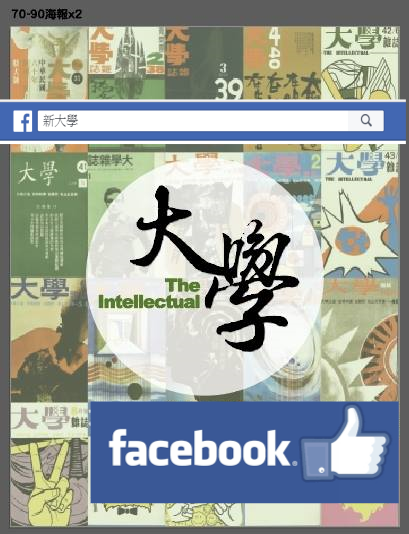♦ 本篇文章轉載自 90號茶室。若有侵害著作權,請速告知,我們將盡速移除 ♦
2025/3/19

近日,75歲的橋水基金的創辦人雷·達利歐,接受美國著名主持人塔克·卡爾森採訪,引起不少關注。兩個小時不緊不慢的對話,看似雲淡風輕,卻藏著這位金融巨頭的真知灼見,和一些深層思考。
例如,他認為美國事實已經在「內戰」中;美國的製造業已經永遠追不上中國;AI可能是人類史上最偉大的發明,也可能是我們自毀的扳機......現將訪談的主要內容,分享給感興趣的朋友。
一、數據裡的“隱密內戰”
達利歐一開口,就丟了個重磅說法:美國正打著一場「隱密的內戰」。不是戰場上硝煙滾滾,你死我活那種,而是經濟、社會、政治裂得越來越開的那種。
為證明自己不是危言聳聽,他直接甩數據:美國貧富差距快趕上100年前最糟時候,底層一半的人,財富加起來還不到全國的2%,而最頂上那1%的人,掌握著30%多的錢。他打了個比方:如果把美國經濟比喻成一艘船,現在的情況是「船頭在天堂,船尾在地獄」。
達利歐認為,比這更可怕的是經濟分化正在轉化成政治和社會的對立。他引用研究數據指出,美國兩黨選民的地理分佈、生活方式甚至消費習慣都在加速分化——共和黨支持者更傾向鄉村和傳統產業,民主黨支持者則集中在城市和高科技區域。這種「地域隔離」讓雙方的對話越來越少,偏見卻越來越多。
他也提到一項驚人的統計數據:超過40%的美國人表示,他們不願意與支持對立黨派的人做鄰居。這種「部落化」趨勢,讓達利歐得出結論:美國社會的凝聚力正在崩塌,而這正是內戰的溫床。
達利歐進一步強調,這場「內戰」的根源並非單純的政治分歧,而是經濟不平等與文化衝突疊加的結果。他用歷史類比來加深印象:
今天的美國,與19世紀內戰前夕的南北對立有驚人的相似之處——經濟結構的分裂(當時是工業北VS農業南,現在是科技精英VS傳統工人),再加上意識形態的極端化。唯一的區別是,今天的戰場從田野變成了網路和選票。

二、極化從何而來?全球化的代價與中國的崛起
那麼,這種撕裂是如何發生的呢?達利歐沒有簡單歸咎於某個領導人或黨派,而是從更廣闊的視角出發,剖析了全球化、技術和政策失衡的疊加效應。
首先是全球化帶來的衝擊;達利歐指出,過去幾十年,美國企業將製造業大規模外包到成本較低的國家,導致大量藍領階級失去生計。
他給出一組數據:1970年代,美國製造業佔就業比例接近25%,如今已不足10%。這些工人並沒有被新經濟吸收,而是被拋在了後面,憤怒和無力感隨之滋生。同時,全球化讓資本家和高技能族群賺得盆滿缽滿,財富進一步向頂樓集中。
但達利歐的目光不僅停留在美國內部,還將視線轉向了中國。“美國在我們有生之年永遠無法在製造業上趕上中國,”他飽含無奈地說 “中國控制著全球33%的製造業——比美國、歐洲和日本的總和還要多。”
他列舉了中國在機器人技術、晶片生產和人工智慧應用上的主導地位,強調這不僅是數量上的優勢,而是技術與規模的全面領先。他提到,中國在半導體供應鏈上的掌控讓美國望塵莫及,而這種差距正在重塑全球經濟格局。換言之,達利歐的一個核心觀點就是,全球化不僅掏空了美國的工業基礎,也讓中國成為了新的製造業心臟,這對美國來講是可悲的,但又無可奈何。
科技進步則是另一個重要推手;網路和社群媒體的崛起讓人們困在「資訊繭房」中,演算法推薦讓保守派和自由派各自封閉在自己的世界裡。達利歐指出,這種「回音室效應」放大了情緒化的傳播,憤怒和恐懼比理性更容易在網路上擴散。而AI的興起,則讓這種分化變得更複雜、更難以應付。
最後是政策的失衡;達利歐批評美國政府在教育、稅收和福利上的失策。他提到,美國公立教育的品質差距正在拉大,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幾乎沒有向上流動的機會;稅收政策則持續偏向富人,導致社會流動性跌至已開發國家下游。
他提到一個令人震驚的統計數據:60%的美國人的閱讀程度低於六年級。僅有300 萬人(美國人口為3.3 億)在推動所有技術創新。這一教育差距正在造成前所未有的財富差距。這些都表明,美國的社會流動指數——即「美國夢」的實現可能性,已遠不如從前。

三、美國還有啥?創新與大學的命懸一線
製造業不行了,美國還有啥拿得出手?達利歐認為,創新和頂尖大學算是美國的最後兩張王牌。但同時達利歐指出,即使是這兩個最後的優勢,也同樣藏著令人不安的隱患:
美國一半的頂尖創新者並不是本土培養的,而是來自世界各地、在美國大學深造的外國人才。這些人帶來了新的思想和技術,但隨著全球競爭加劇,這種優勢正在動搖。
更令人擔憂的是,AI的崛起可能連這最後一塊陣地都無法保住。達利歐談到,人工智慧已經能夠達到博士級的知識儲備,甚至在某些領域超越人類專家。他舉例說,AI不僅能分析法律文件、診斷疾病,還能創作藝術作品。這種技術飛躍意味著,美國依賴大學培養高端人才的模式可能很快就會過時。 「如果AI能自己學習並創新,我們還能靠什麼保持領先?」達利歐的語氣中帶著一絲憂慮。
他進一步分析,這種趨勢對中國有利而對美國不利。中國不僅在製造業佔據主導,還在AI應用和晶片生產上投入大量資金。相較之下,美國的創新生態雖然仍強大,但內部分裂和資源分配不均正在削弱其潛力。

四、AI是救命稻草還是火上加油?
如果說經濟分化和極化是眼前的危機,那麼AI的崛起則是達利歐眼中的未來變數。他在訪談中花了大量時間探討AI的影響。
達利歐預測,AI將在未來十年徹底改變生產力和就業結構。他提到一項研究:到2030年,全球約20%的工作可能被AI取代,而美國可能首當其衝,因為它既是AI技術的先鋒,也是貧富差距最嚴重的國家之一。 AI不僅能取代流水線工人,還能入侵高端領域──律師、醫生甚至藝術家都可能面臨威脅。
當然,這麼宏大的話題,他怎麼會不提中國呢,達利歐認為中國在AI研發上的追趕,以及應用上的領先地位(比如智慧製造和機器人技術),已經讓美國感到非常大的壓力。如果繼續以現在的速度縮小雙方的技術差距的,「攻守互換」的場景,也許不久就能看到。
達利歐對AI也並非只抱持負面看法。他認為,如果政策得當,AI帶來的生產力提升可以為社會創造巨大財富,用於教育、醫療和基礎設施,從而緩解不平等。但要實現這一點,必須有一個必要前提:政府透過「財富再分配」政策,確保AI的好處惠及所有人,而不是只集中在少數科技巨頭手中。
但如果做不到這一點,AI的紅利繼續被少數人壟斷,而底層民眾的生計被新技術侵蝕,現有的社會裂痕將進一步擴大,甚至引發暴力衝突。「AI可能是人類史上最偉大的發明,也可能是我們自毀的扳機」這是達利歐對AI的一個「雙面刃」式的定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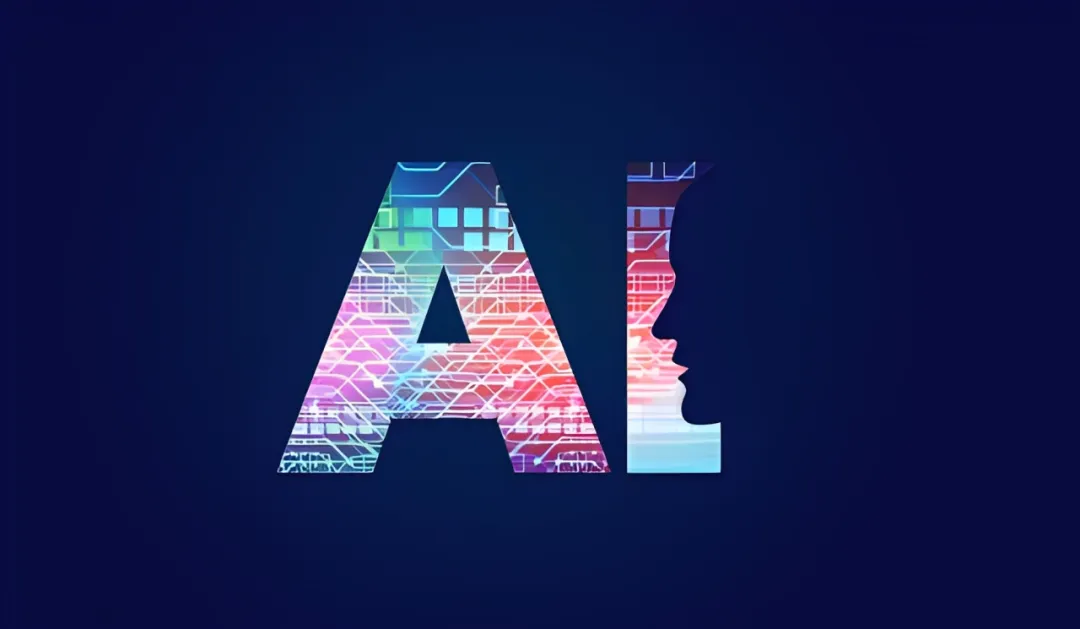
五、幸福到底是什麼?
在訪談接近尾聲時,主持人拋出了一個不新鮮的哲學問題:「什麼才是真正的幸福?」達利歐的回答是社群(連結)。
他認為,在基本需求之外,更多的金錢和權力與健康或幸福之間並沒有相關性。但是當人們有強烈的社交聯繫時,一切都會變得更好。因此,擁有強大社區的國家始終顯示出更高的幸福感,無論其GDP如何,並以印尼並不算富裕,但卻在全球幸福指數中排名第二為例,佐證自己的看法。
達利歐坦言,自己見過太多億萬富翁,他們帳戶裡有無數個零,卻依然感到空虛。在他看來,美國社會的危機,歸根究底就是因為人與人之間連結的斷裂。

最後,達利歐認為,我們正在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變革和不確定性時代。舊的規則將不再適用。這將影響將不可避免的影響甚至顛覆現有的傳統文化、社會機構,經濟市場等各個領域。
至於如何應對這些情況,他開出的「藥方」是,停止那些無謂的爭吵,開始把心思放在重建本地社區。因為在激烈變革的時代,你的人際關係會遠比你的資源更重要。
達利歐的這場採訪,主要是圍繞美國的現狀和未來而談的,但其實的某些描述和現狀,在我們國家是不是也存在類似的情況?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老先生的話也許能帶給我們一些啟發。
♦ 專文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