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0/8
宋楚瑜與張俊宏2020年6月4日對話錄
❖ ❖ ❖ ❖ ❖ ❖ ❖ ❖ ❖ ❖
策劃:環境基金會執行長黃晴琦(Jenny)、新大學網站總編輯何步正
訪談者:楊雨亭
紀錄:新大學網站執行編輯劉小文
時間:2020年6月4日下午3:30
地點:宋楚瑜辦公室,台北市仁愛路三段141號
❖ ❖ ❖ ❖ ❖ ❖ ❖ ❖ ❖ ❖
前言:
這一天宋楚瑜主席和張俊宏委員見面,正好是六四。我們談的主題是1990年3月間發生的大事:野百合學運中的民主改革。但是之前,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過世,國民黨內部經歷劇烈衝擊,到兩年以後,1990年3月,發生野百合學運,從此中華民國與台灣社會逐步由威權走入民主時代,這個戰後戲劇性的轉折點,其所影響到層面,不只是台灣,更是波濤湧上中國大地,進而輻射到全世界的政治文化生態中,至今猶餘波盪漾。這件事可以說是近代以來中國、台灣甚至於世界歷史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因為從威權政治到民主政治自我轉型的成功範例不多。而之後不久,台灣社會內部開始產生族群矛盾與統獨衝突,和1988年1月蔣經國過世後國民黨內部的分裂以及1990年3月份開始的學運和隨之而起的國民黨主流派與民進黨的合流而產生的民主化過程有沒有關係,多年來缺乏對此的研究。在野百合學運中,學生和民進黨之間發生了什麼事情?一般對此情況的了解也不多。
1990年3月16日至3月22日在台北進行了一系列的學生運動,數千名來自台灣各地的大學生集結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上靜坐,提出「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訂定政經改革時間表」等訴求。這是中華民國遷臺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的學生運動。期間,時任中華民國總統的李登輝運用情勢發展以及民進黨的合作,在並沒有得到國民黨高層以及普遍黨員與幹部的共識下,進行對學生與反對黨的承諾,召開國是會議,隨後於1991年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結束「萬年國會」,使台灣一方面進入了民主化的階段,另一方面,並之而來的國民黨黨內紛爭、台灣政治文化選舉化、統獨族群對立、兩岸關係起伏以及種種社會運動包括同志平權運動的發展,都不是當年的運動與政治參與者以及老百姓們所能預見的。
當年,張俊宏是階下囚出獄不久,宋楚瑜是當朝紅人,李登輝和黃信介二人聯手,在參與及運用學生運動中,由國民黨秘書長宋楚瑜與民進黨秘書長張俊宏的穿梭和折衝,鬆動了國民黨傳統政權的根基,決定了台灣政治改革的主軸,為下一階段的中華民國與台灣的政治發展,改裝與布置了新的舞台,開啟了台灣政治本土化路線以及民進黨的新政權時代。
1990年野百合學生運動中的學生如范雲、黃偉哲、鄭文燦、郭正亮、羅文嘉等人,在新時代中藉民進黨直接間接的提攜而登上舞台,並且逐級躋升政治新貴;其中由於學生運動的性質主要是反對國民黨,以至鮮少有國民黨的新人出現。由此,國民黨自野百合運動以後,開始日益在接班梯隊上產生斷層,原本對於中國的視野與理想愈加模糊,黨員和幹部志氣衰頹。而外省族群包括第二代中的許多人物,在政治氣候的變遷中懵懵懂懂,並且長期和本土文化與勢力脫節,對於自身的日益沒落,完全無計可施!
由宋楚瑜與張俊宏二人當年代表雙方上層進行幕後溝通的角色與功能,促成了一個「和平轉型」(相對於「和平演變」)的時代。用他們兩個人的結論說:「必須要有對話來取代對抗,但是對話必須要有對象,對象必須要有對策。」這對於今後的台灣內部、中國大陸內部、香港、以及兩岸關係,甚至和美國、日本、歐洲等國家之間的關係,都有相當的啟發意義。而當時在政治幕後,到底是如何地產生了如此一連串的變動,一般並不十分清楚。2020年6月4日下午開始的宋楚瑜與張俊宏會談,為當時的歷史起了部分解密的作用。
-- 楊雨亭,整理原稿於2020年10月初。

本文:
▍宋:從六四發生事情的角度來看,現在全世界最讓我們珍惜的地方就是台灣,但是台灣近年來越來越糟的新聞道德和水準,讓我們憂慮。今天《華爾街日報》頭版頭條,說美國現在全國不安,走在街上,尤其是在舊金山華人和有色人種的地方,大家覺得非常恐慌,不曉得會發生什麼事。而在全世界,晚上女性同胞走在街上最安全的地方之一就是臺灣,這麼好的一個包容的文化,具有世界觀,而且曉得人與人之間相處的道理,和我們的民主政治很有關係。我們兩個人(指宋楚瑜和張俊宏)原來是對立面,結果可以坐下來共同為臺灣創造民主,這一點請你把它記下來。
我今天很自豪的來說,臺灣有今天的民主是碰到兩個非常認真、有歷史觀的秘書長:一個是國民黨的秘書長,一個是民進黨的秘書長。如果那時候張俊宏是一個像現在我們所標榜的鷹派、不講道理的,兩個人各自堅持觀念,在一些特定的立場在尖銳對立,臺灣根本不可能有今天的民主。很多人並沒有重視當年的這個過程,所以今天我來做歷史見證。我們兩個人還有一個特色:不在外面吹噓,所以外界對幕後協調折衝的過程都不瞭解。沒有這些協調折衝,把意見向他們直屬的兩位主席溝通,我相信不會有我們今天民主政治的成功。我也必須要稱讚那個時候的李登輝先生和黃信介先生,都扮演了相當正面的角色。如果他們兩位都是不能溝通的,而是堅持己見的人,我相信後面的情況也不會有今天的結果。
六四這個事情是個導火線,給我們一些啟發。我們兩個人都和加州柏克萊大學有一段淵源,加州大學是美國一個非常自由化、開放的園地,我們倆都在那邊受過一些薰陶和啟發。今天國際上的大事是美國的兩位國防部長,現任的國防部長跟前任的國防部長公開指責美國的總統,尤其是前任的國防部長Mattis講得非常嚴重:「川普根本破壞了美國的憲法。」這就表示即使是美國,我們以前非常嚮往的民主導師的地位,在處理很多事情時,對於一些理念以及處理的技巧,以及對世界的狀況不很清楚,以美國的實力來講都會產生一些不好的情形。更何況在當年,國民黨以壓倒性的優勢、資源,長年累積起來黨政軍的實力,怎麼可能跟一個弱不禁風的反對黨合作,做出一些基本性的調整。前幾天八卦新聞一直再說經國先生的回憶錄,為什麼我對現在的新聞界頗有一些保留,就是把它變成八卦新聞在報導(黃清龍寫的《蔣經國日記揭密》,楊按)。如果我跟俊宏兩個人來描寫這件事情的話,角度可能就不太一樣,要從更高的層次來講。第一個他(黃清龍,楊按)最先寫的,就是蔣經國先生走的那天在常會發生的事情。經國先生的日記裡面明確地說他對於孔家很不以為然,這就是為什麼那天我會發難。俊宏說他一直在景福門前面看國民黨的黨部,看那天走進走出的人到底是怎麼樣的情形,有沒有做出什麼重要的決定。
▍張:那一段太精彩了。我一直在等待這個真相大白,後來完全沒有延續報導。在那個階段中,如果沒有你所扮演的勇敢的角色,不會有今天。

▍宋:經國先生的日記證實,經國先生對於孔家在介入臺灣未來發展的政局方向是負面的。而我能夠在那個時候,把經國先生真正交代要去做的事情能夠講出來,當時還引起很大的不同的反響。孔家就是指孔令侃,所以你去看看黃清龍所寫的孔令侃的角色。最近,包括周玉蔻每天都在講這件事,我沒有興趣去說到底小孩是誰生的,那個都不重要。對於天安門事情發生,我要講一句話:中國的未來不是靠美國來改變,你自己必須要找出你自己的生存之道和發展的道路。五四時中國是什麼樣子的狀況?中國是個戰勝國,竟然在巴黎和會中遭遇到那樣的情況,所以才有五四運動的發生,然後產生中國共產黨這樣的一個勢力。我們需要自己民族自覺,不要外國人要來幫你忙讓你改變。國民黨和臺灣目前的情況也是要自己思考該怎麼辦。在這個當中,經國先生和蔣夫人的一些嫌隙,我很明確的說蔣夫人晚年在臺灣幾乎不太接觸臺灣的報紙,她也不太管政務,大部分都是孔令侃在那邊寫這些東西,所以大部分的事情經國先生在他自己日記裡面很不以為然,但是他要維持黨內尊老敬賢的傳統,他不能夠跟夫人和他們這些人的關係被人講話。
經國先生走了之後,由孔令侃起草寫一封信給國民黨秘書長李煥先生和行政院院長俞國華,說暫緩不要由李登輝先生代理主席,但是我瞭解這根本就是假傳聖旨。這時候還沒到要開會的時候,關鍵最重要的時候,下午一點多鐘經國先生大去之後,這時候國民黨決定要開臨時常會,由俞國華先生擔任主席,在這時候他們說:「我們應該先去謁靈,還是先讓副總統宣誓就職?」我在旁邊咬耳朵,說:「應該依照憲法的程序先觀禮宣誓。」
▍張:你是當局者迷,你自己在那裡面,後來的發展你也不夠清楚。但是我是旁觀者,那整個場面中就是他(宋楚瑜,楊按)在轉動方向盤。經國先生的過世,我相信全世界至少擔心了十年,因為接著下來會是什麼樣子?不可預測。以我在野的身份,多數的人最關心的,我學政治,認為那一定會有兵變,兵變的主角都已經想好了。
傳來經國先生過世的消息,向來大家都認為這個都是假新聞。我們剛出牢(美麗島事件後,楊按),黃煌雄為我們布置全國巡迴,向大家說「謝謝關心」。那天在和平西路一個小咖啡廳中,我們在談論怎麼佈置時,突然,許榮淑給我電話,她說:「經國先生過世了。」我回說:「這是經常聽到的消息。」但是,後來忽然一想,從她發言,她是立法委員,當時我們坐牢的時候,她在全臺灣的反對黨中幾乎扮演著男人的角色。我跟黃煌雄講:「這由她發言的話恐怕不能輕忽,這是大事!」是不是真的?我國民黨黨部出來的人,知道情況,於是叫一輛計程車到國民黨中央黨部。中央黨部我不能進去,我們就在後面離差不多五十公尺的一個草坪,坐在路邊,這樣我就可以知道,如果是的話,第一個現場一定會有動作。
▍宋:他了解國民黨的運作,必須要由黨來做決定之後的事情。
▍張:我從和平西路到那裡不過是五分鐘,才坐了兩分鐘,就看到大批人馬進出,我就篤定是了。我們就趕快走,立刻到黃信介家裡去看電視,我們一定要共同行動。看到台視裡播出中常會裡亂成一團,那一定的,因為蔣經國死的事情事前沒人敢談,這是大忌諱,亂成一團。你剛才講的那一段,是不是王惕吾說:「這個重大的事情,我們要去敬謁總統蔣公,向他請示。」這個在國民黨裡是具有極大的正當性。我當時想:完了,絕對不可能是李登輝。結果在那個時候,「國不可一日無君,到總統府去。」是不是你喊的?沒有這句話,沒有這個勇氣,沒有今天。
▍宋:那天下午一點鐘,經國先生過去了,事實上他在前一天還準備要到政工幹校,在復興崗,去參加國軍一個重要的會議。結果,早上突然覺得不舒服,我是第一或第二個被王家驊通知趕到七海的。跟以往不一樣,以往他會說:總統有請。中午兩點鐘,我接的電話叫我到七海來,晚年經國先生都在他的臥房裡面見我們,要從側門的偏道開車上去。但是王家驊在電話裡講了一句話:「你從正門進來。」讓我的心裡覺得不祥。
▍楊:他有沒有跟你說他過世了?
▍宋:電話裡沒有講。就叫我從正門進來,我覺得怪怪的。而前一兩天,經國先生接見我,要我好好幫他看家。
▍楊:那時候您是什麼職位?
▍宋:我是首席副秘書長。進去以後就發現經國先生走了,這時候開始打幾個電話,把包括秦孝儀、沈昌煥、蔣緯國等請到七海商量。這時候第一個決定是要開常會。這時候外界都不知道,經國先生的大體還在七海的臥房裡,王惕吾先生在常會裡宣布經國先生大去了,接著就提出來所有常委應該到七海先去向經國先生行禮。
▍張:所以我當時想這一去,李登輝沒有機會了。
▍宋:這時候我就向主席俞國華先生報告,電視都有照出來,你剛才講的沒有錯,台視有錄影,最近我都把這些帶子收集起來,我講:「國不能一日無君,必須趕快依照憲法的規定,讓副總統接大位。就像甘乃迪被刺,詹生副總統在飛機上宣誓就職,要趕快進行。」在下午三點鐘,事實上,初步幾個重要的人在商量時,也討論過要趕快讓副總統接位,趕快宣誓。當時在開會的時候,突然有這麼一個動作,是沒有在現場開會的人提出來,就是王惕吾先生講的。我當時沒有這樣做的話,就有空間和時間,讓別人在運作到底怎麼接班的問題。
▍張:從中央黨部走向總統府,我想局勢己經定了。
▍宋:國民黨的中央黨部就在景福門的後面。所以,沒有向大直開,而是向總統府開,大家都去觀禮副總統宣誓。
▍張:之後,我就跟黃煌雄說趕快找黃信介,因為接著下來就不是國民黨的事情,是民進黨的事情。我們都沒有加入民進黨,因為出牢以後都還在準備「鑼聲若響」,全臺灣繞一圈以後再宣佈加入。看完電視以後就趕快找他說:「我們到民進黨中央黨部去。會不會大亂?大亂,國民黨沒有能力,民進黨就要承擔;國民黨能夠處理,就趕快支持他,沒有別的路;不能處理,黃信介就必須要站出來。」那站出來怎麼辦?黃信介沒有能力,(宋:無兵無將。)必須要民進黨,但是我們都沒有民進黨的身份,我們三個人一起到建國北路民進黨中央黨部。秘書長是黃爾旋,我們要進去的時候,「黃爾旋站在門口阻擋說:不准進來,你們不是黨員。」黃信介不好意思,我就衝進去說:「就是你要來處理,還不讓我們進去,你怎麼做的?」我還和他吵架,後來他看到我那麼兇,才讓我們進去,我們就說:「趕快開臨時中通常會,趕快開。」結果他也很猶豫,最後也開了,但是都找不到人,沒有來幾個。後來尤清說:「很抱歉,俊宏兄,我什麼職位也沒有,我們都沒有緊急的政治意識。」那個時候要另外找朱高正,尤清說:「不要找朱高正,因為他如喪考妣地痛哭流涕。」尤清也不知道怎麼辦,這個是重大時刻,萬一國家亂了,雖然李登輝宣誓為總統,但大家都知道他是主流派的非實力派,萬一有問題的時候,那非得靠反對黨了。所以,黃爾旋事後來道歉說:「我們的政治意識實在遠不及您。」這是我們反對黨的一面。對於這一段,我一直期待記者也好,或者是你閣下也好,應該做出一個說明,因為當時我們都不知道到底臺灣的未來還有沒有。今天連「自由之家」,2017年都說臺灣經過30年,已經是民主的TOP 10,把美國給取代了,美國那年掉下來,補上去位置的是臺灣。美國副總統說的那句話:「臺灣的民主是華人世界的標竿。」當時那一關只要稍微有點差錯,局面就完全改變了!

▍宋:就是幾個重要的人,處理臺灣面臨很大的挑戰的時候,所做的每一個小動作的決定都可能影響後面的變化。剛才講的俊宏那個時候扮演的角色,這是前面剛才講的經國先生過世,然後就一直延續到後來發生天安門事件。這當中又有一段時間,就是李登輝先生己經接了黨主席,前面都還是代理主席。在那個時候,在天安門事件上,我們可以發言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我們怎麼處理臺灣的民主轉型,從威權走向開放。張俊宏有很大的貢獻。
▍張:六四時候你當秘書長。六四造成兩岸的重大的分水嶺,價值觀的分水嶺。JENNY,請先告訴我們妳的綱要。
▍黃:六四的部分,最近有些人到辦公室來跟你談的部分,就是當時候你跟宋主席處理六四發生的當中,你們去協調的部份。在開始的時候是你到總統府要去見李登輝那一段。
▍宋:就是所謂的這個野百合事件,在中正紀念堂。
▍黃:1990年3月16日到總統府後,學生開始絕食,您現在要談的是這個事情。
▍張: 90年是野百合,六四前因,近因是黃信介和我一起發動群眾護送民進黨的國大代表,民進黨的國大代表是要來廢國大的。
▍宋:前面幾個大的時間點,一個是經國先生過去的那一天,一月13日發生的事情;第二個大事情就是剛剛說到的六四發生之後,嚴格講起來就是大家都在關心臺灣未來的發展到底是什麼,我們到底是什麼路線,不能只有去指責或批評大陸上發生什麼事情,我們自己到底應該怎麼去處理;第三個就是在這個過程當中,李登輝先生開始只是接續做完蔣經國總統未完的任期,經國先生只做了一年多,他第二任沒做完。這時候如果要讓李登輝先生繼續他的任期,等經國先生任期結束了之後,他還能不能再繼續領導國民黨,代表國民黨來擔任這個國家的領導人?這時候還是要用舊的制度,就是間接選舉由國民大會代表來選總統的職務。當然,這就是剛才你們講的關鍵的一句話,民進黨一直認為臺灣應該要直接民選,是不是?
▍楊:那時有直選的概念嗎?
▍宋:還沒有講那麼清楚。
▍張:90年已經提出來了,89年時還沒有。
▍宋:89年那時候還沒有,經國先生走的時候還沒有。
▍張:89年談六四的時候還沒有。
▍宋:那時候他們要求的是省長民選,經國先生在世的時候,民進黨就在搞省長民選,但是我今天可以做個證,我是唯一的一個民選省長,那時候蔣經國先生不能夠接受民選,我這個民選省長的民意比我們總統還要高,是全臺灣老百姓選出來的,這是一個非常矛盾的現象。對不對?除了臺北市和高雄市之外,全臺灣的人中許多都投過我一票,但蔣經國總統是由一群老先生所支持的。
▍張:這個我剖析給你聽。這是經國先生的一個「錯招」,他把黃信介跟我一起關起來(美麗島事件,楊按)。你們日理萬機的時候,我們在牢裡「萬日理一機」,就是在談這個。我們不要談總統直選,談總統直選一定會碰撞起來,那麼談省長,而且最好千萬不要我們當選,要讓國民黨黨選。
▍宋:但是你沒有講要我當選,那時候,在政治上我還沒有參與過任何選舉。
▍張:但是居然後來就這樣發展。經國先生、特務機構讓我們關在一起(美麗島事件,楊按),沒有懷好意的。把我和姚嘉文放在同一個房間,黃信介跟林弘宣憲在同一間,希望我們彼此幹起來。果然,黃先生和林弘宣憲一個星期就鬧起來,向我說:「林弘宣憲很差勁,吃飯的時候,蝦不吃也不給我吃。」他是非常帥氣、很純真的一個人。我和姚嘉文住一間,沒有隱私,很難過。每次只端一把椅子,一盞枱燈來,就希望我們兩個吵起來。我之前接觸太多政治犯了,我受了行前教育,知道他們會搞這一套,所以我對於一套東西,我就說:給你給你,我不用。所以我跟姚嘉文沒有吵起來。跟黃先生我是非常仔細地跟他相處,所以黃生先講一句話,他說:「俊宏,我跟我的兒子,跟我的太太都沒有跟你相處的時間那麼長。」他喜歡看書,但是眼睛已經不行了,我寫眉批寫的非常仔細,他都看我的眉批,他說:「你看了兩個月才看完一本書,我兩個鐘頭就知道這本書了。」他和我建立了這種關係。至於未來的情況該怎麼辦?我們就決定總統直選千萬不能碰,但是必須要做,而是先省長選舉,而且民進黨不要選,絕對不要當選,這樣才能促使下一階段非選總統不可。
▍宋:這是他們的話。我做個小小的建議給您將來做大綱,你可能要一個時間表。蔣經國先生哪一天過去,1月13日,然後國民黨開全會、六四,然後這時候國大要開始集會,就是要推選下一任的總統,還是按照原來憲法的規定,間接民選,由國民大會來選舉。這時候就發生主流和非主流,國民黨內部對於推選爭議的問題。在這個過程當中,民進黨一直有非常單一的訴求,認為國民大會這個制度有問題,他們怎麼可以參與這個東西的選舉?這就是野百合運動的主張。尤其那時候他們(國大代表,楊按)又在那邊提出國大要擴權,不但要選總統,還要擴權延長他們的任期,津貼要增加,這變成學生運動重要的反對訴求。那個時候,黃主席(黃信介,楊按)帶學生要到總統府請願,要去衝總統府。結果當然被憲兵擋住,沒人理他們,也沒有派重要的人來接待。黃主席被憲兵抬出來,褲子都撕破了。晚上就由做過台視的董事長的陳重光,一直跟李登輝先生保持很好的關係,跟我也有些來往,就由他陪同我到黃主席的家,我們四個人見面,就是我跟陳重光、黃主席跟張秘書長。
▍楊:那是哪一天?
▍宋:時間都有,三、四月份,我都有記錄,都會給你。我有很好的秘書,我每天做什麼事,幾點鐘見誰,他都有筆記,後來都是按照這個東西去追查出來這些事情。抬出來以後,他們講要杯葛總統的選舉,在陽明山杯葛選舉,國大代表又要加錢,又要擴權,沒有正當性。然後,3月14號我就跑去見黃大老(黃信介,楊按),張秘書長也在那裡,就我們四個人,沒有別人。當中最重要的兩段話我必須要在這邊交代,他幫了很大的忙,就是黃大老講蔣總統要正式道歉,因為黨主席到總統府,你不但不派人接見,還把褲子撕破,還要求見面要怎麼樣,而且要杯葛讓國民大會開不成。我說現在是三月,如果選不出總統,我那時候己經是秘書長了,我說:「如果總統選不出來,5月20號就不能就職;如果不能就職,國不能一日無君,總統任期已經滿了。」「那不行,他現在要見我,而且要向我道歉。」黃大老是很有意思的,很江湖味,聲音很大。我說:「我贊成。」
在這個之前,我必須要講一段很重要的事,我書上都有,將來提供你參考。就是李總統被提名之後,他找王作榮,而且後來被他相當重視,因為余紀忠先生對他很推崇,余紀忠先生一直請王作榮做他的總主筆,在他的中國時報寫社論。我們一起到惠蓀農場討論,假如他要當選總統,第二任以他自己的名義由國民大會選出。這時候,就希望發展臺灣的民主。當時余紀忠提到一個問題,就是要開國是會議,大家來討論這些重大的事情。但是沒有正式的,我全程都參與,到惠蓀農場住了兩天,在那邊討論。所以我心裡面有數,李總統願意開國是會議,跟在野黨一起共同商討臺灣怎麼樣民主轉型的一些構想,但是這還是個構想,連跟民進黨談都沒談過這些事情,影子都還沒有。那這個時候你要杯葛選舉,我做秘書長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要達成什麼任務,就像總統的選舉的事情要能夠平順的先過關。如果這個不能過關,後面的事情都是空談。
對於黃大老的「那不行,現在必須要向我道歉,現在就要承諾這些事情。」這時我就講了一段很重的話,我說:「你講這話我都非常贊成,但是有句話,假如總統是在要脅底下承諾要做什麼事的話,這個總統連我都看不起,他被迫定下城下之盟,答應一些事情。」我說:「倒過來,讓總統選舉順利的產生之後,他以總統當選人的身份,5月20日還沒到,正式要邀請在野黨的領導人到總統府共商國事,在那個地方說我願意召開國是會議,我們一起共同策劃國是會議怎麼開、有誰來參與、討論的題目是什麼。我講這個道理給黃大老和他(張):「你這時候逼著他做下城下之盟,這個總統怎麼會有威望來處理未來的事情?」他同意了。這時,我又提出一個問題:「情治單位告訴我說你們雖然會答應個國民大會召開,大家都很清楚李總統本省人都支持他,但是你們會在投票當中故意把墨水瓶倒在投票箱裡面,把選舉變成亂七八糟的。」他(張)也在旁邊幫忙我化解這個事情,黃大老只講一句話:「不會啦!講話算話。」然後,果然順利產生了總統。李總統在四月二十幾號正式請他們倆人到總統府去共商國事。這裡,我必須要說到香港的民主,應向臺灣學習,向對岸的人說:「不是只有對抗,必須要有對話。」從對抗到對話很重要,必須要有對象,誰能夠代表在野和其他民意的。由對話到有對象,但是更重要的,要有對策,而這個對策不可能一步到位。臺灣不可能會全盤地變成所謂的西方的民主,這就是俊宏所做的非常重要的幾項非常嚴謹的建議。第一階段要做什麼?後來,一段一段都處理了。第一個就是「一機關兩階段」的把國民大會的職權逐漸的慢慢化解掉,產生新的國會。第二件事情,逐步地解除戒嚴;之後就是讓政治犯釋放,修改刑法一百條;第三個省長直選,然後總統直選。這些一步一步的來,不可能一步到位,但是最先開始所接受的承諾,非常重要的承諾就是要籌組開國是會議,在國是會議當中,他(張)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1990年3月,「野百合」為三月學運的精神象徵,「野百合」象徵學生對台灣本土的認同。圖片來源:邱萬興先生拍攝
▍張:這時候,在現場的學生不願意讓任何政黨參與他們的決策,但是他們私下邀請民進黨參與。第一個,他們沒有宣傳車,沒有麥克風,便當等的接濟,所以我就派社運部門的張國忠等著學生制服到現場坐在那裡聯繫支援。第二天或是第三天時,第一通電話打過來,這電話是一個台商剛剛出廠的對話機,有三、四公斤,他帶到現場一部,我在秘書長辦公室睡沙發睡了三天,電話聲響,趕快接起來,聽到:「俊宏兄,學生問要什麼訴求?學生們問你什麼訴求?」我沒有考慮兩秒鐘就說:「開國是會議。」後來,在他們的四大訴求裡面擺上去了。可是我想:你用四大訴求,沒有力量。因為我處理過那個東西,省長選舉、總統選舉,那麼一大堆要求,只能有一樣,群眾運動必須要有力量,集中一項就是開國是會議。(宋:是重要的訴求。)而且我再三強調:最後逼不得已,一定發生228。當年,在我們腦海裡面,沒有消失北京天安門悲劇(宋:這麼多學生聚集在總統府對面的廣場,在那邊鬧事,這時候軍警就要介入。)
我14歲的時候在圖書館看雷震的《自由中國》,我看的就是「國是會議」;其次,我在政工幹校當預官受訓的時候,一個姓宋(可能是宋時選,楊按)的人說:任何群眾運動,第一個解除災難的方法就是趕快離開現場。當時,能夠離開現場的訴求就只有開國是會議,就是讓他進入屋頂來談辦法。(宋:在體制內去討論。)不要讓他們停留在露天的地方,天安門、228都是在空曠的地方。(宋:就是沒有對話、沒有對象,然後也講不出對策。剛剛講的,他的對策就是開國是會議。)一定會逼使再溫和的當權者都必須動用坦克。六四天安門剛發生,我的眼睛就貼在那個電視一直都沒有離開,鄧小平跟學生談判的情景到現在都還在腦海,就是沒有離開現場,到最後逼使他動手。而且你談條件一定要具體,可以被接受的,如果不能被接受,不能離開現場,兩方面不能交代,最後就必須要用流血了來處理,所以我主張這個觀點(讓大家進入屋子裡來談,楊按)。
▍宋:在這邊我要接著他稍微補充一下,這時候這個現場和另外的一個現場,就是在陽明山的國大代表選舉。國民黨很大的壓力還不只是學生這邊在請願,第二個問題是總統選不出來,會發生了嚴重事情,而這兩件事是掛在一起的。在陽明山開會的時候,朱高正和黃昭輝他們幾個人在翻桌子鬧得很厲害,那到底怎麼辦?因此,當中最重要的兩件事情,一個要平息這些學生的訴求,讓學生離開現場。他(張)提出兩個非常重要的概念,讓學生對於民進黨要有信任,信任就是他在幕後給他一這些資源,像他講的,這些資源很多都是我們側面給他們安撫,讓學生不要覺得他孤立無援。第二個,李總統在接受大家的建議之後,他約集幾十位這些學生代表到總統府,跟他們面對面的溝通。這裡面不全然都是民進黨的那些學生,有些國民黨的台大學生,孫震後來他寫條子跟我講,孫震那時候是台大的校長,他的條子我都還留著,他說他也在那邊安撫學生,包括後來很有名的林火旺。這些的學生派代表由我秘書長在國民黨中常會開會的場合裡面約見他們,長談四小時。就是剛剛講的,把他拉進現場,承諾一些事情,我們絕對會改革,但是,改革需要時間,需要步驟。他(張俊宏)扮演的是那一群,我扮演的是這一群,但是最重要,這時候如果沒有溝通的大臣,他們叫我們是「勾結」,情緒下不來。這時候鬧的事情,這就是他(張俊宏)講的,反復的強調:天安門事件會在臺北發生。為什麼?你在那邊鬧,總統又選不出來,你告訴我怎麼辦?
▍楊:軍方有可能介入嗎?
▍宋:你想想看為什麼後來軍方的事情,包括後來劉少康小組,很劇烈的。這就是為什麼經國先生的日記裡面所談的這些民主改革當中的一些也起起伏伏的各種東西,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講完的。我們先講大架構,就是你必須不要節外生枝讓不希望的力量進來,把可以協調的事情處理好。所以,臺灣的所謂的寧靜革命,為什麼會有不流血的原因,這個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一個過程,這個過程當中有幾個不能缺少的,第一個,要有一些溝通的管道,要有一個共同的願景。但是最不容易的是能夠做到的時間表,一個時間表,還有做到的議程,這當中,缺一不可。
後來,之所以為什麼國民黨鬧成主流和非主流,就是有一些非主流的人就認為不能夠直接這麼快的答應可以總統直選。第二個,由民選產生代表,那我的法統到哪裡去?這就是國民黨這些人所關心的問題。這些是後來才會有兩岸關係條例,才會有修憲的前置詞。這個前置詞,我不能不說李元簇先生蠻有耐心的,就提出了一個「在國家統一前」這樣的一句話。包括黃主席、康寧祥和張俊宏幾位都能參與國是會議。尤其是在國是會議裡面,很多事情都是我們兩個人,常常在幕後先大致有個方向,再在檯面上進行討論。這是目前香港最缺乏的,沒有這樣的條件。我上次跟他們講一個很簡單的概念,香港好不容易現在已經選出來超過半數以上的民意代表,但是你代表誰?黃之峰代表誰?我第一步要什麼?第二步要什麼?第三步要什麼?你要有一個對策。現在沒有對象,跟誰談?香港現在要跟誰談?我們統稱叫異議分子。沒有對象。沒有對策。
這位先生(張俊宏)那個時候,經常半夜三更,幾次三番,由我們倆個去解圍。一次在西華飯店,那個時候我們接到了情報,他(張俊宏)半夜一點多鐘也打電話給我,跟我講,有人身上灑了汽油,打火機都在旁邊。
▍張:有幾個事情,我期待您的秘書能夠查證那個時間。你剛剛談的就是台中的「建國連線」,他們全身都潑了汽油,而且在瓦斯行的旁邊,希望瓦斯能爆炸,那前線的就是員警。半夜裡已經一點多了,沒有人能解決,我還在台大為了南向政策開會。連邱義仁他們都出面(宋:我第一次跟他們談判就是跟邱義仁。)邱義仁本來是要挖我的瘡疤,但是他自己親自來拜託我要溝通。我說你再三說我去偷吃溝通大餐,現在你開口要我去吃溝通大餐,是不是?(宋:人家都罵我們倆是勾結。)
他們都是透過立法委員協調的,不願意透過秘書長。連立法委員張俊雄他們幾個人的一起來拜託我,說:「不管怎麼樣,這個一旦發生了,就是比二二八事變更厲害,瓦斯行爆炸燒起來,二、三十個人會死掉。」我說:「你們現在終於要拜託秘書長去溝通了。」「拜託了,拜託了。」車停在外面,在台大法學院。我就找戴一,戴一半夜裡接到我的電話(宋:戴一是我們共同的一位朋友,他是台灣皮包協會的理事長。他是雲林人,和蕭萬長非常好。)他半夜裡穿著西裝,開著車子衝到你(宋楚瑜)家裡。這是第一件,可能比二二八事變更厲害,是朝野同解決的一件事。第二件,雙十節,李鎮源院士一直要跟我談,(宋:跟陳師孟。)他隔天雙十節,要躺在那裡讓戰車壓過去,為了刑法一百條。(宋:他們的訴求是廢掉刑法一百條,而那時候的訴求是反閱兵,因為郝伯村當了行政院院長,他們要反軍方,反閱兵。)他要躺在那裡讓戰車壓過去,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有這個勇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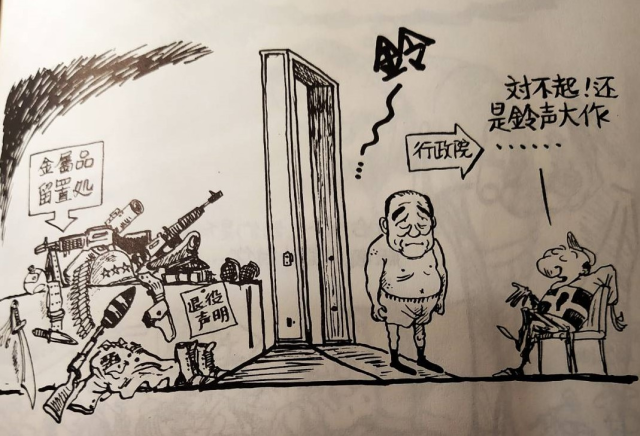
學生立院抗議與警方火爆衝突♦作者|CoCo♦圖片來源|中國時報79·5·5

袪除軍人干政疑慮,郝伯村將建立民主悍衛者形象♦作者|CoCo♦圖片來源|中央日報79·5·4
▍宋:在台大醫院旁邊。是第一次這個部隊不是從重慶南路火車站往臺北法院方向開,而是要從仁愛路往總統府走,所以會經過台大醫院。李鎮源是老教授,就帶著他們這些人擋在那邊,讓閱兵部隊過不去。這是第二件事情,也是戴一幫忙。
▍宋:後來在來來飯店,從半夜12點鐘談到清晨6點,我等等跟你講,很精采。
▍楊:您在嗎?
▍宋:就是我主談,那時後的來來,就是現在的喜來登。
▍楊:您有帶副手嗎?
▍宋:有,副手叫做馬英九。還有洪玉欽、施明德參與。
▍張:施明德的司法問題。我在來來飯店開會,一個記者打電話來:「明天520,特赦政治犯。」連記者都知道明天有一個名單,名單裡面沒有施明德。我說:「怎麼可能沒有?他是第一號元凶。」那時候,我一通電話打給你說:「施明德是沒有釋放?」你告訴我說:「沒有。」我說:「施德明沒有釋放?」你那時候回我說:「我沒有提。」我說:「施明德釋放還須要提嗎?」你說:「他自己不願意出來。」我說:「我們當年進去也沒有問我們要不要進去。我們不進去,你給我拉進去;我們不出來,你硬是把我拖出來。」
▍宋:那有一個前提就是他不認罪,他不認為那是叛亂。你要自己認罪了,然後才釋放。
▍張:當時黃信介說我不出來,他也不出來。我說我給蔣先生的信都寫好了,說我關在這裡習慣了,出去我也沒有飯吃,我不出去。結果說完後沒有兩分鐘憲兵就進來,把我所有的東西打包丟出去。我是被抓進去,被丟出來的。我說當時也沒有問我就把我抓進去,後來好像你就答應我,所以第二天施明德就出來了。
▍宋:後來施明德在他自己的回憶錄裡寫到,就是他不認為當年美麗島的事情中他有做錯什麼事情,不要因此特赦他,好像你犯了錯,我特赦你。在所有人裡面,施明德是很堅持的。
▍張:他很堅持,就是公布他被特赦了,(宋:包括李慶元,在國外不許回台的那些人都回來了。)但是一直到晚上六、七點仍然不出來,於是施啟揚、馬英九,一個是司法院長,一個是法務部長,兩個人來找我要我不管怎麼樣去勸,我回說我勸不動他。那時許榮淑在我旁邊,她說只好她來了,她進去也勸不動。最主要是要他簽一個出來的切結書,切結書要求出去不能亂講話,結果是許榮淑替他簽的。後來,施明德始終不願意承認他是這樣子出來的。

1990年3月,野百合學運的總指揮范雲是台大社會系學生。圖片來源:邱萬興先生拍攝
▍宋:我補充他講的三個非常重要的概念。野百合這些學生,就是後來民進黨現在的主力部隊,包括范雲、鄭文燦,都是那個時候的學生,所以在那一批裡面培養了很多民進黨後來的菁英。
▍楊:馬永成是不是?
▍宋:都是,大部份都是這裡面的人,可以查得出來的。
▍張:還有最後一點,我們在那裡靜坐,後來李總統邀請我們到總統府去,是您閣下(宋:對。)要秘書長一起去,這個時間點是?(宋:我都有記錄。)我說這些的目的就是告訴後代,一個大事就是民進黨的正名。在這之前,民進黨的名字都XX黨,或是X進黨,在接見過以後,第二天報紙全部都是叫民進黨。
▍宋:以前包括青年戰士報、中央日報都叫XX黨,或是X進黨。
▍張:這些把台灣民主轉變的過程裡面,國是會議也好,總統直選也好,朝野政黨之間的和解,也是由他(宋楚瑜)在協商中做到的。
▍宋:對方認為他(張俊宏)是妥協派。這就是我剛剛講的,為什麼他的角色和我的角色沒有在外界被人知道,因為我們兩個人都不太在外面吹噓,說我們怎麼樣把這些事情辦好的。這就是非常重要的概念,談判的過程有很多事情是大家彼此要調整的,但是你把哪一個人所說的話變成是讓步,變成是妥協,在外面就會讓這個人談判的力道和籌碼喪失。這就是現在非常糟糕的問題,大家都把談判放在太陽底下,用顯微鏡來看,請問有哪一件政治上面彼此的協調都沒有任何人做一點點調整?如果調整都是投降,那就完蛋了。
▍張:過去談這些東西,大家都聽不進去。但是,今天你看香港悲劇,使得世界金融中心己經面臨破產,而且面臨對決。在那個情況底下,任何大事沒有朝野共同的結合是做不了的。
▍宋:套用兩個人的真正的結論:必須要有對話來取代對抗,但是對話必須要有對象,對象必須要有對策。
▍張:套用一個管理學家講的一句話:生產線裡面不會有人性的醜陋,分配線裡面不會有人性的善良。分配是永遠不會平均的,當分配線吵成一堆,即將要解體的時候,提醒領導人趕快創造生產線,因為生產線裡面只有人性的光輝,不會有鬥爭。當兩黨之間,整個臺灣面臨轉型期,領導人轉型期擺不平的重大時刻,只有大家共亡,就像今天香港一樣共亡對決時,領導人建立一個新的生產線,生產線裡面沒有人性的悲劇黑暗,而生產線就是創造在低樓層不能解決的問題,地下室也不能解決,地下室也不能解決就跑到二樓,看到生產線的光明,人性的貪婪及黑暗就會消失。我們當時所實驗的就是當一個國家權力的轉型期,當一個既有的軌道已經走不下去,要換軌道的時候,如果沒有建立一個新的生產線,是沒有辦法突破困難的。上天賜給人的洪福大禮必須要透過災難。所以,孫子兵法裡面說:化幻為力。就是在旋轉門裡轉成力,轉成共鳴,我們確確實實在當時,實際上實驗過這種方法。

▍宋:我補充兩個非常重要的概念,需要把它說出來。在這個過程當中,這位先生(張俊宏)從來沒有跟我協調他個人要什麼,我必須要為歷史做見證,包括黃信介先生也從來沒有跟我說他想要在談判當中,希望執政的人要給他什麼樣的權利和個人的利益,從來沒有談到這個問題,這點我很清楚,我們沒有任何利益的交換。
剛才講的由李鎮源先生所帶領的反閱兵,它發生這麼嚴重的問題,朝野要對幹起來了。這是在國際上很難堪的事情,閱兵搞不成;鎮壓,兩個對抗,又是軍方的頭頭郝伯村先生做的行政院長,竟然閱兵都搞不成,怎麼辦?半夜12點鐘在來來飯店,主談的是李鎮源教授,和陳師孟代表他們;我這邊的代表是我個人、馬英九和洪玉欽。我是秘書長;馬英九是副秘書長;洪玉欽是我們立法院的政策協調會的頭頭,他是溝通大臣,跟你(張俊宏)也經常有一些溝通。他們的訴求是廢除刑法一百條,就是叛亂罪。我說依照刑法一百條的全文,很清楚的,意圖以非法的手段顛覆政府,改變國體。如果一個國家遭遇的反對黨以非法的手段、暴力的手段來顛覆他,一個國家都沒有自衛的能力的話,這國家還有任何安全嗎?所以我就提出一個概念,區隔什麼叫做言論犯?什麼叫做行動犯?言論和思想不應該被認為是叛亂,但是用暴力和脅迫的手段來實施,並著手實施,而且有根有據,國家總是需要鎮壓。我講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話,國民黨不會是永遠的執政黨,哪天假如民進黨執政,我用暴力和脅迫非法的手段來給你搞的話,你都沒有防衛措施,這個國家,這個社會,這個政府還能安定嗎?很有意思的,因為晚上已經談了很多,李鎮源教授累了,他年紀比較大,有點打瞌睡。所以主談是陳師孟,他非常接受,他說:「這個有道理。」就是我們不可以廢刑法一百條,而是修刑法一百條,修的方冋就是區隔什麼叫行動?什麼叫做思想和意念犯?他同意了,他要我簽字,他要我把我們剛剛談論的結果簽字。這時,馬英九在旁邊說話,他根本就不認為要修正,他是保守派,我就把他拉到邊上跟他說:「我是主談,我是秘書長,你不要發言,我負責任。」談完以後,陳師孟要我簽字,我就跟陳師孟講:「不能簽字,因為人家就會問你代表誰?你有正式代表民進黨的證書嗎?我今天講的話,我自認為代表國民黨,但是剛剛這些話,嚴格講也沒有經過黨內程序;而我們兩個今天簽的字要立法院完全根據我們兩個人簽的字來執行,太不尊重立法院了吧!如果我們這麼不尊重立法院,這個國家還有民主嗎?」他說:「那我們今天晚上從12點到早上六點鐘,不是白談了?假如到時候你不認帳,怎麼辦?」我說:「如果我不認帳,我回去不能說服我的主席和總統,以後你看到我,吐我口水,說宋楚瑜講話不算話。」所以,後來為什麼「扁宋會」的時候,他跑出來替我講話,他告訴阿扁說宋楚瑜講話算話。我會回去已經七點了,我就接到大安總統官邸跟總統報告這個事情,他原則同意,但是要我立刻去跟郝院長報告,讓郝院長了解,這個時候是禮拜天。禮拜天郝院長到長庚去打球,我就趕到長庚球場把他請出來,在一個地方跟他好好地溝通,然後後面就按照這樣的程序完成,就是區隔什麼叫做行動犯?包括六四和任何概念,它是一個路線的意念,不是顛覆國體,也不是行動要如何,不能由思想變成叛亂的理由。這就是我剛剛講的臺灣了不起的,就是創造很多先例,用和平的方法。很多事情不能一步到位,至少要有一步一步的步驟,,然後要有人溝通,而且有些話不能講穿了誰簽了字,誰沒有簽字,是不是這樣的情形。
▍楊:當年的情況中發生這樣的一個場景,歷史上也很少見。
▍宋:我有沒有跟你講過他跟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我以前和俊宏不太熟,是他的老太爺生病在榮總,我奉經國先生之命跑到榮總去看他的老太爺,我在那裡見到他,跟他第一次好好聊天。他給我講了一段話對我有很大的啟發,他是中山獎學金到柏克萊,我也是在伯克萊拿的學位,他在那個地方參加一個活動,就是有一個柏克萊非常有名的數學的教授,叫做陳省身。陳教授。那時候美國還在越戰,美國不讓他們到大陸去。陳省身是一位少有的教授跑到大陸去訪問,回來以後在柏克萊演講,講他在大陸上的所見所聞。他(張俊宏)老兄就跑去聽,被校園的人打了報告。他回來以後,就開始對他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意見,因此後來的演變變成他因為美麗島的事情坐到牢裡面。在牢裡面沒有別的特權,偶爾還可以看看報,他就跟我說他有一天在報紙上看到陳省身,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載譽回國掃墓。他說我當年就是因為去聽他的演講,結果我反而變得坐牢,結果他還載譽回國,陳省身到匪區去吔!他就跟我講了一句話:「世事在變。」後來,我把他的話歸納成:時代環境在變,權力也不是永遠被哪一個政黨可以永遠壟斷,你必須知道如何分享。這是俊宏講的,就是在野和在朝的必須要知道如何彼此坐下來,相互討論這些問題,所以我常常引用他給我的這個概念,那就是我們兩個人能夠可以對臺灣的民主提出一些貢獻,基本上就不是溫和和激進的問題,而是我們倆都很務實的處理這些事情和困難。
▍黃:主席,當時你到柏克萊,是拿中山獎學金去的嗎?
▍張:到柏克萊是因為我剛出牢的時候。
▍宋:還沒有,是在那個之前,還沒有坐牢。你告訴我說你去聽陳省身的演講。
▍張:那是國務院邀請我到美國。
▍宋:不是中山獎學金,但是你是到柏克萊去。
▍張:到美國去聽了陳省身的演講,他是第一次到中國大陸去,我把錄音帶帶回來,陳鼓應和王曉波很急切地想知道,後來我說你們自己聽聽,結果,他找了一些人去聽,所以我就變成了洩密為匪宣傳。
▍宋:陳省身跑到大陸去演講,看完之後回來演講,他說張俊宏跑到台灣去散佈,其實是別人。
▍黃:剛剛上個禮拜,吳乃德來跟他證實他(張)是不是中山獎學金的,外面一直在傳這個,這個部份要修正,一直在誤傳。
▍宋:順便跟您提一下,他們講了蔣經國先生的日記,特別提到他對康寧祥好像不滿意,我必須要替經國先生講一下話。經國先生在立法院做施政報告,在講預算,康委員就發表不同的意見,經國先生特別在日記上面寫了一句話,他在對於省藉的問題如何如何,經國先生就很激動,用很激動的言語跟康在對著講。他的日記主要的目的在自我檢討,他說雖然他講的話我不一定同意,但是完全違背了他平常過去的基本的做法和作風,就是為什麼要這麼激烈的對他用這樣的話來講,以後要好好調整,他是在自我檢討在寫日記,但他最後那句話:「以後,對小人講的話不必要那麼計較。」就被黃清龍拿來講說:你看!經國先生叫康寧祥叫「小人」。我今天可以這樣講,經國先生在那個時候的自我檢討,「小人」有兩個意思,一是道德上的小人,一個是小人物。你怎麼會去跟這個還不起名的人這麼斤斤計較,當面給他那麼難看,我以後要好好檢討。後來經國先生有多少次單獨的約見康寧祥,如果他這麼討厭他,他會去約見他嗎?而且約見康寧祥有個非常重要的事情,不許旁的人在旁邊,單獨就跟他談,不會有警衛,表示彼此之間的互信,這點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我再講一下許信良,這裡面有提到。我有經國先生的手記,很清楚的就是中壢事件之後,許信良當選了縣長,當然黨內有很大的衝擊。中壢事件又燒了警察局。經國先生有一天在下班的時候,下樓跟我在一起,經國先生的一個參謀,專門負責他的行程,說他要去看許信良。行政院院長要去桃園看許信良,就是要和解。事實上,後面的發展是另外一回事情,他確實也表現出誠意願意跟他和解。我有很多他的照片來證明,後來不止一次到桃園縣政府,甚至還到許信良家裡,單獨到他家裡去跟他溝通,跟他表示善意。這就是我剛剛講的,政治上的發展,有很多事情必須是雙方的,不是單向的。
▍楊:許信良後來不是逃亡嗎?
▍宋:那是後來的事情,就是為了余登發的事情。
▍張:這是另外一個很長的故事。
▍宋:這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講完的,今天是先講他(張)的事情,我是順便提到,你(張)哪天碰到可以問他(許信良)有沒有這件事情:經國先生不止一次的,在中壢事件之後,到許縣長家裡去看過他。這個對於很多人來講是很震驚的:你怎麼去向叛變的人向他去說話。我今天為什麼講這個事情,嚴格講起來,就是臺灣的政治有這樣的成績,我們應該珍惜。真不簡單,是不是?有很多的正面的因素。
▍張:今天這麼值得紀念的日子啊,六四。我看朱立倫今天在報紙上寫的非常好的文章:以力假仁者覇,以德行人者王。非常好的對六四的評論。
兩岸,我們經過了一場價值的戰爭,這價值的分水嶺上,經過了31年,我給它補充:我們承繼的是五四的和平民主,中共也是靠五四起來的,力行六四卻走向極權。這價值的分水嶺就是89和90年。我們所創造的不是由上而下的民主,是由下而上。尖銳衝突的兩黨也能和解,也能創造共贏的故事。過去我們以為是做了一件小事,平常說的,例行性地解決一些災難,沒想到解決的這些災難今天變成世界的標竿,華人世界的標竿。怎麼樣把集權的黃禍變成人類的洪福大地。(宋:好好的接棒下去。)作為一個在野者提出來的任何改變,不會成為笑話而稱為典範,成為標竿。
▍楊:張俊宏委員和我認識十幾年,他常常跟我講的一些偉大的事情我都不太相信,後來許信良跟我說張俊宏做了重大的事情,我也不太相信,今天宋省長講完之後,我覺得可信度有百分之八十。當時發生的那些事情是有點不可想像,在衝突中協調對中國人來說很難。蔣公和毛先生在戰後有多好的機會,1945年那時候兩黨中沒有宋楚瑜先生和張俊宏先生這種人物,當時有這種人物,我們中國可能不會有內戰。宋先生,你看現在藍綠兩個陣營以及兩岸的關係這麼尖銳,這不是你們當初所預想的。
▍宋:我特別要強調一句話,我們兩個在談這些問題的時候,到今天為止,從沒有談過個人利益。你(張俊宏)從來沒有跟我講你要什麼好處,你能分到什麼東西。
♦ 專文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