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轉載自 社會科學報社公眾號。若有侵害著作權,請速告知,我們將盡速移除 ♦
2021/10/23
2000年,美國著名作家大衛·布魯克斯(David Brooks)在其暢銷書《天堂裡的波波族》(Bobos in Paradise)一書中提出了“波波族”的概念。波波族是“波西米亞”(Bohemian)和“布爾喬亞”(Bourgeoisie)的混合體,既雅痞,又自由,既追求生活品位,又不拘泥於世俗的繁文縟節。然而20餘年後,通過對美國社會現狀的分析,大衛·布魯克斯認為,波波族加劇了美國的社會衝突,造成了社會分裂,現代精英體制亟需新的變革。2021年9月,《大西洋月刊》發表大衛·布魯克斯的文章《波波族如何分裂美國》(How the Bobos Broke America),對此進行了分析。


“波波族”如何分裂美國
編譯 | 熊一舟
圖片 | 網路
“布布族”與“波波族”的衝突
2020年夏秋,多艘“特朗普式”遊船巡遊在美國水域支持唐納德·特朗普。參與者吵吵嚷嚷地一大群一大群地聚集在一起。他們在船上掛滿了國旗——美國國旗,但也掛著標誌性的口號旗幟:別踩我,別再胡扯了。女人們站在前甲板上,穿著紅、白、藍三色的比基尼,舉著藍絲帶和高筒牛仔褲向附近船隻上的“愛國者”們致敬。男人們站在控制台上,展現出鋼鐵工人的那種男子氣概,儘管這些人更有可能是房地產經紀人。它們代表了一種新的社會現象:民粹主義賽舟會。這些人收入很高,但認為自己是普通人、被忽視的人。
你也可以在美國以外的地方看到這種現象。人類學家尼古拉斯·凱姆拉(Nicolas Chemla)把這種社會類型稱為“布布族”(Boorish Bourgeoisie,Boubours),即粗鄙的資產階級。如果說中產階級精英“波波族”(Bourgeois Bohemians,Bobos)傾向于擁有進步的價值觀和都市品味,那麼布布族則想方設法用本土主義和民族主義來打擊他們。
擁有高端汽艇的人怎麼可能認為自己是受壓迫的人呢?事實是,他們並不是完全瘋了。在過去的幾十年裡,西方社會的階級結構變得混亂不堪。過去很簡單:富人加入鄉村俱樂部,投票給共和黨;工人階級在工廠辛苦勞作,投票給民主黨;介於兩者之間的是大量的郊區中產階級。我們清楚地知道,當階級衝突發生時,它會是什麼樣子——工人階級成員會與進步知識份子聯合起來對抗資本主義精英。
但不知怎麼,2015年和2016年的階級衝突來臨時,情況卻完全不是這樣。突然之間,西方的保守黨派——曾經是地主貴族的擁護者——把自己描繪成工人階級的戰士。左翼政黨——曾經是無產階級起義的工具——被攻擊為受過高等教育的城市精英的俘虜。如今,你的教育水準和政治價值觀在決定你的階級地位方面和你的收入一樣重要。正因為如此,各階層之間的鬥爭不僅是上下之間的鬥爭,而且是與處於各自階梯上的富人和窮人之間的鬥爭,也是與跨越意識形態鴻溝的對立黨派之間的鬥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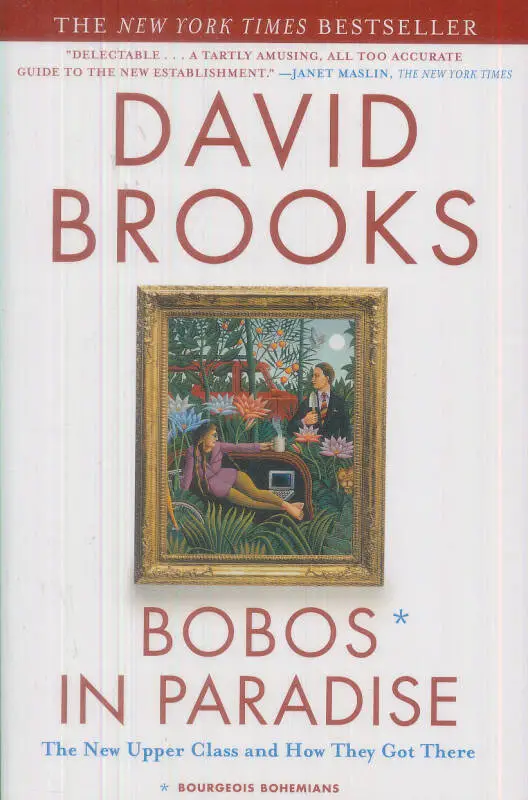
波波族控制了知識體系
2002年,理查·弗羅裡達(Richard Florida)出版了《創造性階層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一書,書中讚揚了創造性階層帶來的經濟和社會效益。他所說的創造性階層或多或少是由科學家、工程師、建築師、金融家、律師、教授、醫生、高管和其他專業人士組成的群體。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創造了巨大的財富,他們可以將新想法轉化為軟體、娛樂、零售概念,等等。
在過去的20年裡,波波族或者說創造性階層迅速增長的經濟、文化和社會力量引發了全球的強烈反對,這種反對越來越惡毒、越來越瘋狂,甚至像世界末日一樣。然而,這並非毫無根據。波波族已經聯合成一群孤立的婆羅門精英,主宰著文化、媒體、教育和科技。創造性階層將文化成就轉化為經濟特權,反之亦然。它控制著喬納森·勞奇(Jonathan Rauch)在他的新書《知識的構成》(The Constitution of Knowledge)中所描述的知識體系——由決定真理的學者和分析師組成的龐大網路。最重要的是,它擁有生殺予奪的大權。它決定了什麼被認可和尊重,什麼被輕視和摒棄。當然,網路已經民主化了,讓更多的人有機會使用擴音器。但精英品位的制定者仍傾向於那些生活在創造性階層聚居地的精英大學畢業生。如果你覺得自己被社會看到了,那是因為創造性階層看到了你。如果你覺得自己被忽視了,那是因為創造性階層沒有看到你。
如果我們以前的階級結構就像一個分層蛋糕——富有、中等和貧窮,那麼創造性階層就像一個從很高的地方掉到蛋糕上的保齡球。大塊蛋糕濺得到處都是。在《階級大轉變》(The Great Class Shift)一書中,蒂博·穆澤格(Thibault Muzergues)認為,創造性階層已經擾亂了整個西方世界的政治。在一個又一個國家,受過教育的都市精英的崛起導致了工人階級對他們的反抗。特朗普的支持者將媒體——創造性階層的縮影——列為美國最大的威脅。瑞典政治學家博·羅斯坦(Bo Rothstein)指出:“工業工人階級和所謂的知識文化左派之間150多年的聯盟結束了。”今天的工人階級不僅強烈地排斥創造性階級,而且排斥它所控制的知識體系。

種族主義仍在分裂和玷污美國,但他們忽視了創造性階層在日益加劇的不平等和社會衝突中所扮演的角色。儘管他們都在談論開放,創造性階層卻非常狹隘。在《21世紀的社會階層》(Social Class In the 21st Century)一書中,社會學家邁克·薩維奇(Mike Savage)發現,通過與不同職業群體的人接觸來衡量,受過教育的精英往往是社會上最狹隘的群體。在《大西洋月刊》的一項研究中,艾曼達·裡普利(Amanda Ripley)發現,最缺乏政治容忍度的美國人“往往是白人,受教育程度更高、年齡更大、更都市化、黨派色彩更濃的人”。
如果創造性階層只是努力工作,賺的錢比其他人多,可能就不會引發如此激烈的政治衝突。導致心理危機的是創造性階層散發出的“比聰明”“比開明”和“比寬容”的氣息。那些覺得自己被忽視了的人會想盡一切辦法讓自己被關注,感到羞辱的人會為他們的羞辱報仇。
增加通向成功的途徑
隨著波波族在經濟、文化,甚至是我們對什麼是美好生活的理解上取得了某種程度的控制,社會開始向他們靠攏,舊的三部分階級結構分裂成令人困惑的混亂的小群體,他們以各種方式爭奪地位和地位。例如,波波族擁有強大的文化、政治和經濟實力。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精英們擁有巨大的文化力量和不斷增長的政治力量,但仍然沒有多大的經濟力量;而從事服務行業的階層和農村工人階層,既沒人聽,也沒人看,幾乎沒有任何力量。與此同時,美國的政治問題變得更加尖銳,身份變得更加突出。

拜登是自羅奈爾得·雷根以來首位沒有常青藤大學學位的總統。拜登宣導的項目——新冠肺炎救濟法、基礎設施法案、家庭支持提案——代表著將資源輸送到那些沒有大學畢業的人以及被創造性階級經濟甩在後面的人的努力。正如拜登今年4月在國會聯席會議上所吹噓的那樣,“在美國就業計畫中創造的基礎設施工作中,近90%不需要學士學位,75%不需要副學士學位”。
如果有一種經濟方法可以消除美國日益擴大的階級鴻溝,拜登的一攬子立法方案無疑是最佳選擇。它將縮小造成當今階級仇恨的收入差距。但經濟再分配只能到此為止。真正的問題在於排序機制本身。它決定了誰被歸入社會上層,誰被排斥在外;誰可以搭乘自動扶梯到達卓越的地位和世俗的成功,誰面對的卻是一堵牆。
現代精英統治是一台產生怨恨的機器。在青春期有完成學業的能力是很好的,但是圍繞著它組織你的社會是荒謬的。團隊合作的能力,為了共同的利益而犧牲的能力,誠實、善良和守信的能力,以及創造性和自我激勵能力是更重要的。一個明智的社會會獎賞具備這些能力和特質的人,不會讚美企業顧問的技能,而輕視家庭護士的技能。
糾正這一體系的唯一方法是通過制度改革。例如,我們需要更多的成功途徑,所以那些不傾向於學術的人有通往社會領導層的途徑;使有和沒有大學學位的人彼此之間有更多的直接聯繫。終結像住宅分區條例這樣將富人隔離在頂層的政策。更廣泛地說,改變這種分類機制需要改變我們整個的道德生態,這樣,擁有斯坦福學位的人就不再被視為更高層次的存在。

波波族一開始並沒有想要成為精英統治階級。他們只是讓自己適應一個獎勵某種成就的體系,然後讓自己的孩子們也能在這個體系中茁壯成長。但是,他們忽視了自己的力量,造成了巨大的不平等——經濟上的不平等,以及令人更痛苦的尊重上的不平等。我們面前的任務是廢除養育我們的制度。
♦ 專文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