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篇文章轉載自 。若有侵害著作權,請速告知,我們將盡速移除 ♦
2024/7/16
吳衢註:J·D·萬斯將成為川普2024年大選的競選夥伴,即副總統候選人。此人早在2016年出版的自傳著作《鄉下人的悲歌》也被重新挖掘了出來。事實上,萬斯當年正是因為此書一炮而紅,走入大眾視野,只不過彼時他還是川普的反對者。 2017年該書在國內翻譯出版。彼時國內剛剛「發現」「紅脖子」這群人(其實不比美國人晚太多),因此這本書就成了了解的關鍵。然而當時讀了這本書的我基本上沒留下什麼記憶,並不是什麼嚴肅的社會科學討論,倒是重新強調了可以「往上爬」的美國夢。除了作者的導師是「虎媽」之外,就記得作者要求「不能廢除小額高利貸,要是廢除了小額高利貸我們鄉下人就沒有任何出路了」。如今作者變成這樣,對於我來說是不意外。
不過,仍然值得回顧下當年的一些討論,尤其是左派給予的批評。本文翻譯了兩篇批判性書評,分別是發表在《衛報》上的Hari Kunzr u的Hillbilly Elegy by JD Vance review – does this memoir really explain Trump's victory?和《雅各賓》上的Bob Hutton的Hillbilly Elitism,供讀者參考。
此外,這本書原名為Hillbilly Elegy,Hillbilly本推送翻譯為“鄉巴佬”,但是其中的“山地”含義值得注意,這和原書的阿巴拉契亞山區有所聯繫;而Elegy一般翻譯為「輓歌」。關於這兩個翻譯在《雅格賓》的書評中都有所討論。但由於中譯本翻譯為《鄉下人的悲歌》,因此一旦出現書名,以中譯本書名為準。
原文連結如下: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6/dec/07/hillbilly-elegy-by-jd-vance-review
這本回憶錄真的解釋了川普的勝利嗎?
作者:Hari Kunzru
有些書可以透過閱讀文本本身被理解,而有些書則幾乎不可能脫離其時代的政治文化爭論去做出評價。 2016年6月,就在美國大選的幾個月前,一位年輕的矽谷投資經理出版了一本工整的回憶錄,一躍而起成為了《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第一名。 J·D·萬斯(Vance)在俄亥俄州鐵鏽地帶的貧寒中長大——據他描述,自己家庭是極不健全的。書中,他描述了自己如何克服重重困難,進入耶魯大學法學院深造,並取得了豐厚的收入。這本書沿襲了「倖存者故事」(survivor story)的體裁,這種體裁在美國的自我對話/反省中佔有一種特殊地位。在階級流動性停滯不前的當下,萬斯是個統計上的異類(一個倖存者-譯者註)。他本來不應該有機會離開俄亥俄州的米德爾敦(Middletown)。他把自己的成功歸功於運氣、性格和被稱為「姆媽(Mamw)」的祖母帶給他的相對穩定的生活。
「姆媽」和「阿爹(Papaw,即祖父)」是18世紀和19世紀定居於肯塔基州東部山區的白人後裔。在大蕭條期間,許多來自阿巴拉契亞地區的移民走出山區,湧入北方的工廠。萬斯家族則居於其後,作為第二波戰後移民潮的一部分來到了米德爾敦,一座圍繞著一個巨大的鋼鐵廠發展起來的小鎮。阿爹(儘管是個暴力的酒鬼)在美國軋鋼公司(American Rolling Mill Company)工作期間過得還不錯。然而,隨著重工業向東亞轉移,這家公司和依賴它的小鎮都遭遇了嚴重衰退。隨著萬斯逐漸成長,公司承辦的社交活動和豐厚的退休金也慢慢褪成遙遠的記憶。

萬斯自幼便沒怎麼見過父親,而他的母親則是一個行事無常又忽視孩子的家長,並且有著酗酒和藥物濫用的問題。他被迫去適應「接踵而來」的繼父,直到在姆媽那裡找到了避風港。萬斯和她一起生活,直到他決定離開米德爾敦去加入海軍。在經歷了伊拉克的軍旅生活和俄亥俄州立大學的本科教育後,萬斯被耶魯大學法學院錄取,這打開了躋身美國社會上層的門。
在書的後半部分,他列出了「我到耶魯法學院時不知道的事情」的清單,裡麵包括「面試時需穿著正裝」和「金融是一個人們從事的行業」。他用一個小插曲來描繪自己的外來者形象——在一次重要的面試晚宴上,他因為「從未見過這種飲料」而把一杯氣泡水吐了出來。他也把自己定位為一個從醫學或心理意義上於自己的過去中「倖存」下來的人,這段過去讓他經歷了間歇性的暴力衝動和情緒隔離的發作,對他的婚姻造成了許多問題。由於不願意去看心理醫生,他自我診斷為擁有過激的「戰鬥或逃跑反應」(fight-or-flight),據說這是一種對他混亂且暴力童年環境的壓力反應。
萬斯在書中也偶爾採取了更具學術性和少些個人色彩的寫作,在這個過程中,他將自己的私人故事與對他“鄉巴佬”族群“意外般富有凝聚力的文化”的粗略民族志結合了起來。他自稱為“蘇格蘭-愛爾蘭裔”,並特別將“大阿巴拉契亞”地區(“Greater Appalachia”)的人與“東北部的WASPS”(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s=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做了區分。這是一個非常要緊的區分,這正是一種在唐納德·川普復仇主義(revanchist)身份政治中被有效動員了的「非法白人」認同(outlaw whiteness)。雖然書中沒有描述萬斯妻子的背景,但她有一個印地語名字烏莎(Usha),這為這種身分認同增加了一個未被有效認識的複雜面向。

萬斯認為鄉巴佬文化是一種有毒的文化,並真心希望其中的許多問題能得到解決。身為青少年,他曾在雜貨店當收銀員,觀察鄰居的購物習慣。那些貧窮的人時常被「瘋狂積壓的壓力」所驅動,不得不購買那些冷凍即食食物;而富有的人則會有條不紊地購買新鮮農產品,並且可以大量賒帳。萬斯寫道:「我討厭這種感覺,我的老闆認為我們的人比那些用凱迪拉克拉貨回家的顧客更不可信。但我克服了這種感覺:我告訴自己,總有一天,我也會有帳可賒。當回想起自己的一些「食物券顧客」在利用福利系統,轉售汽水換取現金,並持有如手機這樣的奢侈品時,他這樣寫到:「我永遠無法理解,為什麼我們的生活感覺像是一場又一場的掙扎,而那些依賴政府施捨的人卻享受著那些我只能夢寐以求的玩意」。
萬斯在書中關心的是“我們的生活”,而這個“我們”正是他書籍取得巨大成功的關鍵。這本書落入了一場全國性的激烈爭論中,把定義模糊的「白人工人階級」與同樣模糊的「沿海精英」對立起來,彷彿他們是美國政治舞台上的遜尼派和什葉派。評論界對川普獲得越來越多的支持感到困惑,因為川普看起來顯然不符合候選人的標準——他的競選看起來更像是惡作劇,而非認真競逐白宮的嘗試。但萬斯,作為一個口齒伶俐且真正來自阿巴拉契亞的人,成為了有線新聞界的常客,成為關於「另一個美國」的一種本土的、民族誌的消息來源。
萬斯,不出意料地,是共和黨人。他在耶魯大學的導師包括布希時代的演講稿撰寫人大衛·弗魯姆(David Frum)和「虎媽」法學教授艾米·蔡(Amy Chua)。他是米斯瑞爾資本(Mithril Capital)的合夥人,與該公司的聯合創始人,那位自由主義億萬富翁兼川普顧問的彼得·蒂爾(Peter Thiel)有著緊密合作。他的書中包含了許多聳人聽聞的「白人垃圾」墮落故事,而這通常被與政府的腐敗作用聯繫起來。 「每兩週我都會拿到一張小小的薪資單,看到上面寫著我的薪水裡扣除掉的聯邦和州所得稅。幾乎同樣頻繁的是,我們的毒癮鄰居會買T骨牛排,那是我自己窮得買不起的。

正如不止一位評論員所指出的那樣,萬斯關於鄉巴佬病理現象的故事,奇怪地讓人聯想到裡根年代用來攻擊黑人並為削弱社會安全網辯護的“福利女王”故事。他滿足於透過心理學和「文化」來解釋白人病態的問題,但對於結構性經濟不平等卻顯得不那麼關注。在文化方面,他寫道:「我們揮霍無度,最終陷入貧困……我們的家裡一團糟。我們像在看橄欖球比賽一樣對彼此大喊大叫。家庭中至少有一個人吸食毒品……」在心理學方面,他說:「這裡並不存在主觀能動性,而只存在一種對自己的生活失去了控制的感受,以及傾向於把責任歸咎於除了自己以外的所有人。」他將自己在加入海軍陸戰隊之前的狀態稱為一種「習得無助感」(“learned helplessness”)。
萬斯捕捉了美國白人內部的階級斷層,但作為新政治格局的指南,《鄉下人的悲歌》卻顯得不夠均衡。
自從川普獲勝以來,萬斯的書獲得了不同的意義,至少是在某些「浴血奮戰而又幾近陷入迷茫」的中左翼自由派評論員中間,這些人在競選期間曾尋求萬斯的建議。在這些圈子裡,突然出現了一種普遍的看法:民主黨之所以失敗,是因為未能充分關注白人工人階級的擔憂,而過於關注所謂的“身份政治”,即LGBTQ群體和有色人種的代表權和定義。在一篇廣泛討論的《紐約時報》文章中,馬克·利拉(Mark Lilla)呼籲“後身份自由主義”(“post-identity liberalism”),這種政治立場聚焦於羅斯福著名的“四大自由」(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其中「身分認同」問題應「安靜、敏感且適當地被處理」。對於一些評論員來說,這暗示了他們可以通過將少數族裔排到“公車後排”的方式來安撫萬斯的“我們自己人”。
對此觀點有相當大的反對聲音,特別是那些質疑為什麼這種新的、好的「身份政治」(讓我們去理解這些被剝奪的白人!)會成為治愈舊身份政治——導致了希拉里·柯林頓失敗——良方的人。這種「應該由精英自由派來做出一個非此即彼——白人工人階級,還是少數族裔——的選擇」的認識是荒謬而居高臨下的。美國的經濟困境並不會去關心種族界線:在歐巴馬任期內受害的不僅是銹帶的年長白人藍領工人,還有在零工經濟中被剝削的城市千禧世代。無論是警察暴力、環境正義,或是醫療保健的取得都與代名詞(身分)幾乎無關。那些希望了解美國白人內部階級斷層的讀者將會從萬斯關於階級流動性的敘述中獲得啟發,但作為對新政治格局的指南,《鄉下人的悲歌》卻顯得如此不平衡,其對作者真實意圖的模糊處理也讓人感到困惑和沮喪。

鄉巴佬菁英主義?
作者:Bob Hutton
JD Vance的《鄉下人的悲歌:危機中的家庭與文化回憶錄》(Hillbilly Elegy: A Memoir of a Family and Culture in Crisis)受到了人們的強烈推薦:《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執行主編雷漢·薩拉姆(Reihan Salam)、矽谷富豪彼得·蒂爾(Peter Thiel,Paypal的創立者。)和「虎媽」艾米·蔡(Amy Chua)都在腰封上大加讚賞。此後,保守派媒體,包括薩拉姆的《國家評論》(萬斯經常為該雜誌撰稿)、《美國保守派》(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和《每週標竿》(the Weekly Standard)也都紛紛發表了積極的書評。大衛布魯克斯(David Brooks)在《紐約時報》的專欄文章中盛讚《鄉下人的悲歌》,認為這是一種「更好的民族主義」。
右翼的支持並不令人意外。畢竟,萬斯自己就是他們的一員,而《鄉下人的悲歌》則堅定地捍衛了資本主義一直以來用於贏得底層民眾支持的「自力更生」的童話。
但當然,這本書並不是面向底層人民的(很少有書是寫給底層人的),而是針對中上層讀者的,他們很樂於見到美國白人的貧窮與他們無關,也跟美國經濟和社會的任何結構性問題無關,而只和窮人與生俱來的惡習有關。
白人貧民區
考慮到《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才對農村白人下層階級進行了攻擊,萬斯這本書的出版時間就顯得很有趣了。凱文-威廉森(Kevin Williamson)在2014年對肯塔基州歐斯利縣(Owsley County)貧困狀況的考察——該縣毗鄰萬斯的出生地佈賴特希特縣(Breathitt County),也是《鄉下人的悲歌》的主要背景之一——可謂是該雜誌的一種出櫃,呈現了雜誌對這一階層及其所謂的自我墮落的蔑視。
在白人工人階級湧向唐納德-川普的復仇主義「悲情民族主義」(revanchist sado-nationalism)之後,該雜誌突然對這個曾被歡呼為「雷根派民主黨人」的群體惡言相向。像傑特-希爾(Jeet Heer)這樣的觀察家顯然將《國家評論》這種對窮白人的蔑視與他們對川普正在接管美國保守主義的擔憂聯繫在了一起,他們對這事態的發展可不太高興。
因此,萬斯被暫時徵用了,他在廣播台和電視台四處奔走,試圖解釋川普對像他這樣的「鄉巴佬」美國人的吸引力。不管有沒有川普,《國家評論》的保守派決定展示他們之前隱藏起來的對墮落白人的厭惡。
從表面上看,《悲歌》的描寫與威廉森公開的惡毒攻擊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但萬斯同樣認為,貧窮的白人受到其退步文化的束縛。讀完《鄉下人的悲歌》,你會發現「美國夢」是萬斯最喜歡的短語之一,但他很少解釋這個短語,而是讓讀者自己決定這個短語的含義。萬斯的出版商稱這本書是「從阿巴拉契亞到耶魯大學法學院的幾代人的旅程——兩個世界不能隔得更遠了」。

透過強調兩個世界間的距離,萬斯可以更好地推進本書的論點:他的成就來自於勤奮工作,以及由「鄉巴佬」祖父母(與他放蕩不羈、濫用藥物的父母形成鮮明對比)提供的相對規範的家庭環境向他灌輸的傳統價值。萬斯的個人經歷使他能夠自稱“鄉巴佬”,然後斥責他的鄉巴佬同胞在文化和道德上的敗壞。
“責怪除了自己以外的所有人”
「鄉巴佬」(Hillbilly)是大多數美國人都熟悉的一個詞,其歷史至少可以追溯到鍍金時代。歷史學家安東尼-哈金斯(Anthony Harkins)在《鄉巴佬:一個美國形象的文化史》(Hillbilly: A Cultural History of an American Icon)一書中解釋說,「鄉巴佬」只是「幾十個類似的標籤之一......是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的評論家們對貧窮和工人階級南方白人的意識形態與圖像建構,北方人和南方人都用這個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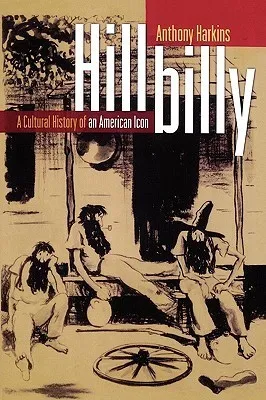
諸如此類的稱謂讓“非農村、中產階級、白人、美國”觀眾能夠“想像一個浪漫化的過去,同時也讓這同一群觀眾能夠......嘲諷前現代、不文明社會的負面問題" 。同時,農村白人「重新奪取」了這個以及其他類似的詞(如紅脖子、刷子猿(brush ape)、窮白人垃圾、蹩腳鬼),"作為本階級和種族乃至自豪感的身份標誌" 。
哈金斯解釋說,“鄉巴佬”一詞之所以能在多元文化時代大行其道,是因為“鄉巴佬的白人身份......使這一形象成為一個看似去政治化的場域”,“ [白人]製片人可以在這裡描繪貧窮、無知和落後的形象,而不會引起民權倡導者以及黑人和少數族裔社區對其偏執和種族主義的抨擊"。
一個多世紀以來,「鄉巴佬」一詞被廣泛使用,但可能從未被用於非白人。它不僅用來表示白人,還暗自承認了種族內部的等級制度(不言而喻,由於拒絕布爾喬亞的行為模式,鄉巴佬處於這個種族內部的最底層)。

萬斯在導論中闡明了他的論點:美國白人自己無法控制的條件給他們帶來了經濟困難,但他們先在的「鄉巴佬文化」決定了他們「用最糟糕的方式應對身處其中的糟糕環境"。
“人們缺乏主觀能動性”,萬斯寫道,“感覺自己幾乎無法控制自己的生活,願意責怪除了自己以外的所有人”。白人,尤其是年輕的成年男性,面對經濟危機的反應是暴力或藥物濫用,而不是逃離「與社會隔絕」的環境,比如像萬斯那樣,透過一直勤奮工作、多才多藝的祖父母的支持,去耶魯大學法學院深造。
故事沿用了霍雷肖·阿爾傑(Horatio Alger ,美國小說家,其作品風格大多一致,均描述著一個貧窮的少年是如何通過其正直、努力、少許運氣以及堅持不懈最終取得成功。——譯者註)的模式,在歌頌「鄉巴佬文化」優點的同時,也抨擊了它的缺點。萬斯利用了克里斯多福·拉許(Christopher Lasch)曾稱之為「懺悔式」(confessional style)的寫作手法,但採取了相反的形式。拉斯奇抨擊懺悔者尋求的「不是對現實的代表性片段進行客觀描述,而是引誘他人給予他關注、讚譽或同情」。
與此相反,萬斯不僅聲稱他客觀地敘述了自己的傳記,還聲稱它是白人工人階級經驗的縮影。如果有經驗證據顯示他的經驗是例外而非常態,他總能回到「《鄉下人的悲歌》只是他個人的『旅程』」這一立場——這對於任何想要批評他的人來說來說都是一個絕妙而又令人惱火的悖論,因為他們可能會把他的論點理解為“鄉巴佬”這一群體(但作者可以聲稱這討論的是“他”的事情,所以可以規避這種批評。

萬斯和他的家人稱自己為鄉巴佬,因為他們居住在「大阿巴拉契亞」地區(Greater Appalachia)——他借用了(但沒有註明出處)科林·伍德沃德(Colin Woodard)的「十一民族」理論(「Eleven Nations」)(雖然他確實引用了小漢克威廉斯(Hank Williams)的話來支持自己的觀點)。萬斯不加批判地使用"鄉巴佬"來形容肯塔基州傑克遜市(Jackson, Kentucky)和俄亥俄州米德爾敦市(Middletown, Ohio ,該城有11%的人口為黑人,基本上達到全美平均水平。— —譯者註)的人們,並效法伍德沃德,將研究對象的白人身分視為既定事實。他在書中很前面就說不需要討論種族問題:「我確實希望這本書的讀者能夠從中領悟到階級和家庭是如何影響窮人的,而不用透過種族棱鏡來過濾他們的觀點」。
這段話的前五頁,萬斯認定「鄉巴佬文化」是當地居民「蘇格蘭-愛爾蘭」(「Scots-Irish」)種族認同的產物,這種文化對他們來說包括了「貧窮是家族的傳統”,“強烈的忠誠感”和“對家庭與國家的強烈獻身精神”,並且通過仇外心理和好鬥的傾向進一步發酵。萬斯撇開了該地區的經濟困難和磨難——更不用說印第安戰爭或奴隸制了——認為是這種民族性從根本上塑造了該地區。
他引用了一篇2012年的《發現》(Discover)文章來證成他那嚴重去歷史化的對「蘇格蘭-愛爾蘭人傾向」的描述,但他的總體看法與吉姆·韋伯(Jim Webb)的《生而戰》(Born Fighting),還有歷史學家戴維·哈克特·費舍爾(David Hackett Fischer)、福雷斯特·麥克唐納(Forrest McDonald)和格雷迪·麥克維尼( Grady McWhiney)的著作如出一轍。後兩人都擔任南方白人民族主義聯盟(white nationalist League of the South)的負責人,該組織持續擁護南方白人社會的「凱爾特論」。

萬斯的這項分析帶有種族決定論的味道,即使在他的論述中「文化」取代了生物學。此外,他的論點也陷入了與理論其他支持者相同的循環邏輯。在他們為論文集《新保守主義:批判性導論》(Neo-Confederacy:A Critical Introduction》所撰寫的文章中,尤安·黑格(Euan Hague)和愛德華·塞貝斯塔(Edward Sebesta)將凱爾特(或蘇格蘭-愛爾蘭)文化被描述為一堆要素,「可根據任何意圖進行重新詮釋和挪用」:
不符合給定的那種「凱爾特文化」的元素可以被省略,而其他元素(如暴力傾向)則可以被大肆宣揚。因此,某種特定行為(如暴力)被視為個人實踐凱爾特文化的證據,這成了「自我實現」:表現出凱爾特人行為的人是凱爾特人,因為他們表現出的行為是凱爾特人的。這不僅假定了凱爾特文化是同質的,而且還暗示了人們在世界上的所作所為受制於他們的文化。
但萬斯現在在矽谷工作,在那裡,支持新保守主義被認為是粗魯的,所以上面引用這種說法不太可能解釋他使用韋伯、麥克唐納和麥克維尼的原因。相反,蘇格蘭-愛爾蘭人、鄉巴佬,甚至“文化”一詞都是作為一種縮寫(shorthand),與探討阿巴拉契亞具體的貧困問題相比,它們讓故事變得簡單得多。
畢竟,蘇格蘭和愛爾蘭移民的子孫後代生活在美國各地;他們與其他族裔的後代通婚;他們既可能富有,也可能貧窮。然而,在肯塔基州東部,不管是什麼族裔,當地人都遭受可追溯到十九世紀的貧困。
而大阿巴拉契亞地區居民所經歷的問題在全國也都存在。可以肯定的是,那些工資異常低、基礎設施不存在或癱瘓的地方——如肯塔基州的傑克遜和俄亥俄州的米德爾敦一樣的地方——經歷的問題會更為嚴重。

托馬斯·弗蘭克(Thomas Frank)將此稱為“美國大部分地區的逐步阿巴拉契亞化”(gradual Appalachification):在遠離萬斯目前居住地舊金山——美國最紳士化的城市——的地方,工資和期望值趨於遲滯不變,但這肯定不僅限於俄亥俄河流域的美國白人。萬斯對貧窮的看法有著嚴重的種族和地域局限,這限制了他理解貧窮的能力。
即使他真的認為阿巴拉契亞的貧困在某種程度上是特殊的,他也沒有深入研究這一主題的豐富學術成果。社會學家德懷特·比林斯(Dwight Billings)和凱瑟琳·布利(Kathleen Blee)對肯塔基州克萊縣(Clay County, Kentucky)進行了細緻的研究,其著作《通往貧困之路:阿巴拉契亞的財富與苦難的形成》(The Road to Poverty: The Making of Wealth and Hardship in Appalachia)表明,精英家庭主導了當地的工業和政治,為內戰前長期的低工資經濟奠定了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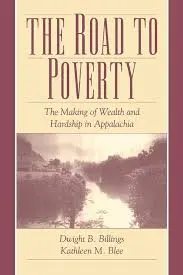
同樣,歷史學家約翰·R·伯奇(John R. Burch)的《肯塔基州歐斯利縣與貧困的永續》(Owsley County, Kentucky, and the Perpetuation of Poverty)一書也對威廉森所諷刺的同一個縣做出了類似的結論(伯奇本人並不是福利國家的忠實捍衛者,他也展示了當地精英如何利用新政和「偉大社會」計畫來達到自己的卑鄙目的)。
與《鄉下人的悲歌》不同,在這兩本書中,人們的具體行為——尤其是富裕白人對當地政治的掌控——解釋了肯塔基州東部普遍存在的極度貧困。反過來,「鄉巴佬」們是在他們無法控制的霸權和市場條件下受苦受難,而不源自於祖先的律令。
當然,威廉森和萬斯都沒有考慮這些作者,也許是因為這些學者認為肯塔基州東部居民最大的錯誤並不像萬斯所說的那樣沉湎於貧困,而是追隨了經濟精英的腳步。
相反,《鄉下人的悲歌》讓我們回到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邁克爾·哈靈頓(Michael Harrington)、奧斯卡·劉易斯(Oscar Lewis)和丹尼爾·帕特里克·莫伊尼漢(Daniel Patrick Moynihan)所推廣流行的「貧窮文化」理論。尤其是莫伊尼漢,他被指責其建議是基於對黑人家庭內在的種族主義成見,這些成見涉及單身母親、遺棄兒童、吸毒和其他形式的恣意妄為,萬斯在他的個人敘事中也詳細描述了這些成見。
用哈金斯的話來說,由於他們的白人身份,這些對氫可酮上癮的「紅脖子」形象與政治格格不入。與所有其他美國人一樣,萬斯的研究對像也是按照他們是作為生產力的工人來分類的。作者擔心的是,他們已經不再是以前那麼有生產力的工人了。

凱文威廉森(Kevin Williamson)等保守派人士可以支持萬斯的論點,因為資本主義需要底層賤民。自由派也可能感興趣,因為他們不認為「鄉巴佬」是他們的政治盟友,而且在田納西州諾克斯維爾(Knoxville, Tennessee)這樣的城市,當學者搬到鄉巴佬的社區時,他們也不會好好清理院子(不只一位自由派同事是這麼跟我說的)。
萬斯的解決方案反映了他有些溫和的中右派政治承諾。他建議「以一種不會把窮人隔離成小飛地的方式」管理學校代金券(以代金券代替貨幣來支付學費,是美國的一種社會保障形式。——譯者註),這樣窮人家的孩子就可以學習模仿富裕的同學。他也以鄉巴佬大家庭發揮的「巨大作用」為由,建議社會服務部門放寬對寄養父母的規定,讓祖父母、姑姑和叔叔可以幫助瀕臨絕境的孩子。 "他寫道:「我們國家的社會服務並不是為鄉巴佬家庭打造的」。
這是一個有些古怪但相當無害的想法。但萬斯從未建議肯塔基州和俄亥俄州的居民可以從更高的工資、更好的醫療保健或復興的勞工運動中受益。
這些建議會幹擾萬斯寫作《鄉下人的悲歌》的目的。這本書主要是一部自我慶賀的作品,是文學上的勝利之旅,也是對最低限度安全網(minimalist safety net,指保守派對社會保障的要求為“最低限度安全網”。——譯者註)的辯護。大衛布魯克斯(David Brooks)是這本書的粉絲,這一點也不奇怪。
居高臨下的態度壓倒了萬斯對家人和家鄉「瘋狂的鄉巴佬」的愛。他的書最終說明了資本主義及其捍衛者所需要的那種矛盾:任何勤奮工作的人都可以升到頂層,但在任何時候,都必須有更多的人留在底層。
《鄉下人的悲歌》的名字起錯了。哀歌是獻給死者的詩(原文的Elegy一般譯為「輓歌」。-譯者註)。美國鄉巴佬並沒有死,他只是窮。這本書的名字應該叫《鄉巴佬的訓斥》(Hillbilly Reprimand),因為萬斯並不想悼念鄉巴佬──他想讓鄉巴佬成為一個好工人。

♦ 專文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