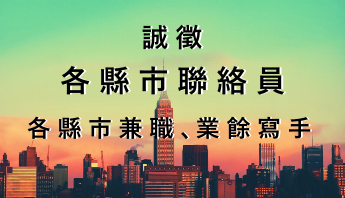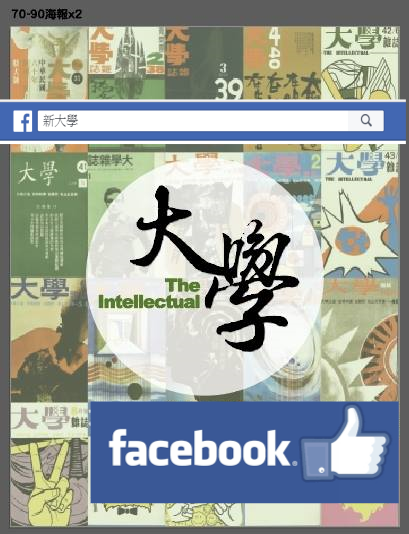♦ 本篇文章轉載自 亞洲週刊。若有侵害著作權,請速告知,我們將盡速移除 ♦
2025/2/10
台灣北一女國文教師區桂芝痛批108課綱去中國化,削弱學生國文能力和史觀、道德弱化,源於前總統李登輝和台獨學者主導教改,孕育「天然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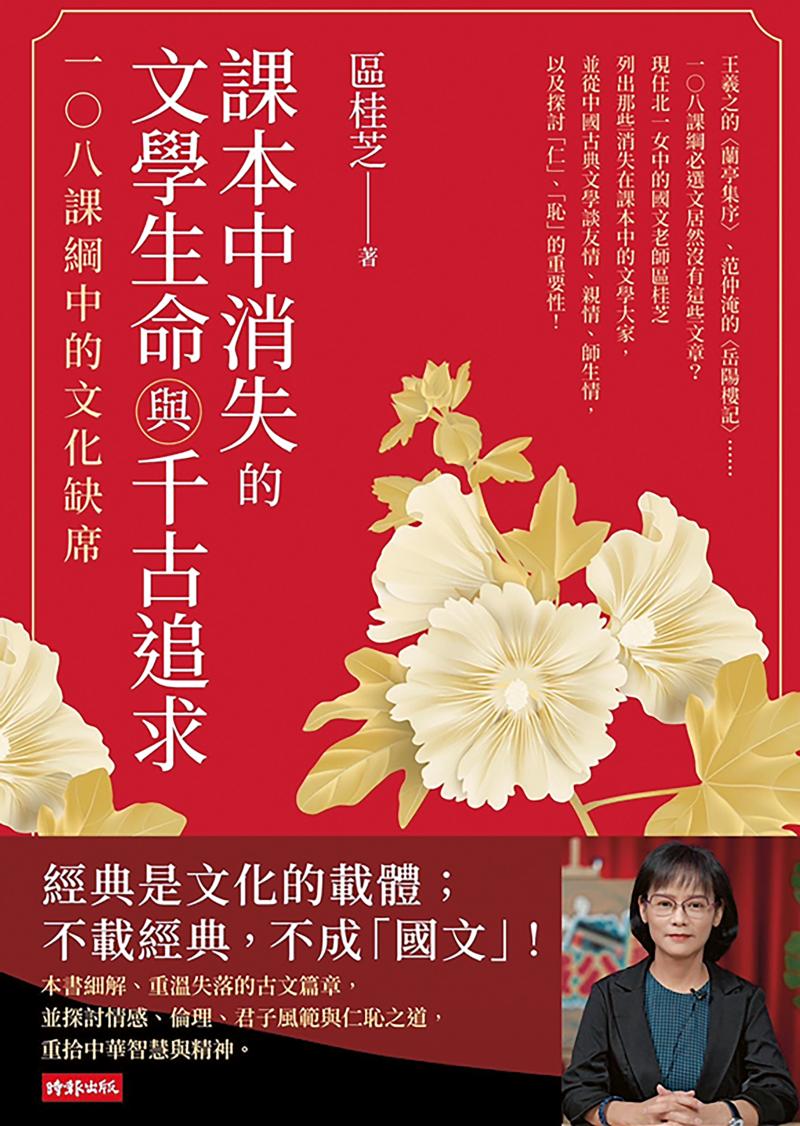
區桂芝出版新書:號召更多人加入文化抗爭
台灣教改三十年毀譽參半,批評聲浪不斷。其中的指標性人物台北第一女中(北一女)國文教師區桂芝痛陳:「一零八課綱是三十年教改滅台的最後一哩路。」此課綱首次整合國小、國中與高中為十二年一貫,強調終身學習,但其「去中國化」內涵備受爭議,試圖削弱學生對中華文化的認同,進而改變年輕世代的歷史觀與民族意識。
批評者認為,一零八(二零一九年)課綱割裂台灣與中華文化的連結,可能削弱學生的文化自信,進而引發國家認同危機。他們指出,該課綱過於強調「本土意識」與「台灣價值」,忽視歷史的完整性,恐使學生迷失方向,缺乏對全球化視野與文化融合的理解。
很多人批評一零八課綱,但很少人像區桂芝這麼犀利,直指問題核心。二零二三年十二月,這位北一女教師公開批評一零八課綱為「無恥課綱」,引發廣泛關注。她指出,課綱刪減文言文比例,削弱學生的語文能力與價值觀教育。以刪除顧炎武《廉恥》為例,她批評學生將不再理解「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導致道德觀念模糊、價值觀錯亂。她痛斥課綱無法培養學生正確認識恥辱與國恥,反而助長不清不白的社會風氣。
她直言課綱內容背離了教育的初衷,甚至對台灣的未來造成危害,這一番話讓這名敢言的國文老師迅速成為焦點人物。許多家長支持她的勇敢發聲,認為她道出了普遍的不滿與擔憂。更有美國僑社邀請她演講,分享教育改革見解,並主動捐款支持,彰顯其言論在台灣教育界與僑界引發的共鳴與認同。
但區桂芝的批評觸動綠營敏感神經,民進黨網軍與側翼展開污名化攻擊,指責她「認同中國」,稱其為「偽裝成國粹派的戰狼老師」,還暗示她多次到訪大陸,影射其動機不單純,試圖混淆她的教育與政治立場,以削弱其公信力。這場圍剿行動無形中放大了區桂芝的影響力,也讓更多人開始重新檢視一零八課綱「去中國化」背後的爭議與意圖。
區桂芝近日出版《課本中消失的文學生命與千古追求》(時報出版),集結她多年來對一零八課綱的研究心血,批評其對台灣教育與文化認同的影響。她將此形容為一場「戰爭」,並認為自己有責任站出來,號召更多人加入對抗行列。為了讓聲音被更多人聽見,她深知媒體報道的重要性,坦言:「媒體也要你有辛辣的標題。」因此,她的發言愈發犀利,用詞直接尖銳,以吸引更多關注。
她坦承,這樣的言論背後不僅是對媒體需求的回應,更是內心強烈激憤的自然流露。「如果今天我沒有出這個名,我只能夠默默地守在學校裏面,我也就罷了,我的憤怒只能自己體內在燃燒。」她的話透露出一種無奈與使命感:如果她選擇沉默,那麼她對教育現狀的批判與憤怒便無法帶來任何改變,而站出來則是她將內心的憤怒轉化為行動的方式,也是一種對抗無力感的自我救贖。
區桂芝鮮明而尖銳的立場,使她成為教育界備受矚目的爭議人物。許多教師選擇與她保持距離,避免因其激進言論而引發爭議或壓力。不過,仍有部分教師私下支持,對她的勇氣與堅持表示認同與敬佩,儘管不敢公開表態。

區桂芝:橫眉冷對千夫指(圖:中央社)
面對孤立處境,區桂芝坦言自己如同一隻「孤鳥」,但深知僅憑一己之力難以改變現狀,期望號召更多志同道合者捍衛教育正義。她說:「孤鳥成不了事,還是希望呼群保義。」以下是區桂芝接受亞洲週刊訪問的內容紀要:
你認為一零八課綱是三十年教改滅台最後一哩路,好像是說執政民進黨有什麼陰謀?
一零八課綱的精神和它所彰顯的目標,其實是延續過去教改的主張。然而,以往的教改雖然有爭議,但在歷史課本上並沒有完全打亂時序,也沒有以議題為主軸,更沒有像現在這樣大幅刪減課程內容。但一零八課綱的改動尤其在歷史這一部分特別明顯。從夏商周到唐宋,這一千多年的歷史現在課本中的篇幅只剩下一千多字,這讓學生根本無法建立任何完整的歷史觀,甚至連基本的常識都無法掌握。
在國文的部分,文言文的學習也受到了重大影響。過去的教改雖已削減了文言文篇幅,但還保留了三十篇,但一零八課綱直接將文言文篇幅減少到十五篇,同時國文的授課時數也被削減。這種做法其實反映了一零八課綱的一致精神,只是手段變得更加激烈。
以往的課綱雖然也有改動,但並未被認為是「去中國化」,因為歷史內容還沒有被如此大幅度地改動。然而,一零八課綱之所以被認為是「去中化」,正是因為它對歷史內容進行了如此顛覆性的處理。我認為這樣的改動對學生的文化認知與歷史觀產生了極大的破壞,這才讓人感到擔憂,認為這可能是一場更深層的操作,甚至有可能是執政黨在文化層面的一種政治布局。
老師對一零八課綱的反應是否和你一樣?
起碼我所接觸到的大部分老師,對一零八課綱的反應是相似的。雖然一般老師可能對「去不去中」這類議題並不特別在意,但在歷史科的領域裏,老師們因為意識形態的差異,對課綱的看法有不同的意見,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對。不過,即使如此,大多數老師在表面上並不表態。
至於其他學科的老師,他們的抱怨主要集中在課時被削減導致的問題。時數減少使學生的基礎能力下滑得非常嚴重,這讓許多老師感到挫折。此外,課時的縮減使得老師們無法深入講授課程內容,即使刪減了部分內容,課程進度依然無法完全跟上,常常需要「趕課」。這種情況不僅影響了教學品質,也讓老師們在教學工作中感到壓力和無奈。
為什麼會這樣子?
砍掉的時數去上其他課,因為一零八課綱其實就是延續教改,其實就是西方大概近二十多年來的一個思潮的主流,就是去中心化,所以反映在教育上面,他們要去學科本體意識,它強調跨科合作,所以不要再以學科為本位,要跨科合作,可是它沒有考慮到,學生們沒有基礎,跨科如何合作?再來就是說,既然強調跨科合作,又強調要多元學習,同時也要去學科本位,所以把學科時數砍掉之後,多出來的時間全部來上選修課,而這些選修課其實是考試不考的。
你一再批評現在課程內容「道德弱化」,是什麼意思?
道德弱化,主要是指教育課程中對道德與倫理教育的重視程度大幅下降。以往的小學課程中有「生活與倫理」課,國語課本中也包含許多關於忠孝節義的故事,但現在這類教材和課程被削減或取代,如「生活與社會」這類課程,卻未再強調倫理教育的內容。
在國中階段,以前的公民課稱為「公民與道德」,課程中第一課通常教授五倫(君臣、父子、夫婦、朋友、兄弟)的倫理關係,並進一步延伸至法律與社會層面的理解。但現在不僅課名改變,內容也已經完全剔除了這些倫理基礎的教育,甚至國文課本中與品德相關的文本也大幅減少。
此外,教育政策強調議題式討論,但因課本缺乏足夠的道德與倫理素材,學生對相關議題的知識與基礎理解不足,導致課堂討論流於表面化,無法進行深入或長遠的思考。教師因缺乏教材支持,也無法有效引導學生。結果,課堂討論變得空洞,時間被浪費,而道德教育的功能更加被削弱。
你覺得你所教的北一女的學生有學過一零八課綱跟過去的「九九課綱」兩者的差別在哪裏?
相比於九九課綱,我明顯感受到在一零八課綱下學生在尊師重道這方面的表現有所弱化。以班級經營為例,學生的自律和對課堂秩序的重視程度降低,老師在維持班級秩序面臨更多挑戰。學生上課時吃飯的情況變得普遍,這與他們課餘時間被大量課外活動佔用有關,導致學生中午無法正常用餐,只能將吃飯時間挪到課堂上。這種行為對課堂的專注度和學習效率都有負面影響,而教師對此也難以有效干預。
此外,社會風氣的變遷也影響了學生的行為。例如,在一零八課綱下,我注意到更多學生開始在課堂上化妝。我前一陣子在課堂上遇到一名學生,看到她一邊塗抹防曬油,一邊照鏡子塗塗抹抹,完全沒有專心聽課。當下我感到非常生氣,脫口而出讓她出去,但隨即意識到這樣的話可能會被認為侵犯了她的受教權。因此,我馬上補了一句:「請你出去到洗手間整理好自己再回來。」只能以這種方式圓場。
在一零八課綱以前,學生頂多在課堂上梳頭,但一零八課綱實施後,甚至開始有人化妝。還有老師提到,有學生竟然在課堂上畫眼線,他真是氣到不行,但也不敢講。
你說三十年教改造成無法復原的災難,為什麼會這樣?
我所謂的「無法復原」,是指學生的青春時光一去不復返,他們最黃金的學習階段就這樣被耽誤了。而學生往往自己並未察覺,因為他們沒有經歷過課綱改變前的教育方式,不知道自己究竟錯失了什麼。
現在許多人,包括部分社會人士,可能認為多元學習很好,也覺得選修課的增加為學生提供了更多選擇。例如,我曾在台灣電視傳媒人王偉忠的節目中聽到他提到,如果他讀書時有這麼多課程可以選,學校生活會變得更有趣。但他忽略了一個關鍵問題:學科基礎的奠定需要時間。如果學生的基礎尚未穩固,就急於讓他們進行多元選修,實際上是將大學的選修精神提前移植到國、高中,甚至小學階段。
這種做法沒有考慮到基礎教育的重要性。當小學、國中和高中都在強調多元學習,學生就幾乎沒有時間紮實建立基礎學科能力。教育部官員或許認為這並無大礙,因為他們自教改以來,一直強調建立「終身學習」的能力。他們可能相信,即使學生在校期間未學到足夠多的知識,也可以憑藉自主學習和終身學習的精神,在未來補足。然而,這忽略了基礎教育的缺失所造成的長期影響,這種損失是學生未必能靠後天學習完全彌補的。
台灣教改會變成這樣,你覺得誰要負最大責任?
如果要追本溯源,我認為最大的責任在於(前總統)李登輝。因為李登輝在權力穩固之後,結合了一些深綠的台獨學者,例如杜正勝、李遠哲等,他們在學術界和社會輿論中具有重要的引導作用。透過這些人主導教改,逐漸將教育方向導向他們所期望的意識形態目標。經過三十年的改變,現在我們可以清楚看到他們的目標已經部分實現。
在一零八課綱之前,學生的中國意識和中國認同就已經逐漸薄弱。這在國文和歷史等教科書中表現得尤為明顯,許多教科書在描述中國時採用「他者」的敘述方式。長期下來,學生自然將中國視為「他者」,並逐漸形成「一邊一國」的概念。這就是所謂的「天然獨」,但實際上,這種天然獨是透過後天教育逐漸灌輸出來的結果。
因此,很多人將過去三十年的教改形容為一場「潤物無聲」的台獨工程。這種形容很貼切,因為教改在不知不覺中,悄然改變了學生的意識形態,有人甚至稱之為「寧靜的文革」。我甚至將它誇大為一場文化戰爭,特別是中西文化的對立戰爭。因為這次教改中引入的許多教育概念來自西方,並且結合了台獨的意識形態,使其更具吸引力,尤其是對於那些對意識形態敏感度不高的人。
最終,我們看到這些教育改變對年輕一代的影響非常明顯,尤其是在意識形態和文化認同的塑造上,遠超許多人原本的預期。
亞洲週刊 2025年06期 2025/2/10-2/16
|
|
|
♦ 專文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