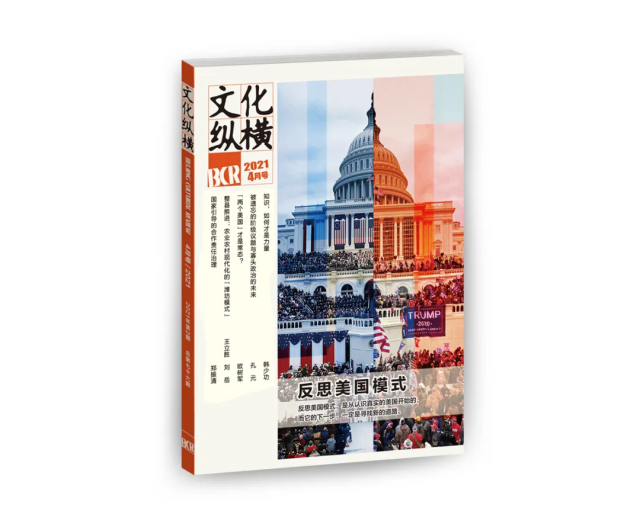♦ 本文內容轉載自 《文化縱橫》微信:whzh_21bcr ♦

✪杜維明 |北京大學
【導讀】近日某貼吧“裹小腳”圖片流傳網絡,引發強烈爭議。公眾質疑:為何今天還有此類陋習?一些人認為,這是漢服文化熱與短視頻流量雙重推力之下的譁眾取寵。也有分析指出,重拾“糟粕”的亂象,是當代傳統復興趨勢的一個異化變種。事實上,除了形式上的回歸傳統現象,向傳統尋求某種精神資源,也成為一種群體衝動:萬千碩博、海歸參加公考求取仕途,女德班暗地生長,商業化的國學熱......這構成了一個巨大的問號:歷經百年現代化之後,人們卻在集體無意識中選擇性地“回歸”傳統,這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
杜維明先生認為,五四運動以來,救亡壓倒啟蒙,為快速實現現代化,中國早期知識精英提出全盤西化的主張,在助推國家現代化的同時,也使民族對自己的傳統喪失信心。然而百年實踐之後,人們卻發現,中國的現代性價值並不能與西方理性完全接軌,中國的器物背後難以全然安置西洋的靈魂。決定中國現實生活之根本價值的,仍是這片土地上幾千年來一直隱隱作用的文化及價值觀——它們不被人們輕易察覺,卻無時無刻不影響著人們的行為選擇。面向未來,他提問:中國的傳統文化能否超越政治化的限制、去除糟粕,能否超越“從西方發展出來的現代性”,給世界帶來類似西方“人權”的普世價值?他認為,作為中國文化傳統支柱的儒家思想,是創造多元現代性的切入點。在傳統復興的大背景下,我們需要的並非儒家價值的回歸,而是儒家價值的重生。
本文原載於《文化縱橫》,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讀者參考。
多元現代性中的儒家傳統
▍從儒家的立場來反思啟蒙心態
20年來,我一直在考慮這樣一個問題:中國的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是否能夠超越政治化的限制、去除糟粕,走上現代化的道路,對西方的啟蒙作出回應,並與西方的現代價值相匹配?
張灝曾指出,現代化是對傳統的嚴厲批判,他提出要從傳統的價值角度來反思現代化。我的想法就是從儒家的立場來反思西方的啟蒙心態。關於啟蒙,西方很多學者將之作為一場運動,哈貝馬斯則認為它是一個還未完成的計劃。在這裡,我們既不把它當作還在發展的一個計劃,也不把它當作一種運動,而是看作一種心態。這種啟蒙心態不僅影響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它還孕育了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市民社會。此外,包括跨國公司、民間或官方組織,都與啟蒙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
舒衡哲和李澤厚指出,救亡壓倒了啟蒙,對此我基本接受。但我認為,更重要的是啟蒙被大多數甚至是全部知識分子認為是能夠使中國現代化的唯一道路。那麼,我們能否從儒家人文精神的角度對啟蒙做一同情的了解和批判的認同,我們是否能夠通過儒家的核心價值,對啟蒙所代表的核心價值做一些反思呢?
在這中間就出現了這樣一個預設:一個中西方間可以進行平等互惠對話的時代也許已經到來。之前的對話是不公平的,實際上,現在的對話條件也是不公平的,因為我們的力量太薄弱,特別是在文化領域。西方提出了“軟實力”的說法,我們也用軟實力,但是我認為這是值得商榷的。這個概念是約瑟夫·奈提出的,他認為僅衡量政治、經濟和軍事力量還不夠,還應包括文化力量,這種力量是軟實力,美國在這方面就相當強。中國提軟實力並不一定合適,一是因為我們這方面的力量太弱,比美國、歐洲或者日本都要弱很多,甚至美國一個局部地區的軟實力都比我們強;二是如果我們要推出軟實力,可能會招致更多“中國威脅論”的觀點。
五四運動時代中國的知識精英常常是把我們的糟粕與西方最核心的價值相比較,比如拿“抽鴉片煙”、“包小腳”、“蓄妾”、“等級制度”、“封建意識形態”和西方的“理性”、“自由”、“法制”、“人權”、“個人的尊嚴”作比較。我們本來就弱,這麼一比,我們就沒什麼民族自尊可談了,結果是對自己的傳統文化完全喪失信心。
傳統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它有很多陰暗面,但是我們在面對傳統的時候,不應該持一種全面否定的態度。五四時期大家對傳統的批判力度很大,然而,如果以粗暴的態度對待傳統,那麼在吸收西方價值上就不可能深刻,而如果只是膚淺地認識西方價值,結果很可能只是歐風美雨、比較表面的東西大行其道。
在對待傳統上,我們應該從四個向度同時進行,即對傳統同情地了解、發揚,對傳統進行批評,對西方的先進思想和製度充分引進,以及對歐風美雨加以排拒,它們是一體的,而不僅僅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問題。當我們把這四個向度變成兩個向度,就是古今之爭、中西之爭的問題,再把這兩個向度集中到一點,就是如何全盤西化。
譬如,胡適為什麼贊成全盤西化這種偏激的主張?正如胡適所言,假如我們現在說80%西化,那麼實際上只有3 0%,假如說100%,那麼實際上還達不到60%。後來他不再用全盤西化,而提出充分現代化。這些一流的思想家,他們對西方了解比較深刻,他們反傳統是因為愛國主義的激憤。
如今對西方的啟蒙,包括對啟蒙心態批評最嚴厲的,還是西方一流的學者,有解構主義的、環保主義的、女性主義的、後殖民主義的和多元文化主義的學者,他們發展出來的觀點應該是我們方法論據的重要參照。這是當前的基本情況。那麼,西方的自由、理性、法治、人權和人的尊嚴這些核心價值,能否與中國傳統特別是儒家傳統的仁、義、禮、智、信進行對話呢?具體而言就是關於對正義的理解、對責任的理解、對社會和諧的理解這些方面。
以前人們對亞洲價值的提法是有問題的,很多學者把亞洲價值等同於權威主義、裙帶關係、缺乏透明度、黑箱作業。但仁、義、禮、智、信,這些才是亞洲價值觀。如今,西方的人權觀念力量很大,成為普世價值,這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我認為當前出現了一個新的契機。大概從1968年開始,人類首次看到了地球全貌,它的礦物、植物、微生物、動物,還有水源、土壤、空氣,我們都一目了然。這一嶄新的視野使得各個宗教傳統都有了徹底的轉化。
舉兩個例子,一個是基督教,一是佛教。任何當代基督教的大師都不可能說,我們等待未來天國,地球是個凡俗的世界——應該是凱撒歸凱撒、上帝歸上帝,我們不要再照顧這個凡俗的世界了。佛教徒也不可能說,我們注重淨土、彼岸,對此岸、紅塵,我們可以不照顧了。所以,如何對地球——我們的家園有一個新的認識,我認為這是儒家最大有可為的地方,在儒家傳統中不存在超越突破,至少不能從超越突破看儒家的價值取向。所以,我認為儒家可能在此一世紀發展出一個寬廣的人文精神,可以針對啟蒙提出新觀點。
啟蒙心態存在兩個很大的缺失,一是從哈貝馬斯哲學裡看出的,就是對宗教掉以輕心,在科學主義大盛,強調發展科學理性之期,對宗教問題照顧不到。二是自然,它成為一個由人類來宰制的對象,天人合一或人與自然萬物一體的思想在這裡起不到很大的作用。因此,如今儒家倫理和啟蒙心態是不是有一個對話的可能?我們也有我們自己的強勢,雖然目前這個強勢可能是想像而非現實,但是想像和理想本身就有價值,能夠想像,我們知識的發展空間廣大。
所以,我現在想做一個對啟蒙的反思的研究計劃,它分成幾個部分,第一就是回到17、18世紀。據我們了解,西方的基督教傳教士,像利瑪竇他們把中國文化傳到西方,而這個時期中國文化內部也是波瀾壯闊的,不必說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和吳宗周這些人了。當時的中國,在伊斯蘭教方面也出現了幾位大師,如馬德新、王岱輿,還有劉智。這些思想家達到的思想水平,不僅完全可以和利瑪竇所謂的天主教世界的思想相比,和中國當時最重要的大思想家也可以相提並論,例如劉智的《天方性理》。因此,17、18世紀中國的思想界是非常活躍的。
第二是研究西方啟蒙時代的思想,特別是啟蒙思想家的問題意識。第三則是啟蒙心態到了中國以後的影響。在我們目前的文化傳統中,西方的因素遠遠超過我們自己的傳統文化,雖然現在各方面的國學院和儒學院都在發展,而且這也不會是靈光一閃、曇花一現的現象,但是很多傳統思想還無法真正深化。在國學和儒學復興的氛圍中,除了廣為流傳的大思想家外,再出一些比較有分量的思想家,這是我們大家共同努力的方向,也是每個人的責任。
如果將這個問題再細化,就是儒家傳統的創新和人文精神的發展問題,這既包括針對中國這個傳統,也針對西方的傳統。這個研究計劃至少需要三年準備時間才能起步,而且需要大家齊心協力,而不是少數幾個人可以完成的。西方有一個優點,他們有一批學者,可以說是西方最好的學者,特別重視對傳統及近現代思想家的反思,反思康德、反思福柯,每個人都成為反思的對象,但是他們反思的語境基本上都是歐洲中心論。現在他們剛開始比照中國,在此基礎上進行自我反思。我們也要比照他們的成果,為以後了解在中國發展的啟蒙心態,並為儒學的發展創造條件。
▍文明交流與儒學的發展
關於學習,英文裡有learning、relearning和unlearning,就是學習、再學習,但是對這個unlearning,我就不知道怎麼翻譯,即學習以後,把之前學的東西消解掉,否則無法進一步提升自己的知性和理性。現在的年輕人,他們的職業變化會很快,即使從事同一個職業,也在變。所以一定要“再學習”。但是,儒家的學習觀念是“學做人”,我常常引用法國哲學家哈達(Hadat)“精神磨煉”的觀點,這是一個更深層次的學習。
然而,現在遇到這樣一個問題,就是把信息、數據、知識和智慧的層面混在一起。一打開電腦,90%以上的信息都必須要拋棄,不然就找不到想要的數據。而知識是有系統性的,從認知論講,是指理性、知性,但最麻煩的是把知識與智慧混為一談。我相信如果沒有人生閱歷,體認之知即不可能,倒不是說年紀大一點就更聰明,隨著計算機和信息工程的發展,年紀越大可能越糟糕。但是,智慧是和體驗、人生閱歷有關的,是逐漸積累的。比如說,一位電腦專家,他體現的是聰明才智,平常我們不把這叫智慧,而一位歷史學家或哲學家討論一些問題,他可能是有智慧的一面的。所以,我認為學習的問題對我特別有啟發。
對話最重要的基礎是容忍,從容忍開始,並有承認,即接受對方的存在是不可消解的。但是承認要提升到尊敬,如果僅僅是承認,而沒有尊重,也是不夠的。只有尊重,才可以互相參照,有了參照才能互相學習。比如顧彬,他說中國沒有文學,這樣,侵略性就太強,就好比你告訴他德國沒有文學,那他一定和你拼命。但他說中國當代沒有嚴格意義的文學是有一定目的的,他要刺激乃至激怒我們,大家受到刺激,一定會反彈,這就不是對話而是吵架了。這樣其實沒有太大價值。這樣的例子很多,又比如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長期血戰,這是他們不能容忍,互不承認對方的存在,其目的就是要消滅對方,而現在感覺消滅辦不到,就勉強承認對方的存在,這已是一大進步,但還沒有達到相互尊重。  歡迎長按上圖二維碼
歡迎長按上圖二維碼
預訂《文化縱橫》2021年新刊
差異是值得慶賀的,這是我個人的經驗。只有差異的存在,互相學習才變得更有意義。比如和基督教對話,我在上大學時有位天主教神父很賞識我,他花了一兩年時間,把天主教神學給我慢慢講述了一遍。那時我學到了很多東西,對他的一些觀點也非常認同。所以,我認為自己是基督教的受惠者。因為我和他的一些對話,使我對儒學的了解加深了。以前不了解的,現在了解了;以前認為無法改變的觀點現在開始懷疑了。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不希望一個基督教士在和我對話後變成一個儒家,他希望成為一個更好的基督徒,這對我一方面是很大的挑戰,另一方面也會有很多啟發。
當然,我們不能完全否認改變信仰的可能性。一個基督教徒和佛教徒對話,可能會逐漸認同佛教,或者反之,這些都不是沒有可能的。卡普洛就說過,一個基督徒能不能同時是一個佛教徒,一個佛教徒能不能同時是一個基督徒?像天主教的有些教士在修道院和佛教禪宗弟子一起打坐、一起靜坐。基督教的靜坐,是要冥想上帝;而佛教的坐禪,是為了證空。但是他們靜坐的形式是一樣的,逐漸,他們有了共同的語言,覺得越來越能夠溝通,這與沒有靜坐經驗的人是很不一樣的。
現在有些人提出dud membership。這在宗教裡面有沒有可能?在中國傳統裡面,這根本不成問題,韓國、越南和日本也沒有問題。中國有儒釋道,有三教合一、一體同源的理論和實踐,首屈一指的日本問題專家賴肖爾說,日本大概有70%是神道教徒,但是大概也有70%是佛教徒,既是神道,又是佛教,他們對儒家的倫理基本上也認同。韓國也一樣,它原來的主流是薩滿巫教,現在基督教大概佔30%,再加上所謂的儒教以及大乘佛教,這中間有很多是重合的。我覺得中國現在可能要從三教擴大成五教,除了儒釋道以外,伊斯蘭教從元代開始,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回教徒會說漢語的大概有兩三千萬,他也屬於中國文化的一部分。這裡面有沒有對話的可能,當然是一個值得大家考慮的大問題。另外,就是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新教。
所以,對話不是藉這個機會來使對方改變他的信仰,這方面最糟糕的例子就是以前的十字軍東征。像布什還講十字軍東征,那是很荒謬很危險的。因為這是一種侵略、一種征服。此外,對話不是藉此機會發表你的觀點或政見,也不是藉此機會解釋自己認為被人家誤解的地方,而是通過對話培養聆聽的能力,通過對話拓展視野,通過對話加強自我反思的能力。
比如和基督徒談話,他講一些他們考慮的問題,就激發我在心靈深處產生了從來沒考慮過的一些思想。又比如,我從來不認為儒家是一枝獨秀,儒家的發展,一直是與其他傳統有很多碰撞與交流,這也是一種對話。可以說,如果沒有與佛教的交流就不可能發展出宋明儒學。現在如果要有任何發展,與西方的交流就是關鍵。如果一種學術不開放的話,它就會變成特殊主義,就沒有辦法進一步發展,特別當特殊主義有侵略性時,那困難就更大了。基督教和伊斯蘭的原教旨主義發生的大衝突就是明顯的例子。再進一步說,我們需要有相當深層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
在這裡順便提一下所謂的自我定義,大家可能會覺得有點驚訝,我覺得“新儒家”這個名詞擺在我身上是不適合的,因為我從來不認為我是新儒家。為什麼?你說新基督教,或者新佛教,這都不恰當。新康德主義,大概就沒有康德思想那麼豐富的哲學資源。因為宋明儒學在西方叫Neo-Confucianism。所以,陳寅恪也把宋明儒學叫做新儒教,有了“新”儒家,那“後新”儒家乃至“新新”儒家都會出現。
因此,我認為儒學有三期的發展是比較符合儒家傳統的歷史進程。第一期是從曲阜的地方文化成為中原文化。第二期是從中國文化,或者中原文化,成為東亞文明,那麼,現在能不能再走出東亞文明成為全球文化的組成部分?如果更細地分成不同時代,有宋明儒學,有當代儒學,你說我屬於儒學第三、第八代的成員,或者你說我希望成為當代的,這都是對的。那麼為什麼不用新儒家呢?因為用新儒家就很容易有新新儒家,後新儒家,這樣就沒完沒了。
可以說,大陸解放以後有大陸的儒家。比如說,馮友蘭的路途是非常曲折的,還有像張岱年先生,甚至上海的馮契先生,後者的思想非常敏銳。他講智慧,其實就是想把儒家的修身哲學和馬克思的實踐哲學配合起來。所謂新儒家多半是指海外的現象。比如香港、新加坡、台灣和北美。這樣細分是可以的,可以說清代有清代的儒學,甚至可以說,不僅有宋明儒學,還有金代的儒學,還有元代的儒學。如果從現代看的話,那可以說是儒學的第三期發展,我現在和一些文化中國地區的學者在交流,包括港台澳,他們對儒家的現代轉化的研究比大陸的儒學大概早了30年,可能40年。
目前儒學的發展,大概韓國是最好的。所以,儒學和現代性的這個問題,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就已經在韓國討論很多了,有很多的文本可以參考。日本也討論這個問題。甚至新加坡,從1982到1989年,他們成立了一個東亞哲學研究所,那個研究所專門從事儒學研究,有中國大陸最好的一批學者,像李澤厚、陳來、朱伯昆、餘敦康、金春峰、朱維錚都在那裡做過研究,方克立也去過。美國學者方面,像狄白瑞、陳榮捷、葛瑞漢、余英時、林毓生、張灝也去過;歐洲學者布斯曼爾在那裡游學好幾個月,台灣的韋政通、戴璉璋、梅廣、蔡仁厚也是。那十年,新加坡可能就是在中國大陸以外最蓬勃的儒學研究基地了。如果沒有這些發展,我想現在大陸的儒學就不能發展得這麼熱絡。所以要用世界的視野來看它。
儒學的一個基本信念是,所謂知識精英,不管他是先覺還是後覺,假如他講的這套不能在日常生活中起作用,不能在一般的老百姓中起作用,那麼它就不是真正的儒學,儒家最高的價值必須在人倫日用之間體現。和希臘哲學大不相同,柏拉圖以來的哲學真理一般人是無法理解的,如果不是精英就不會知道,有的時候只有三五人知道。而儒家一開始就是落實民間的教育,在評價它時就不能簡單地判斷正面或負面,它可能有庸俗的一面,但是它也有非常大的力度。所以,對於丹現象,也許她有一些觀點我不一定贊同,但是如果她沒有經過很好的中國文化的訓練,從小詩詞歌賦念了許多,如果她沒有很好的口才、沒有大眾傳播的魅力,她就不可能使她的《〈論語〉心得》達到好幾百萬的銷量。這是一個很值得進一步探討的現象,我相信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
▍ “多元現代性”抑或“現代性中的多元”?
那麼,到底是多元現代性,還是現代性中的多元?這是一個大問題,這個問題非常複雜。如果接受多元現代性,那對現代性的解構力度就很大;如果認為現代性中是有多元傾向的,那基本上還是接受從西方發展出來的現代性。
我對這個問題考慮了相當長的時間。我在日本參加一個學術討論會後曾經問過丹尼爾·貝爾,西方之外有沒有現代主義?他的回答非常有意思,他說當然有,有無數的可能,但是每一種可能都是災難性的。他所想到的和亨廷頓想到的是一樣的,儒家的權威主義、裙帶關係、沒有透明度、官商勾結和伊斯蘭的原教旨主義;只有西方所代表的,歐美所代表的現代性,才是可以持續的現代性。但是像亨廷頓他們所提出的觀點,在西方學術界不少學者看來,也是非常狹隘而且非常膚淺的提法。應該作深層地思考,像比較文化學者艾森斯塔特,他們的討論就比較細緻。
艾森斯塔特認為,反現代性還是屬於現代性,都離不開現代性,它的範圍非常大。我當時提出“多元現代性”有這樣一個考慮,我認為西方之外,有東亞現代性,它是從日本和“四小龍”開始的,當然,今天的中國特別是沿海一帶也包括在內,但它們的現代性與西方所表現的文化形式不一樣,與西方的現代性不是一根而發的,也就是說,現代化的過程中有不同的文化形式。這中間涉及到另一個問題,就是現代性中的傳統問題。儒家傳統在東亞傳統中是多元多樣的,中國、日本、韓國、越南的儒家傳統不同,東亞現代性中的儒家傳統也是多元多樣的,它們塑造了現代性,它把整個傳統改造了,傳統對現代性不是限定,而是一種創造。
(點擊上方圖片圖解4月新刊)
1980年代,很多人認為大西洋的力量逐漸要被太平洋所取代,並提出21世紀是太平洋的世紀、亞洲的世紀,甚至是中國的世紀。季羨林先生也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現在要從西到東了。我基本上不能接受這樣的觀點,為什麼呢?因為那時候也有些學者,像龐樸提出,要想超越美國單邊主義以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鬥爭的觀點,就應該強調世界地緣政治應是鼎立的態勢。
現在世界上存在三極,就像一個鼎一樣,就比較穩了。哪三極呢?就是北美,東亞和歐盟。如果印度起來了,那我們就四極吧,俄羅斯也站起來了。高盛公司的一位經濟學家最先提出BRICs——金磚四國,第一個就是B,Brazil,是巴西,也就是拉美。你說伊斯蘭世界就一定起不來?現在我們認為非洲一無是處,但是50年以後非洲會成為什麼樣?這些都很難說,所以我們稱之為多元現代性。對這個觀點,很多學者認為過分樂觀,不現實,是理想乃至空想。譬如國內也很少有學者願意接受多元理性化的觀點,就是說,現代性可能有多元的傾向。這個值得考慮,這和我要對啟蒙進行反思是一樣的,假如有這種可能,將來會出現什麼樣的情況呢?儒家傳統和東亞的現代性有什麼關係?
韋伯的命題實際上非常簡單,他所說的是根源性的問題,是講發生學的,即某一現像是怎麼來的?另外,這個東西出來以後,通過模仿,每一個地方都可以發展。他特別提到中國,但同時他寫了一個注,注裡面說日本絕不可能。他說日本絕不可能,這當然是錯誤的。他認為如果中國學了西方,即可發展它自己的模式,還有其他的地方也一樣,對此他不是很樂觀,特別是對全球化的文明的衝突。
彼得·伯格(P.Berger)說,面對現代性,發展中國家的反應共有四種。一種是真正的抗拒,伊斯蘭國家就是代表;一種是全盤的接受,中國就是一個代表;一種是共存;最好就是融合。其實中國都有,是和平共存,像辜鴻銘。辜鴻銘在馬來西亞長大,17歲才學中文。他以前在愛丁堡,跟英國最重要的史學家卡萊爾念過書,他英文是最典雅的,是西方文化培養出來的,但他又有長辮子,且用英文來批評西方,他對西方有強烈的批評。也有全盤接受的,大概錢玄同可以作為代表。但是也有努力使它融合的。“新儒學”就是這樣,我們講儒學的現代轉化就是這個意思。
有很多從西方發展出來的價值,比如人權,已經成為普世價值,但是在東亞乃至亞洲社會發展出來的,也可能是普世價值,儒學就是一個例子,雖然是否能成功尚不知道。如果要進一步發展,就應該有一種平等互惠的對話,或者叫核心價值的對話。這種對話現在已經開始了,但還需要經過相當長的努力,因為我們之間的差距太大,無論是經濟、政治,還是文化的積累。現在我們的工作是迎頭趕上。西方最好的價值與儒家思想是可以對話的。比如說西方對自由的重視,但也必須重視正義,伊斯蘭世界就以為正義比自由更重要。
西方對理性很重視,但他們所強調的只是工具理性。也不能忽視對同情、惻隱之心、慈悲的重視;講權利、人權,還有責任的問題、個人的尊嚴以及社會的和諧。因此,有很多對話的空間。最好的價值,不是把它們擺在一起就是最好的,它們之間的矛盾往往是非常尖銳的,比如自由和平等的價值就有衝突,如何共同考慮而能消解尖銳的矛盾,這是很難的課題。所以,如果所強調的只是工具理性而不是溝通理性,那就太片面了。溝通理性是已經軟化的理性,而真正的理性是沒有同情感的,如果要照這樣走下去,就會碰到很大的困難。有些西方學者認為自由是唯一需要推動的,但後來他們發現,自由不是可以涵蓋一切的,還必須有責任。假如一個跨國公司的總裁沒有任何善心,他是可以把整個社會弄得一塌糊塗的。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10年第2期,原題為《多元現代性中的儒家傳統》

《文化縱橫》2021年征訂啟動
訂閱全年雜誌及365天電子刊組合僅需242元
(原價297元,下單立減55元)

♦ 專文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