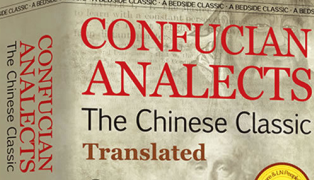♦ 本篇文章轉載自源 爾雅國學報 。若有侵害著作權,請速告知,我們將盡速移除 ♦
一、走向國際,並不等於邁向一流
生活在全球化時代,要想完全拒絕“國際交流”,也很不容易。從政治話題到生活方式,從文化娛樂到學術表達,當今中國,誰都無法“閉關自守”。這不,暑假到了,北大校園裡依舊熙熙攘攘,眾多國際會議你方唱罷我登場,各路英雄豪傑你登壇來我說法,至於前來參加各種暑期學校(短訓班)的國內外學生,更是如過江之鯽。北大的學生呢,同樣行走天涯,四處求學問道。我指導的研究生中,今年暑假,一個到劍橋大學參加有關布盧姆斯伯裡團體的講習班,一個去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查閱女性文學研究資料。而且,都是自己出錢的。這可真是天翻地覆的變化。想想我第一次持護照出國參加國際會議,是在博士畢業兩年之後。我們那代人,第一次出國時,大都有強烈的“文化震撼”;而如今的青年學生,經由電影、電視、互聯網的多年薰陶,對於歐美及日本、韓國的城市風貌等,早就了然於心。對於他們來說,出國旅遊、開會、進修、念學位,仍然會有新鮮感,但已經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了。國際形勢的變化,文化潮流的轉移,加上個人經濟實力的提升,對於新一代學者來說,具備某種意義上的“國際視野”,已經並非難事。
我曾經談及改革開放以後,中國人開始熱情擁抱整個人類的科技創新與文化成果,或者說直面整個西方世界——“大量域外思想、文化、學術著作的譯介與出版,構成了最近30年中國文化建設的主要特徵”。②以“閱讀”為例,從當初的自成一體,到如今的取消隔絕與隔膜,基本上“跟世界思潮同步”,這個變化實在太大了。30年的文化變遷,值得誇耀,也需要反省,其中的關鍵點,在於是否具備“國際視野”,以及如何“與國際接軌”。而這,取決於你所處的位置,以及你所從事的專業。
2000年6月,我第一次到韓國,參加全南大學主辦的“全球化背景下的人文研究”國際研討會,發表《數碼時代的人文精神》,談及互聯網(Internet)必將改變21世紀人類的生存方式、精神風貌以及治學方法時,我斷言:“網路在中國的普及,極有可能打破凝定的以北京為中心向外輻射的學術、文化格局。”因為,作為個體的學者,“無論身處何地,均可借助互聯網,獲得與北京學者幾乎同樣多的資訊,並在同一起跑線上競走。”③現在看來,這個預言太樂觀了。兩個月前,我隨北大代表團去拉薩,商談如何在學術上“對口支援”西藏大學。互聯網早就接通,各種先進設備也已經有了,可就是缺少那種“面對面”的交流。各專業情況不一,建設“異地而能同窗”的“世界課堂”,理科、工科、醫科乃至社會科學,都比人文學要容易得多——最難的是本國(本民族)語言文學教育。因其不僅是翻譯問題,還涉及政治立場、文化趣味以及學術標準。
不同學科的國際化,步調很不一致。自然科學全世界評價標準接近,學者們都在追求諾貝爾物理學獎、化學獎;社會科學次一等,而學術趣味、理論模型以及研究方法等,也都比較容易接軌。最麻煩的是人文學,各有自己的一套,所有的論述都跟自家的歷史文化傳統,甚至“一方水土”有密切的聯繫,很難截然割捨。人文學裡面的文學專業,因對各自所使用的“語言”有很深的依賴性,應該是最難“接軌”的了。文學研究者的“不接軌”、“有隔閡”,不一定就是我們的問題。非要向美國大學看齊,用人家的語言及評價標準來規範自家行為,即便經過一番勵精圖治,收穫若干掌聲,也得捫心自問:我們是否過於委曲求全,乃至喪失了自家立場與根基。
面對鋪天蓋地且絕對“政治正確”的國際化論述,我倒想潑一潑冷水——“走向國際”,並不一定就是“邁向一流”。兩者之間,確實有某種聯繫,但絕非同步,有時甚至是風馬牛不相及。今日中國大學,正亦步亦趨地複製美國大學的模樣。舉個例子,幾乎所有中國大學都在獎勵用英文發表論文,理科迷信SCI,文科推崇SSCI或A&HCI;聘教授時,格外看好歐美名牌大學出身的;至於教育行政官員,更是唯哈佛、耶魯等馬首是瞻。在我看來,改革開放30年,若講獨立性與自信心,中國學界不但沒有進步,還在倒退。④落實在日常生活中,便是對海外漢學家(中國學研究者)的過度推崇。
無論國家還是個人,“虛心好學”從來都是美德;但如此饑不擇食地獲取“國際視野”,不是特別必要。放眼世界,很少像中國人這樣極度關注國外的“中國學研究”。很難想像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會大量譯介並刊行中國人研究莎士比亞、盧梭或歌德的著作。而在中國,這很正常——稍微像樣點的談論中國的英文(不是法文、德文、俄文、日文、韓文、西班牙文)著作,都很可能有中文譯本。最近20年,譯介國外(尤其是北美)中國研究著作成為熱門,各種叢書、工具書、資料集、研究專著層出不窮,好多大學成立了專門的研究所(中心),而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復旦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浙江大學、福建師範大學等,更是開始培養“海外中國學”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和碩士生。
當下中國的學術會議,沒有幾個“洋面孔”,似乎就不夠“國際化”——因而也就不夠“高規格”了。其中規格最高、最為壯觀的,當屬財大氣粗的“北京論壇”與“上海論壇”。前者以“文明的和諧與共同繁榮”為總主題,北京大學主辦,韓國高等教育財團贊助,創辦於2004年,每年一次,已連續舉辦了7屆(2011年11月舉辦第八屆)。據論壇組織者稱:迄今已有來自世界70個國家和地區的2700多位元名流政要和知名學者參加了這一學術盛會。與“北京論壇”遙相呼應的“上海論壇”,其總主題是“經濟全球化與亞洲的選擇”,復旦大學主辦,同樣得到韓國高等教育財團的資助,2005年創辦,也是每年一次。這兩個論壇邀請的嘉賓,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大概占三分之二。還有專門邀請海外漢學家或中國學家的,那就是國務院新聞辦與上海市政府組織的“世界中國學論壇”(2004年創辦,兩年一屆)、國家漢辦和中國人民大學合辦的“世界漢學大會(也是兩年一屆,2007年創辦)。這還不算各大學主辦的專題性質的國際會議……這就難怪,歐美大學中稍微知名點的中國學家,每年絡繹不絕地前來中國“傳經送寶”。其中有準備充分、態度誠懇,給予中國學界很大幫助的;但更多的是行禮如儀,於觥籌交錯中互致問候。而中國學界如此看重“國際化”,在展現“大國風範”的同時,似乎也掩蓋了另一種隱憂——那就是學術上的不自信。
1997年春,在一個討論如何與“海外漢學”對話的國際會議上,我談及:如果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主要任務是盡可能地打開大門,迎接八面來風;21世紀的中國學界,可能會更多考慮如何自立門戶、自堅其說。海外中國學依然是重要的思想及學術資源,只是流通方式很可能變為“雙向選擇”。出而參與世界事業的中國人,很可能在“如何解釋中國”上,與海外中國學家意見相左,乃至正面衝突。最佳狀態是:借助各種對話以及合作研究,彼此溝通思路,爭取各自走向成熟。⑤
要不要“國際化”,這已經不是問題了;難處在於如何在全球化大潮中站穩自家腳跟。作為一個主要從事現代中國文學史/教育史/學術史研究的人文學者,我追求的是“國際視野與本土情懷”的合一。而這一立場的獲得,是在與各國漢學家長期對話中逐漸形成的。以下的論述,更多基於一己之經歷與心得,然後再略為推演開去。
二、“傳媒時代”如何“學術交流”
在大眾傳媒無遠弗屆、無孔不入的時代,如何進行有效的“學術交流”?那些廣為傳播、無人不曉的“大會”,很可能並不重要。反過來,對中國學界或某個專業領域影響十分深遠的“對話”,則很可能被政府及公眾忽略。費那麼大力氣組織國際會議,當然不希望錦衣夜行;可一旦大眾傳媒介入,又很容易被扭曲了方向。上報紙電視,還是不上報紙電視,對於當下中國學者來說,是個很難取捨的問題。需要調整心態的,不只是會議組織者,還包括論文發表者——你想默默耕耘,還是希望成為學術明星?假如是後者,你就必須按大眾傳媒的口味組織自己的發言。
《中華讀書報》曾開列“2007年度文化熱點”,其中包含“陳平原質疑顧彬:學術討論還是嘩眾取寵?”記者陳香對此“熱點”的描述是:
去歲年末,德國漢學家顧彬在接受“德國之聲”電臺採訪時聊起了中國當代文學,很快這段近3000字的訪談漂洋過海來到中國,卻只剩“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一語,引起軒然大波,儘管事後證明此語為媒體斷章取義,但顧彬對中國當代文學評價不高卻可見一端;3月26日,世界漢學大會“漢學視野下的20世紀中國文學”圓桌會議上,顧彬終於有機會當面表達觀點,他以酒作比:“中國現代文學是‘五糧液’,中國當代文學是‘二鍋頭’。”
顧彬認為,問題出在“釀酒”的作家身上,論據則有些特別——優秀的作家首先應該是翻譯家。他推崇中國現代作家精通多國語言的翻譯家視野,提出,如果一個作家只掌握母語,就不能從外部來看本國語言有什麼特色,也就根本算不上作家。“基本上現在的中國作家都是業餘的。”在顧彬看來,同樣“業餘”的還有對待文學的態度,“好多中國作家是蜉蝣。一個中國作家寫小說,一到三個月內,可以寫完一部”。對之,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當場批評顧彬言論偏頗狹隘,對顧彬“談中國文學,不談體制,不談文學場,最後只歸結到外語水準”表示異議,認為不能將作家和翻譯家劃上等號,並表示顧彬“這樣的全稱判斷,已經不是一個學者在學術會議上討論問題的姿態,有點嘩眾取寵”。
諸多媒體報導後,一批學者、作家捲入爭論餘波,而顧、陳二人之爭也再次將中國當代文學引入了公眾視野。……⑥所謂“顧陳之爭”基本上不成立,因為,除了圓桌會議上的發言,我沒再對此發表意見。這確實不是個人恩怨,⑦而是緣於各自迥然不同的學術風格及問題意識。我與德國波恩大學漢學系教授、系主任顧彬(Wolfgang Kubin)的最大差異,不是如何評價中國當代文學,而是怎樣進行學術交流。
號稱廣邀國外頂級學者共襄盛舉的“世界漢學大會”,其“漢學視野下的20世紀中國文學圓桌會”特意安排在晚上,除與會專家學者外,允許新聞記者旁聽。按照慣例,“外來的和尚”先念經。顧彬教授講述其心路歷程——提出“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後,不太敢來中國,擔心受攻擊;沒想到那天在上海入境,當即有人沖上來,說你講得太好了,中國當代文學就是垃圾。於是大受鼓舞,決定在漢學大會上發揮其“五糧液”與“二鍋頭”理論。說實話,我原本準備接受顧彬教授的解釋,然後轉入本次圓桌會的主題——因為,“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這樣的表述方式,更像是大眾傳媒的“捕風捉影”、“無事生非”,而不太像出自德國教授之口。可現在,緊接著掌聲不斷的“二鍋頭”高論,輪到我登場,不得不撇開論題,略作辨析。查閱互聯網上的“漢學視野下的20世紀中國文學圓桌會”現場速記,我當時除了談及中國當代文學,更重要的是分辨“發言姿態”——面對學界與面對媒體的差異。一個學者,在國際會議上發言,不該越過前排的同行,而向後排的記者喊話。不管是“垃圾說”,還是“二鍋頭”,都很有轟動效應,但不是學術語言。用“垃圾”或“二鍋頭”來評價中國當代文學,這樣的“發言姿態”,更像媒體人,而非嚴謹的學者。在國外學界,即便是大牌教授,也沒有權利如此明顯“違規”、“越界”。我說我很不高興,因為“顧彬教授有點嘩眾取寵”。
對於顧彬的“高論”,中國學界有人批評,有人讚賞——大體上是專業研究者批評,行外的人讚賞。⑧其實,我更關注媒體的報導,以及此事的後續效應。幾乎所有關於這次會議的報導,都圍繞“二鍋頭”做文章;而我則因當場“奮起反擊”,被激賞或譏諷。“看熱鬧”的人群中,真正關心中國當代文學的很少,絕大部分讀者感興趣的是中外學者如何“吵架”。引幾篇關於此事的報導,看看“文化熱點”是如何形成的。
先看《新京報》的報導:
昨天,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陳平原解釋了自己在漢學大會上批評德國波恩大學教授顧彬的動機。“顧彬對當代中國文學的批評不是一個學者對中國當代文學進行研究分析之後做出的學術判斷,而是一種大而化之的,憑感覺說出來的話。因此,中國作家也沒有必要太在意。”陳平原稱,一個真正的漢學家決不會這樣說。當顧彬說自己也寫小說,寫詩的時候,“我表示,如果你是作為一個作家這麼發言的話,我可以理解”。陳平原稱,沒有收集大量材料,沒有仔細研究、分析,“顧彬所採用的發言方式是媒體所樂意見到的,這件事情從一開始到現在就是娛樂化的”。⑨關於此事很可能被“娛樂化”的判斷,不幸而言中。緊接著的是《中國教育報》的報導,題目很聳人聽聞——《中國當代文學只是“二鍋頭”?》:
德國作家、詩人、漢學家、波恩大學教授顧彬在世界漢學大會“漢學視野下的20世紀中國文學”圓桌會議上提出,“中國當代文學是‘二鍋頭’,中國現代文學是‘五糧液’”,一時成為討論焦點,並遮蔽了很多人的光芒。⑩如此文章開篇,大有深意:首先,顧彬的主要身份是德國作家而非漢學家;其次,會議討論的焦點是“二鍋頭”;第三,面對如此精彩發言,其他學者全都黯然失色。再接著,就是《中國青年報》的報導: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首先對“談中國文學,不談體制,不談文學場,最後只歸結到外語水準”表示不滿。他以不會外語但文學造詣深厚的沈從文為例提出:“個性化的作家可能有人外語好,有人外語不好,因此只能拿他的作品來評判。”對於顧彬肯定現代中國文學,否定當代中國文學的提法,陳平原不客氣地表示:“這樣的全稱判斷,已經不是一個學者在學術會議上討論問題的姿態,有點嘩眾取寵。”此報導引入在場的另一位元漢學家的視角,可謂一語中的:
“老顧,我覺得您在玩兒遊戲。”荷蘭萊頓大學漢學研究院中文系教授柯雷用一口純正的普通話說,“一個非常深刻的話題已被你控制了。20世紀的中國文學有很多有意思的話題,我建議我們不要繼續講這些可笑的話”。(11)柯雷(Maghiel van Crevel)的提醒特別值得關注,因他道出了顧彬的論述策略,以及嚴肅學者的尷尬處境。只要你進入大眾傳媒,“非常深刻的話題”根本不敵“可笑的話”。這也是我事後絕口不談“二鍋頭”的緣故——任何回應,都會被媒體往“娛樂化”方向引導、解讀。結論必定是:雙方各打五十大板,有利有弊,無是無非。於是,“看熱鬧”的大呼過癮,“唱怪論”的收穫名聲。(12)
這就是我們熱切盼望的“國際交流”,或者漢學家對於中國學術的貢獻嗎?我很懷疑。從什麼時候起,海外漢學家到中國的大學裡演講,不再小心翼翼,而可以如此“放言無忌”?記得20世紀80年代初京都大學榮譽教授小川環樹(1910—1993)來北大演講,選擇的題目是《敕勒之歌——它的原來的語言與在文學史上的意義》。(13)北齊時代斛律金(488—567)詠唱的《敕勒歌》,為明清以來的古詩選集所必錄,面對這首原本是用少數民族語言唱詠、如今讀到的只是漢文譯本的名作,小川先生討論其原來的語言,以及如何演進……選擇這樣考據性質的、中國學者極少涉及的題目,據說是擔心自己學識不夠,怕被中國學者嘲笑。隨著中外學術交流的日漸頻繁,雙方都不再有神秘感——很多漢學家常來常往,在中國大學裡演講,不再緊張,也不再認真準備(中國學者外出訪問,也有這個問題)。因為,講好講不好,都能博得無數禮貌性質的掌聲。
二三十年前,中外學者交流少,見面難,一旦有機會,都渴望瞭解對方。於是,努力表白自己,傾聽對方,尋求共同研究的基礎,在一系列誠懇且深入的“對話”中,互相獲益,且成為長期的朋友。(14)現在國際會議多如牛毛,學者們很容易見面,反而難得有推心置腹的對話。不是就文章論文章,就是為友誼乾杯,不太在意對方論文之外的“人生”。至於只看重對方的身份、頭銜、象徵資本等,那就更是等而下之了。
不是說中外學者間沒有嚴肅的對話,而是那些深入細緻的思考,被甚囂塵上的“好玩的話”給遮蔽了。就以那次世界漢學大會為例,《南方週末》做了4個專版,刊發關於瑞典漢學家羅多弼(Torbjorn Loden)、美國漢學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中國學者嚴紹璗的3篇專訪,以及我的文章《視野·心態·精神——如何與漢學家對話》,(15)應該說都很有分量。只是在刊發我的文章的版面,穿插顧彬照片且有如下說明文字——“漢學大會上,德國漢學家顧彬再次‘放炮’,被荷蘭萊頓大學柯雷指為‘玩兒遊戲’”,以致不少讀者誤以為我的文章是針對顧彬而寫的。我這篇事先提交給世界漢學大會的論文,主要討論三個話題:第一,“漢學家”並不等於“國際學界”,相反,所有的漢學家,都有與其本國學術對話的欲望與責任;第二,與漢學家對話時,應保持平和的心態;第三,所謂的學術交流,應儘量從資料、技術層面,逐漸擴大到理論、精神層面。中國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認定此文“不僅對於中國學界應如何與漢學家展開對話有深刻的見解,其本身即是我們建構漢學對話平臺的絕佳引言者”,於是邀請美國耶魯大學孫康宜教授、日本京都大學平田昌司教授、香港科技大學陳國球教授、臺灣“中央”大學康來新教授,共同參與對話。(16)大家都意識到,在國際交流日漸頻繁的今日,如何與海外漢學家展開卓有成效的“對話”,是個“真問題”;可此類認真、深入的思考,只能局限於學界內部。
在學術共同體沒有真正建立的中國,學者的聲譽很大程度受制於大眾傳媒;而媒體需要的不是高深的專著,而是各種充滿娛樂精神的“怪論”。倘若你長期正襟危坐,不願意“配合演出”,很容易被媒體冷落乃至遺忘。我之所以在意“二鍋頭”事件,就因為顧彬教授的高論及其後續效應,凸顯了現代中國學者的兩難處境。
(待續)
注釋:
①本文乃作者提交給韓國現代中國研究會主辦的“中國學:內外視角的交叉與溝通”國際學術研討會(2010年8月25日)的主題報告,特向主辦方致謝。
②參見《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講述“30年文化之變”:經過了30年,我們與世界思潮同步》(王愛軍、高明勇報導),《新京報》2008年12月13日。
③參見陳平原:《數碼時代的人文研究》,《學術界》2000年5期。
④陳平原:《既有國際視野,也講本土情懷》,《新京報》2011年4月23日(清華百年紀念特刊[陸]人文日新),《人民日報》2011年6月13日轉載時,改題《走向國際,不代表邁向一流》。
⑤陳平原:《中國學家的小說史研究》,初刊《清華漢學研究》第三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0年2月),收入陳平原《學者的人間情懷——跨世紀的文化選擇》,北京:三聯書店,2007年。
⑥參見陳香:《2007年度文化熱點》,《中華讀書報》2007年12月12日。
⑦劉若南:《顧彬:我希望我是錯的》(《南風窗》2007年4月B):“顧:國內有兩個人,我用他們的資料用得比較多,一個是上海復旦大學的陳思和,他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寫得很好,一個是陳平原,我用他的現代文學史特別多,他也寫得不錯,基本上不錯。如果沒有他們兩個人的文學史研究的話,我也可能沒法寫我的20世紀中國文學史,因為他們客觀,有很多很多資料,等等。《南》:但是陳平原就反對你的很多觀點。顧:無所謂。君子不怨。”作為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我贊成邀請顧彬來北大演講。
⑧蔡翔:《誰的“世界”,誰的“世界文學”——與德國漢學家顧彬先生商榷》一文,批評顧彬觀點中暗含著西方中心主義立場(《文匯報》2007年4月22日)。另外,《中國圖書評論》2007年第3期發表李大衛《顧彬、魯迅和我們的世界文學想像》、郜元寶《中國作家的“外語”和“母語”》、洪治綱《傲慢、奴性及其他》三文,也都對顧彬持批評態度。支援顧彬意見的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肖鷹,在《中國學者的“大國小民”心態》(《新京報》2007年4月3日)中反批評:“陳平原過敏地用民族文化對立的眼光來看待顧彬的講話,實在是因為他完全被一種‘大國小民’的心態支配著。”
⑨張弘:《“顧彬只是中國文學旅遊者”》,《新京報》2007年3月30日。相關報導還有《“基本上中國作家是業餘的”》(《南方都市報》2007年3月28日)、《顧彬“再轟”中國當代文學世界漢學大會為此“炸開了鍋”》(《中華讀書報》2007年3月28日),內容大同小異。
⑩參見楊桂青:《中國當代文學只是“二鍋頭”?》,《中國教育報》2007年4月1日。
(11)參見蔣昕捷:《中國文學需要多少個“顧彬”?》,《中國青年報》2007年4月2日。
(12)接下來的這幾年,顧彬教授理所當然成為中國讀者最為熟悉的漢學家,頻繁地在中國各地出書、演講,影響也越來越大。不能說顧彬教授拋出“垃圾說”是為自家新書登場造輿論,但此等“怪論”確實讓中國讀者很快記住了這位“勇敢”的德國教授。
(13)20世紀日本享有盛譽的漢學家小川環樹,1933—1936年就讀於北京大學中文系,曾任日本中國學會理事長、日本學士院會員。此次演講稿,由嚴紹璗、中島碧協助譯成中文。參見小川環樹:《敕勒之歌——它的原來的語言與在文學史上的意義》,《北京大學學報》1982年1期。
(14)比如,我認識中島碧教授10多年,一直保持著相當密切的聯繫。但說實在話,真正的深入交談,有賴於1992年9月的湘西之行。參見陳平原《共同研究是否可能——重讀中島碧先生信有感》,《中華讀書報》2001年5月16日。
(15)參見《南方週末》2007年4月5日上《“讀〈左傳〉不如讀〈紅旗〉”?——專訪羅多弼》、《“如果美國人懂一點唐詩……”——專訪宇文所安》、《與日本神話發生中國關係——嚴紹璗訪談》以及《視野·心態·精神——如何與漢學家對話》。
(16)參見《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十七卷第四期(2007年12月)王璦玲為“21世紀的漢學對話”專輯撰寫的“導言”,以及陳平原、孫康宜、平田昌司、陳國球、康來新5文(第85-117頁)。
來源:《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6期
♦ 專文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