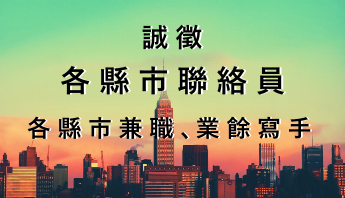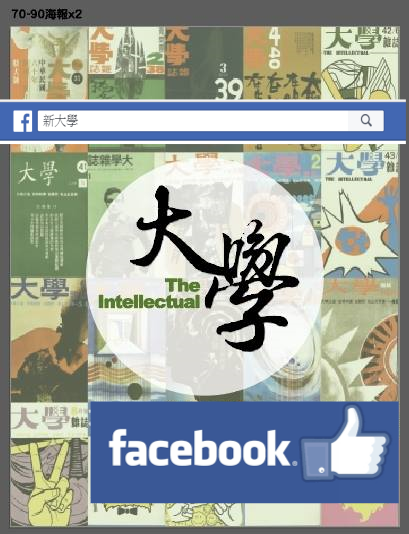♦ 本篇文章轉載自 英魂回家。若有侵害著作權,請速告知,我們將盡速移除 ♦
2025/1/19

2025是抗戰勝利80周年。新年伊始,來自全國各地近300位抗戰將士後代、社會各界愛心人士和志願者,齊聚湖南衡陽,南嶽忠烈祠,舉行80周年紀念首場祭拜悼念抗日忠魂大型典禮。
衡陽作為全國唯一的抗戰紀念城,南嶽忠烈祠作為“抗日戰爭中興建之唯一大型紀念祠墓”並供奉抗日陣亡將士總神位,在如此重要的節點裡,承載著我們永志這段厚重歷史、追尋先輩榮光、傳承民族不屈精神的堅定決心。
早晨9點10分整,以忠烈祠牌坊為起點,眾人高舉全國34個省份牌,30多位後人手捧抗日先輩的照片,以三牲開路,向著主祠堂拾級邁進。


隊伍中,白髮的老人用深沉的目光勾連著久遠的記憶,神態至誠;年幼的孩子端正地手持菊花,靜默跟隨大人的腳步。甚至一位小少年行動不便,坐在輪椅上,被家人堅持托舉著跟緊行進的行列。這裡的每一代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表達著對歷史的敬重。他們帶著深淺不一的思考,依次穿過具有特定象徵意義的七七紀念塔、紀念堂、安亭戰役紀念碑。
號聲吹響,鼓樂齊鳴,而後攀登276級臺階。每上一階,代表抗戰時一位將官生命的逝去。

走完最後一階,便至忠烈祠最高層,享堂。
全體人員面向享堂正中的抗日陣亡將士總神位,祭悼儀式正式開始。站在儀式第一排的,是一批抗日先輩的後人。他們的面容,總是在某方面像極了捧在胸前照片裡親人的樣子。他們帶著親人一個又一個鮮活的個體抗戰故事,幫助世人串聯起歷史的真相。



坐在輪椅上的唐之傑,其父親唐夢龍,曾擔任抗日名將宋希濂的貼身衛士長達8年之久,征戰南北。老兵去世後留給女兒的遺物,有其作戰時飲過日寇血的軍刺,還有在松山戰役中使用過的煤油燈……
王愔的祖父王麟是22集團軍124師740團團長,陣亡在台兒莊戰役滕縣保衛戰最慘烈的時刻。王麟第一次出川抗日時,算命先生說他凶多吉少,不死也要脫層皮。剛從重病中痊癒的他不屑一顧地哈哈大笑:“老子早就脫了一層皮!去打仗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何懼凶多?”王愔的相框裡,是連著的三張先輩照。除了祖父,她的舅舅、叔爺(王麟親弟弟)皆犧牲在抗日戰爭之中。
姚天明的爺爺姚貴民,從拿筆桿子的教書先生變成拿槍桿子的部隊參謀。探親歸隊時他對百般挽留的妻子承諾:“打完這場仗就無仗可打了,結束後我一定好好回來過日子!”後來,姚貴民陣亡在衡陽戰場,師長向其家人回信說明:“戰事已日益艱難,姚貴民主動提出由他帶領師部後勤人員,甚至伙夫和通信兵都帶上了,火速趕往前沿陣地。此去再沒能回來。未幾,衡陽城破。”
“死”字旗第三代傳人王烈勳,其伯父王建堂當年抗戰出征,收到父親寄給他的一面“死”字旗:“我不願你在我近前盡孝,只願你在民族份上盡忠。賜旗一面,死後裹身,勿忘本分。”後來在諸多次戰役中,王建堂負傷便從父親給的旗子上撕下一角裹傷。
有馬家五兄弟齊聚現場,他們的父親馬如龍,原本是第10軍裡的一名理髮兵,衡陽保衛戰,連長丟給他一把槍:沒事去打鬼子吧!戰場上,馬如龍打槍不行,刺刀上手,卻跟玩剃鬚刀一樣麻利,生死關頭一刀將日軍斃命——“我吃住都在戰壕裡,那便是我在衡陽城的四十七天。”脫離戰俘營逃亡的時候,馬一直帶著部隊理髮用的藤條籃子和竹筒子。老兵向自己的孩子交代,“我死之後,其他所有東西都可以扔,就是這個籃子不能扔。”
還有前不久才尋親成功的林志文、王金鼎兩位營長之後人,在此之前從未見過其先輩的模樣,從未得知,先輩在衡陽的戰場上,皆有著以一營戰士對陣日軍上千兵力而死戰到底的壯烈之舉。
更有至今還未找到親人下落的後人,只能舉著先輩的陣亡優撫令來到祭拜現場……


諸多將士血親後代的參與,讓祭悼更顯神聖而意義非凡。
儀式上,集體向抗日忠魂主神位莊重默哀,奉祀三牲,鞠躬獻花。各省同胞還紛紛敬獻各自家鄉的特產,讓戰死異鄉的兒郎們嘗嘗家鄉的味道。


民革衡陽市委原秘書長范林頌讀、點焚祭文。為著無數還未魂歸故里的將士兒郎,和一段又一段依舊塵封在角落的抗戰歷史,在他的帶領下,全體人員同聲宣誓:
“我輩華胄,重任在肩,
尋找英烈,不舍近遠,
查名求籍,期續親緣,
英雄歸隊,再聚堯天,
載冊銘史,石勒碑鐫。
告慰先烈,心誠志堅!
為愛止戈,為和發願。
英魂作證,旦旦此言。”

我們高喊誓言,是警醒自己,勿忘歷史。也是號召同輩,凝聚力量,每一個人腳踏實地地盡己所能,發掘更多抗戰歷史,保護每一份珍貴的抗戰文物與史料,給予身邊日漸凋零的抗戰老兵更多的關愛,不放棄任何一條為戰爭失散家庭尋親的線索……
主祭之後,大家分赴孫明謹師長墓地、陸軍第三十七軍六十師公墓、陸軍第七十四軍公墓及羅啟疆將軍墓地開展分祭。
站在享堂觀景台前眺望,祠宇四周墓葬環抱,如眾星拱月,永遠守護著延綿80年的勝利之光。

♦ 專文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