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轉載自 。若有侵害著作權,請速告知,我們將盡速移除 ♦
2022/5/16

正是“半路出家”而又“野心勃勃”, 導致了黃仁宇的毀與譽。黃仁宇的作品當然不是沒有問題, 有些地方存在很嚴重的硬傷。但是, 他的洞察力、 悟性、 歸納能力、 綜合能力、 “通感”能力是罕見的。他強烈的問題意識和勇氣, 他將學術成果通俗化的本領, 無人能出其右。
“黃仁宇現象”實際上是對史學界的警示, 學術研究應該走出狹小天地, 從面向上層和少數精英到面向非專業化的讀者, 實現為社會服務功能的轉化。
黃仁宇是歷史學界的瓊瑤?
來源| 《歷史的局外人》
01 退稿與解聘
1976年,五十八歲的紐約州立大學教授、華裔歷史學者黃仁宇用英文完成了一本書,取名為《無關緊要的1587年:明王朝的衰落》(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我們從這本書洋洋灑灑的行文中可以讀出作者在寫作時是如何逸興遄飛、文思泉湧。確實,這本翻譯成中文時名為《萬曆十五年》的書後來被評論為一部充滿激情、才華橫溢的作品,作者試圖從中國歷史上這看起來無關緊要的年頭出發,解釋一個重大問題:中國在歷史上何以落後於西方。
黃仁宇四十八歲才入行歷史學界,個人作品不多,已近六十花甲的他急需出版一本有分量的作品來證明自己的學術水平。因此這本書是他調動一生的經驗和思考,全力以赴的作品,寄出書稿的時候,他充滿信心。他認為這是一顆重磅炸彈,將在世界史學界引發一場巨大震動。
然而他收穫的,卻是美國多家出版社一次又一次地退稿。市場化的出版社認為,這本書雖然包含宮廷秘史、妃嬪恩怨等普通讀者可能感興趣的流行要素,但是又夾雜有大量思辨性的內容,對普通讀者來說有很大閱讀難度。從本質上來說,這本書應該屬於學術著作。
而學術類出版社的編輯看到這本書,更感覺一頭霧水,認為這本書的寫作方式過於文學化,既不像一部斷代史,也不像一篇專題論文。曾留學美國的政治學者劉瑜談起學術界的“規矩”,她說,論文寫作“格式化”,排斥個性和風格,不僅國內如此,美國其實也是這樣。美國的學術圈子鼓勵的同樣也是“精緻的平庸”,如果你想在這個圈子裡生存,就要自覺地順從“學術產品”的流水線規則。
美國學術出版的慣例是作品須經不具名的審稿人進行評審。審稿人面對這樣“不倫不類”的“四不像”,發現他們根本無法提出修改建議。它更像散文或者小說,而不是歷史。他們認為用這種方式去呈現和探討歷史,根本就是錯誤的。
禍不單行,就在這本書屢遭退稿的過程中,1979年,黃仁宇以六十一歲的“高齡”,被所在的紐約州立大學辭退。他在回憶錄《黃河青山》中說:
一封1979年4月10日由校長考夫曼博士(Stanley Coffman)署名給我的信如下: “你的教職將於1980年8月31日終止。你的教職之所以終止,是由於人事縮編所致。”
這是一個突然的打擊,黃仁宇完全意想不到,因為到1979年春季為止他已在紐約州立大學連續任教十年,已經獲得了“終身”教職。黃仁宇在回憶錄中說:“我被解聘了。這是侮辱,也是羞恥。 ”
相對羞恥,更為難以承受的是經濟問題。他的生活陷入朝不保夕的境地。他後來回憶說:“我被解聘後,就沒有找到工作,也沒有申請到研究經費。……我只要一聽到熱水器要更新或是屋頂有破洞,心都會一陣抽痛。”
就在被解聘前不久,因為在歐美出版無望,黃仁宇乾脆自己動手把這部書稿譯成中文,定名為《萬曆十五年》,託人帶到國內碰碰運氣, ,看看有沒有出版的機會。
黃仁宇與黃苗子的夫人郁風的弟弟認識,黃苗子和中華書局的編輯很熟,因此他在1979年5月23日給傅璇琮寫了一封信:
璇琮同志:
美國耶魯大學中國歷史教授黃仁宇先生,託我把他的著作《萬曆十五年》轉交中華書局,希望在國內出版。第一次寄書稿來時,金堯如同志知道。表示只要可用,就盡快給他出版。這樣做將對國外知識分子有好的影響,並說陳翰伯同志也同意他的主張。但書稿分三次寄來,稿到齊時,堯如同誌已離開了。現將全稿送上,請你局研究一下,如果很快就將結果通知我更好,因為他還想請廖沫沙同志寫一序文(廖是他的好友)。這些都要我給他去辦。
匆匆即致
敬禮!
苗子
在這樣的背景下,這本書在中華書局幾經討論和反复,終於在三年後,也就是1982年付梓出版。有意思的是,也許是因為作者的籍籍無名,書的封面上竟然沒有出現黃仁宇的名字,只有題字者廖沫沙的名字。
接到樣書後,已經六十四歲的黃仁宇心情非常激動。雖然他也指出:“封面上……沒有作者黃仁宇的名字,在設計上似欠完善。”但是接下來,他還是在信中一再對中華書局表示感激。他說:“大歷史觀容作者盡懷縱論今古中外,非常感謝,應向執事諸先生致敬意。”

02 “生平不讀《十五年》,就稱明粉也枉然”
一開始,誰也沒想到這本書能夠成為暢銷書,包括黃仁宇自己。
為了證實他的激動心情,黃仁宇在這本書剛剛出版時表示,雖然他經濟上處於困窘之中,但“不受金錢報酬”。因為“國內作家多年積壓書稿亦望付梓,《萬》書與之爭取優先出版機會,故暫不收稿費及版稅”。
後來中華書局向黃仁宇贈送了200冊書以充稿費。然而這本書上市後,市場反響居然非常好,第一次印刷25000冊,很快就銷售一空,在讀書界引起很大轟動。後來三聯書店拿過這本書的版權,將它作為“黃仁宇作品系列”中的一種出版。雖然沒有做任何營銷,但是《萬曆十五年》還是迅速成為大陸最暢銷的歷史著作,迄今銷售已經數百萬冊,成為現象級出版物。嗅覺敏銳的台灣出版商立刻推出台灣版,同樣引發巨大轟動。
從此,黃仁宇的作品在海峽兩岸一部接一部地出版,幾乎每本都受到熱烈追捧。在20世紀最後十餘年間,黃仁宇成了中國海峽兩岸普通讀者心目中影響最大、名聲最盛的歷史學家,甚至都不用加“之一”二字。

而《萬曆十五年》的英文版也在屢屢碰壁之後,在他被大學解聘後的第二年,終於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黃仁宇的期待一定程度上得到實現,這本風格獨特的書立刻引起了評論界的關注。美國著名作家厄普代克(John Updike)在《紐約客》雜誌上為這本書撰寫書評,大力推薦,他說:“儘管深富歷史學識,然而《萬曆十五年》卻也具備著卡夫卡(Kafka)的優美而又令人頓挫之故事《中國萬里長城築成之時》的超現實的虛構特質。 ”1982年和1983年,該書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歷史類好書兩次提名。後來又被以法、德、日等多種版本出版,在美國被一些大學採用為教科書。
如今,這本書已經一紙風行三十年,坊間甚至有“不讀《萬曆十五年》,讀遍詩書也妄然”“生平不讀《十五年》,就稱明粉也枉然”的戲語。
為什麼這樣一部最初不被看好的作品,後來在中國大獲成功呢?
首先這與時代背景密切相關。
1949年後,大陸史學界迅速定於一尊,對歷史形成一系列固定的近乎公式化的解釋,比如五階段論、農民起義是歷史前進動力論等。歷史學界越來越呈現一種僵化、沉悶、壓抑的局面。直到改革開放之初仍然如此。
《萬曆十五年》的出現,如同在沉悶的房子裡打開了一扇窗戶,讓剛從“十年浩劫”中走過來的中國文化界呼吸到了外面世界的新鮮空氣。人們不約而同地驚嘆:“原來歷史可以這樣寫。”
劉志琴在《黃仁宇現象》中說:《萬曆十五年》在這一時期出版立即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反映了民眾對教條化的史學讀物早已厭倦。且不說別的,就是將一個王朝的盛衰濃縮到一年的這一研究方法,在國外屢見不鮮,而在中國30年見所未見;以人物為主線,從政治事端、禮儀規章、風俗習慣描繪社會風貌,就引人入勝;在論理中有故事有情節,具體生動,不落俗套,使讀者興趣盎然。我想,如果不是《萬曆十五年》而是其他歷史著作捷足先登中國,只要有類似的特點,也一樣有轟動效應。
其次,這本書的暢銷更與黃仁宇獨特的敘事策略有關。黃仁宇選擇了明朝萬曆十五年,這樣一個平淡的、沒有什麼突發事件的一年,選擇了六個人物,用七篇文章來展示大明帝國,並分析它的內在機理。這六個人物是萬曆皇帝朱翊鈞、首輔大學士張居正、後繼首輔申時行、清官楷模海瑞、大將軍戚繼光、名士思想家李贄。他們都是時代的佼佼者,他們也都或多或少地認識到自己所處時代的問題,都想用自己的力量挽救這個王朝,然而最後,他們一個又一個地敗下陣來。這六個失敗者的群像,組成了一個失敗的王朝。事實上《萬曆十五年》的敘事結構就是以一個個人物為中心,明代萬曆年間的歷史被組接為一個個故事性敘事,作者把一樁樁歷史事件圍繞著一個個歷史人物,敘述得娓娓動聽。
這本書大受普通讀者歡迎的另一個原因,是它提供了一個簡單明了的通史觀。這也幾乎是一個規律:大部分影響力很大的通俗史學名著,背後都有一個清晰的觀點。畢竟,普通讀者選擇讀歷史作品,不是為了學習考證的技術,而是為了獲取知識和結論。學者可能樂於展示自己的專業技巧,螺螄殼裡做道場,但讀者並沒有觀察庖丁解牛的耐心。因此,對普通讀者來說,好的歷史作品是小中見大,從一個小的切口進去,能夠看到清晰的大的規律。
《萬曆十五年》剖析的是1587年,但是黃仁宇要展示的是整個中國歷史的全貌。他要告訴讀者的是,為什麼從明代起,中國落後於世界。黃仁宇的答案是,“中國的悲劇乃是其在地方組織及技術上的設備尚未具備規模之際,先已有大帝國之統一,因之上下之間當中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間階段,全靠專制君主以他們個人身上的機斷彌補”。 大一統體制一方面簡單有效地維持了社會的穩定,另一方面卻也限制了社會變化發展的空間。傳統政治體制的弱點在於組織簡單,效率低下,既缺乏彈性又欠實力,只重道德的表面,而缺乏務實地解決具體問題的能力,表面上看起來如同龐然大物,實際上不堪一擊。因此黃仁宇認為,中國問題的關鍵是引入西方的“數目字上的管理”,“道德非萬能,不能代替技術,尤不可代替法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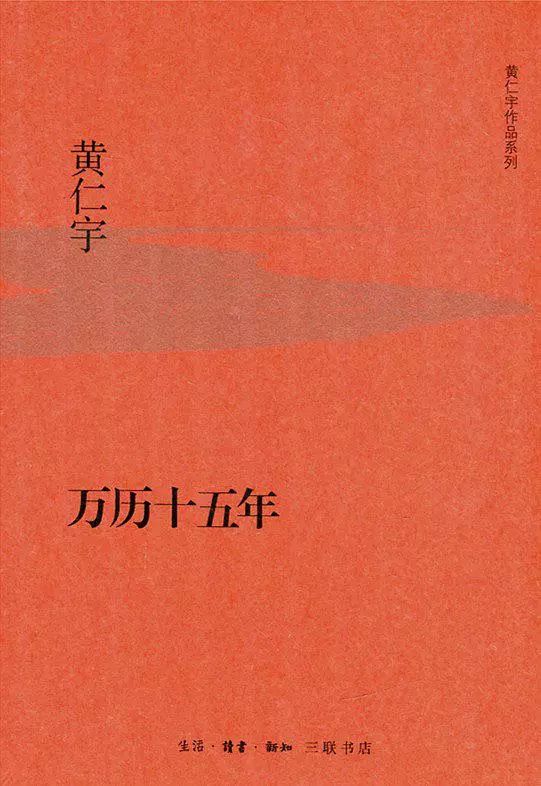
03 歷史界的瓊瑤?
為什麼黃仁宇能獨闢蹊徑,寫出這樣符合讀者口味的作品呢?這與黃仁宇的個人特質有關。
黃仁宇的人生是頗有點傳奇色彩的。黃仁宇是湖南人,少年早慧,十四歲就開始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十八歲考入南開大學理學院機電工程系,不出意外的話,他本來應該成為一名工程師,在機電工程領域大展所長。然而上學不久,抗戰爆發,一腔熱血的他投筆從戎,奔赴戰場,曾先後擔任陸軍第十四師排長及代理連長,後來更是遠赴緬甸,1944年5月,因在密支那負傷,受頒陸海空軍一等獎章。
戰後他負笈美國,憑在美國陸軍指揮參謀學院所修的學分,獲密歇根大學錄取,以三十四歲的“高齡”從大學三年級讀起,先讀新聞,後轉到歷史,1954年獲學士學位,1957年獲碩士學位,1964年獲博士學位。

這樣的經歷,在當代歷史學術界可謂絕無僅有。“半路出家”,一方面使黃仁宇的學術訓練可能不夠嚴格、規範,另一方面,卻也使他沒有被學術界學術產品的“流水線規則”所馴化,保持了強烈的個性。更重要的是,“半路出家”使黃仁宇終生保持了對歷史發自生命深處的草根式興趣。
“半路出家”的黃仁宇的所有思考與寫作,都與自己的生命經驗息息相關,他的研究不只是為了解決學術問題,更是為了解決個人生命中的困惑。“我所以成為歷史學家,是因為自己顛沛流離,一切源於中國的動盪不安。”“對我來說,歷史學不只是行業技藝而已。……我開始接觸這一行業和技藝,是因為動盪不安的生活造成心靈苦惱。”他說:在美國讀書和打工時,我常被在中國的痛苦回憶所折磨,不時陷入沉思。 後來當教師,拿著麥克風站在五百名大學生面前,無法立即解釋:為何康有為失敗了,孫中山失敗了,袁世凱失敗了,張作霖失敗了,陳獨秀失敗了,蔣介石失敗了。為使我的講課內容前後一致又有說服力,唯一的方法就是說,中國的問題大於上述人士努力的總和。中國文明將和西方文明融合的說法,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的事件。上述不同階段的失敗必須被視為階段的調試,以達成一致的終點。
黃仁宇個人的獨特經歷,造就了黃仁宇作品的獨特性格,也造成了黃仁宇作品的意外“走紅”,更讓身處失業陰影中的黃仁宇的生活柳暗花明。如果不是大量的通俗性學術作品在海峽兩岸贏得了源源不斷的稿費,六十二歲失去“飯碗”的他可能連吃飯都成了問題。而通俗歷史寫作的成功,支撐了他在被辭退後能維持二十年有尊嚴的中產階級生活,並且在死後讓他的妻兒生活有所依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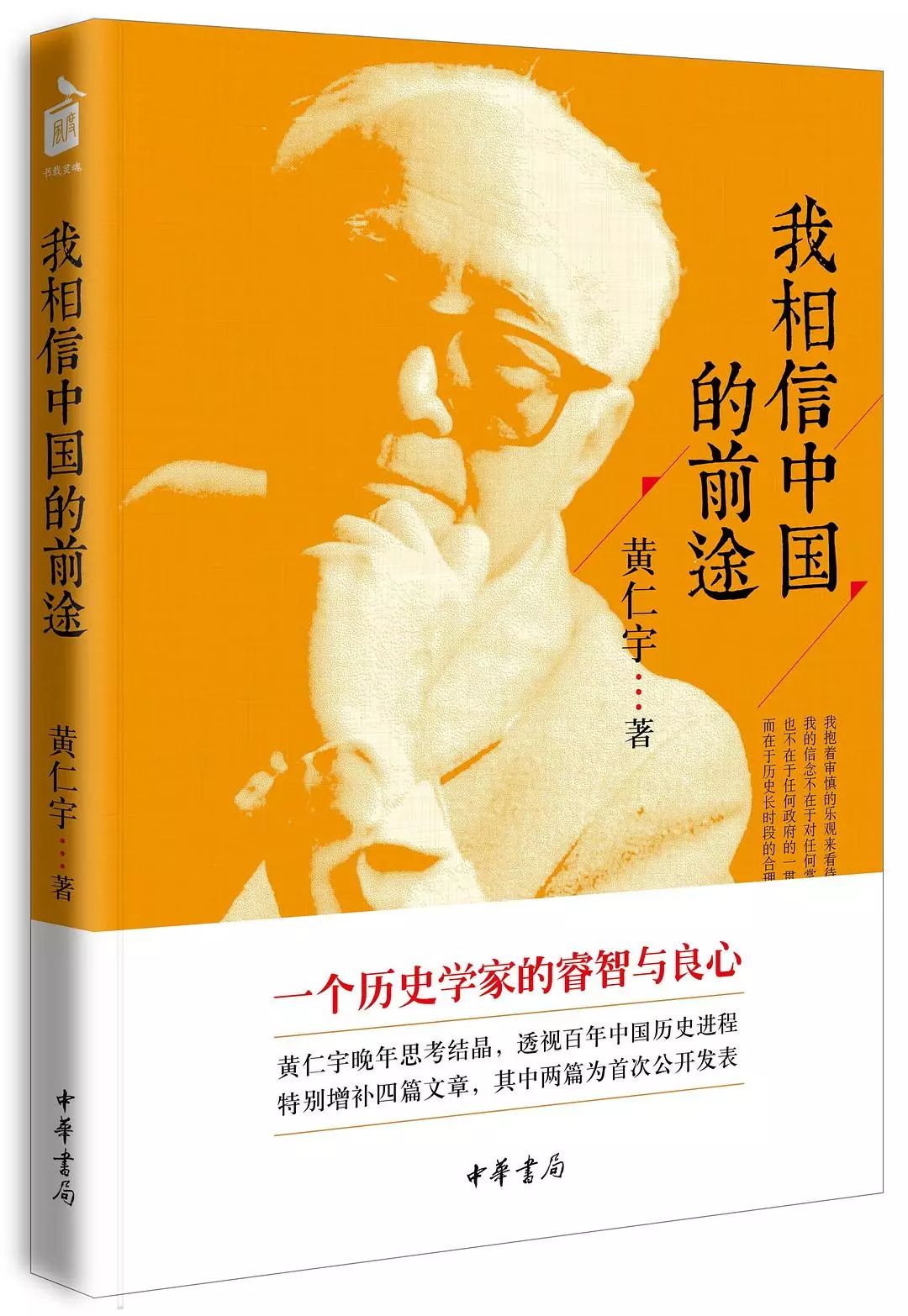
聽起來,這似乎又是一個學術界醜小鴨變成白天鵝的故事,結尾應該是從此黃仁宇就迎來學術的春天,贏得無數鮮花和掌聲。然而,事實並沒有這麼簡單。普通讀者可能只知道黃仁宇的盛名和其書的暢銷,卻不知道他在學術界受到的排斥。學術界對黃仁宇的反應是複雜而意味深長的。“他那標註了'大歷史觀'稱號的小中見大的史學技巧在讓相當一部分人欣喜的同時也遭遇了另外一小部分人的狙擊。”
朱學勤對黃仁宇的獨特之處表示欣賞。朱學勤說:“他是在中國出了名的歷史學家當中,唯一一個進大學以前有過漫長的、非學院生涯、底層生涯的人士。而在進了大學以後,他沒有把進大學以前的記憶作為包袱,而是作為財富,點石成金,他的《我的大歷史觀》,他的《中國主要問題如何實現在數字化上的管理》等等,和他抗戰的時候做過步兵參謀,在雲南那種瘴氣密布的叢林裡作戰,親眼見中國的西部是如何的荒僻,如何的落後,和北京、上海這些現代化據點差距有多大的這些經歷都有關係。”
然而,兩岸歷史學術界的大部分主流學者,對黃仁宇表示肯定的並不多。有人對他的學術根底表示懷疑。胡文輝在一篇專門批評黃仁宇的文章《局部或有所見,大體仍屬不經》中說:從純學術的角度,他對歷史學及相關社會科學的知識準備仍較欠缺,對歷史的體認往往先入為主,其史學實有嚴重欠缺,他不為美國主流學界接納亦可以說事出有因。
有人對他的寫作方式完全不認同。黃仁宇在文字表達上的強烈個性和不拘一格,他的混合散文、小說和論文風格的敘述方式,讓他的作品在普通讀者讀來味道濃烈,軟硬適度。然而,他也因此備受學術界中那些特別看重學術規範的人的批評。他的文筆在他們看來是“粗野”的,欠缺精準。他的表達方式在他們看來過於注重感覺而非理性。“對歷史的體認往往先入為主,其史學實有嚴重欠缺。”
尤其為他們所不能接受的,是他的“大歷史觀”。黃仁宇很為自己的大歷史觀自豪,他說:“大歷史的概念是無意間得之,是生活經驗的一部分。”他的注重“長時間、遠距離、寬視野”的大歷史觀,迎合了那些想迅速了解中國歷史全貌的讀者的閱讀心理。
但是在學術界看來,他的大歷史觀“粗糙、粗略、粗淺、粗鄙”,“嚴重不成熟”。正如耿立群在《黃仁宇研究資料目錄》一文指出的:“歷史學者或漢學家常質疑其半路出家,學術著作不夠嚴謹;驟然處理數百年、上千年的大歷史架構,總讓歷史學者覺得過於冒險,將歷史解釋簡單化。”
因此,正統學術界的主流看法是,黃仁宇的見解“局部或有所見,大體仍屬不經,真正的史學價值甚微”。大陸學者認為黃仁宇是“歷史學的余秋雨”,而台灣學者則說黃仁宇是“歷史界的瓊瑤”。台灣著名學者龔鵬程甚至說:“我讀黃先生書,輒為其缺乏中國思想、文學、藝術等之常識所驚”,“黃先生的史學和史識是根本不能涉入任何關於哲學與文學領域中的”,“技僅止此,便欲縱論上下古今,可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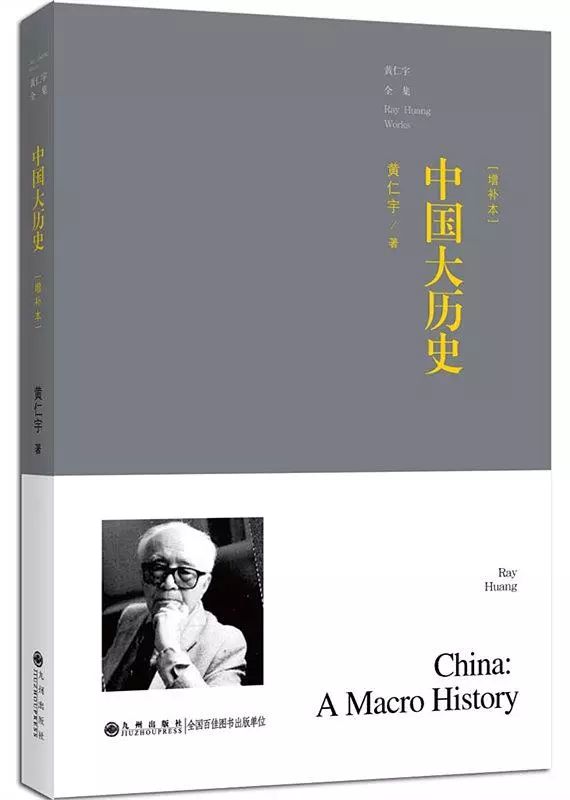
除了對黃仁宇的學術思想不認可之外,中國明史學界對黃仁宇的反感,還在於他個人的性格。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中國明史專家王春瑜在黃氏去世後寫了一篇文章,名為《瑣憶黃仁宇》。文中說,1988年,明史學界召開國際明史研討會,因為一位認識黃仁宇的前輩專家的推薦,他們邀請了黃仁宇。結果,大陸學者驚訝地發現這個美籍學者嚴重缺乏一個歷史學家的“風度”:在另一次討論會上,黃仁宇發言時,說著說著,竟跳起來,蹲在沙發上,侃侃而談。他大概是忘了,這是在國際明史研討會上,而不是在當年國民黨的下級軍官會上,或訓斥國民黨大兵的場所。他這樣的舉動,理所當然地引起與會者的反感。
明史學界反感他的另一個原因,是他在明史會議上不規規矩矩談明史,卻談“大歷史觀”:更讓人不快的是,他在發言中,不談明史,卻大談所謂“五百年大循環”的“大歷史觀”,令我輩聽之無味。……我說:“這是在中國開會,最好只談學術,談明史,免得遭人非議。不能像在美國,您想說什麼就說什麼。”可見他的作風與國內學界如何格格不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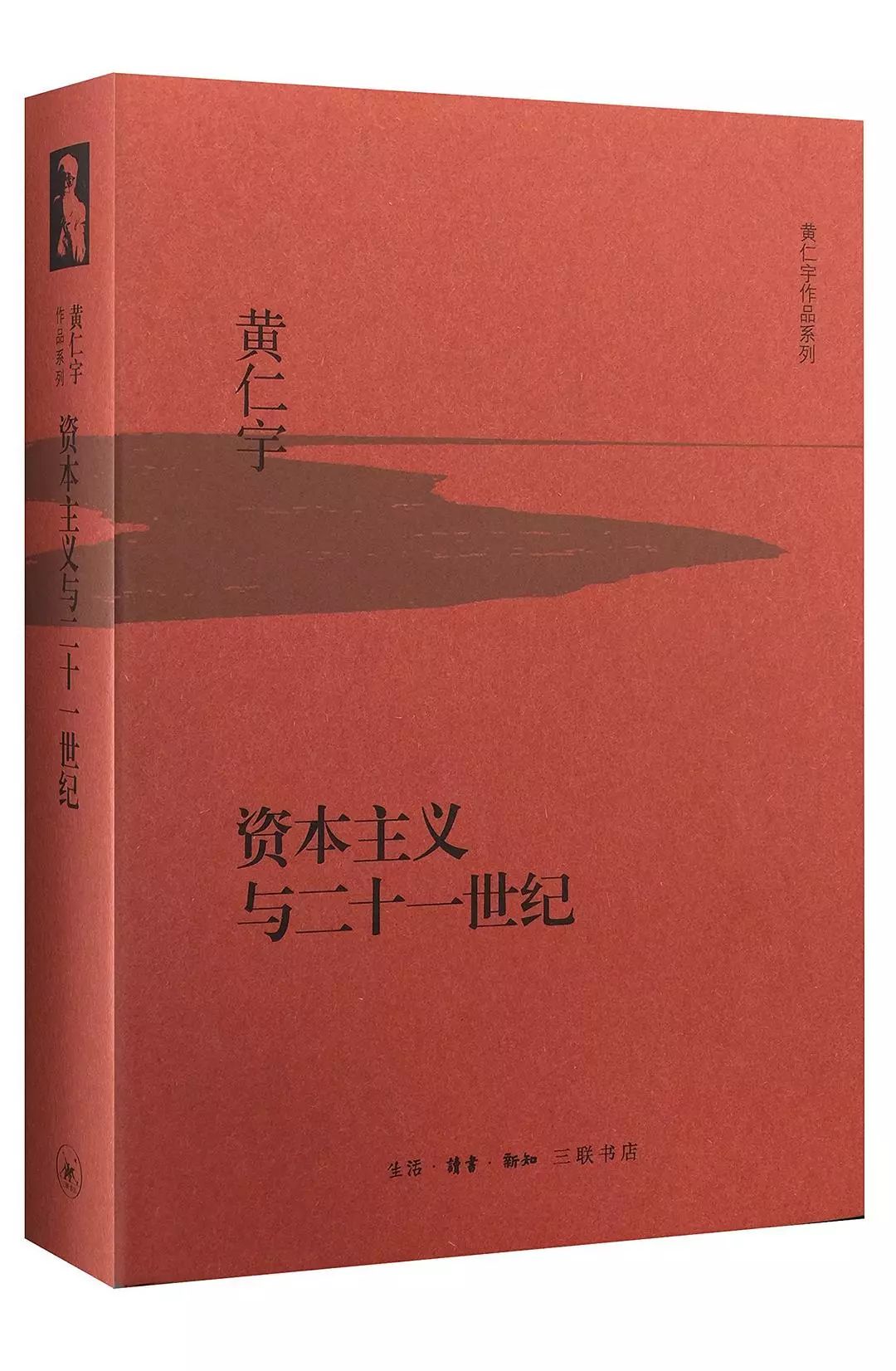
04 “黃仁宇現象”的反思
正是“半路出家”而又“野心勃勃”,導致了黃仁宇的毀與譽。黃仁宇的作品當然不是沒有問題,有些地方存在很嚴重的硬傷。但是,他的洞察力、悟性、歸納能力、綜合能力、“通感”能力是罕見的。他強烈的問題意識和勇氣,他將學術成果通俗化的本領,無人能出其右。
除此之外,即使以學術圈內的嚴格標準去衡量,黃仁宇也是頗有一點學術分量的。他的博士論文《明代的漕運》,他獲得基金支持的專著《十六世紀明代中國的財政與稅收》都是被認可的有相當水準的學術著作。學界泰斗費正清和李約瑟都對他很欣賞,特別邀請他參與《劍橋中國史》、《中國科學技術史》和《明代名人傳》這些重頭學術著作的撰寫。這都是響噹噹的學術履歷。如果他沒有寫這麼多通俗和半通俗的面對普通讀者的歷史著作,如果沒有在普通讀者中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他可能不會受到學術界如此強烈的批評。
黃仁宇評論現代學術的研究方式說:“一般風格,注重分析,不注重綜合。各大學執教的,都是專家,因為他們分工詳盡,所以培養了無數青年學者,都戴上了顯微鏡的目光,對望遠鏡的觀點,倒很少人注意;而且對學術的名目及形式,非常尊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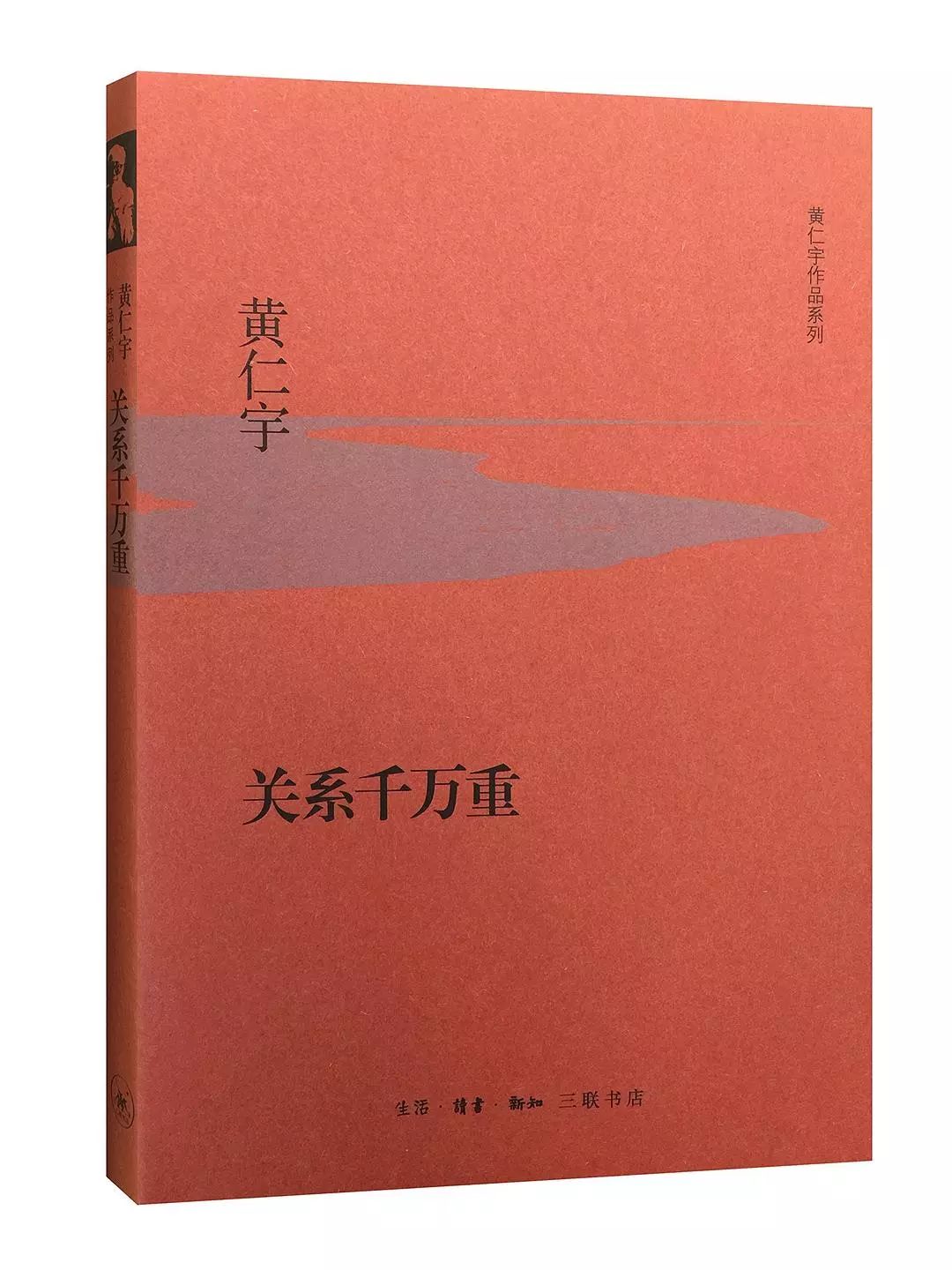
確實是這樣。歷史學術研究方式越來越專業化,是一個全世界範圍內的趨勢。隨著歷史學越來越專業化,歷史學的“致用”價值被“科學化”所遮蔽。許紀霖說:“如今我們的……知識體制所培養的史學研究者,不再是像陳寅恪、呂思勉那樣知識淵博的通人,而僅僅是匠氣十足的專家。
史學墮落為一門純技術的學科,在考證史實的背後,不再有熾熱的歷史關懷,不再有尖銳的問題意識。不少治史者猶如'雨人'一般,除了自己那個狹而又窄的專業領域之外,在知識的其他領域(包括史學的非專業領域),顯現出的是驚人的無知。”
大陸學界在這個方面與台灣、與世界大部分地方情況一樣。這種情況下,史學和公眾的關係也越來越遠,枯燥無味到不少歷史學者都不愛讀。面對社會興起的“歷史熱”,歷史學界不但罕有參與,而且多抱冷嘲熱諷之態度。
因此,黃仁宇雖然收穫了普通讀者的無數鮮花和掌聲,在學術界卻是孤家寡人。“但在另一方面,即他的個人創作方面卻顯得很不幸運。無論是史學界和漢學界,他都沒有多少可以平行、平等、平和地進行交流的同志,他應該是處在獨學而無友的狀態;他在一所並不出名的大學教著一門並不重要的課程;他所進行的一些學術嘗試,也經常得不到多少有力的響應。”
“黃仁宇現象”實際上是對史學界的警示,學術研究應該走出狹小天地,從面向上層和少數精英到面向非專業化的讀者,實現為社會服務功能的轉化。
♦ 專文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