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篇文章轉載自 公眾號 經濟觀察報書評 , 作者 劉玉海、李佩珊。若有侵害著作權,請速告知,我們將盡速移除 ♦
2019/9/24
今年是新中國政府成立70周年。在這70年跌宕起伏的發展歷程中,確立市場經濟體制,無疑是其中最關鍵的轉折:其不僅奠定了其後三四十年中國高速發展、一躍高居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基礎,也是包括前蘇東國家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的特例。
然而,中國通往市場經濟之路卻並非一蹴而就:從1976年10月中國進入轉折時刻,到1984年確定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之前,雖然改革、經濟建設、告別貧窮成為共識,但改革的目標並不明確;而在初步確定這一目標的1985年之後,如何到達商品經濟的彼岸,則成為當政者最頭疼的問題,並在其後幾年連連遭遇各種挫折;直至1992年小平南方談話,才“臨門一腳”將中國在1993年送上市場經濟軌道。這之後,又歷經分稅制改革、國有企業和鄉鎮企業產權改革、價格並軌、銀行體系改革、建立證券市場……一系列傷筋動骨的結構性改革,中國才真正鞏固市場經濟體制。
如今,站在新中國政府成立70周年、改革開放40周年的節點上回望,歷史並未事先為中國劃定這樣一條發展軌跡,而是通過無數人持續十餘年如履薄冰的探索試驗,迭經艱難與驚險,才最終將中國導向市場經濟之路。
對中國通往市場經濟之路所經歷的關鍵問題,近日《經濟觀察報·書評》借《探路之役:1978——1992年的中國經濟改革》出版之際,專訪歷史學者、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改革開放史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蕭冬連先生,期望通過對歷史的打撈以照亮未來。
中國的改革一直有內在驅動因素
▌ 經濟觀察報:您這本紀念改革開放的《探路之役》,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您談到了改革的初始條件對改革路徑和方式選擇的促進作用。一直以來有個泛泛的說法是:中國改革因為漸進才取得成功,而俄羅斯是激進的“休克療法”而失敗,漸進改革就一定會成功嗎?您怎麼看中國改革的漸進路徑?
▌ 蕭冬連:對1980年代改革的突破,我的基本觀點是:改革是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是它的初始條件(改革開放前30年所形成的經濟結構、政治結構)和新的因素(市場化改革、對外開放)重新組合的結果。歷史有轉折性,也有連續性、有路徑的依賴性,改革不是革命(革命也不是一切從頭開始,改革更不是),所以改革裡面,前30年、後30年因素的作用都會有,也許是正面的,也許是負面的,或者兼而有之。首先應該有這樣一個基本判斷。
改革之所以發生,恰恰是我們過去那個發展方式遇到某種危機,才會產生改革的動力。如果改革開放前30年的發展一切都很順利,就沒有改革的必要了。
其實,在1956年前後,中國就面臨一些問題。中國當時的計劃經濟體制,基本是仿效蘇聯的、是蘇聯幫我們建立起來的,包括“一五”計畫的編制。當然也有我們自己的一些經驗,比如根據地的經驗、解放區管理經濟的一些經驗,中國比較有自己獨立特點的,是農業部門管農業這塊,跟蘇聯似乎有一些不大一樣。

蕭冬連
1956年,中國剛剛完成“三大改造”的時候,有兩個背景:一是蘇共二十大暴露蘇聯內部的問題,赫魯雪夫秘密報告傳到中國以後,就引起中國領導人的思考:我們能不能走一條中國式的工業化道路?所謂中國式工業化道路,就是比蘇聯付出的代價小一點,走的更穩定、更快一點的發展道路。二是“三大改造”完成以後,合併的又快又多,小商小販、夫妻店都合併了——這也不完全是政策要求的,他們紛紛要求合併,沒辦法,就把他合了。但他們過去都是特色服務,各種各樣的修理業、服務業,合併後都沒了,群眾生活不方便了;還有一些合併以後,傳統的特色產品品質下降了。企業不再考慮面向市場銷售,就不願意去生產那些麻煩的、各種花色品種規格的東西,只是按計劃生產“大路貨”,於是生產供應和市場需求脫節。再一個就是效益問題。按陳雲的說法,就是“大少爺辦經濟”,合併之後不講究經濟效益,經營上不像過去那樣精打細算了。
所以,1956年,領導人就想對中國的經濟體制做一些改革。毛澤東的基本想法是:下放權力,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加速發展。還有一些人思想更進一步,像陳雲,在八大的時候提出“大集中,小自由”——主要是公有制,但也應該允許少量的個體經濟的存在作為補充。因為計劃經濟很難完全滿足市場的需要、老百姓的需要。
後來因為“大躍進”,這種經濟體制改革嘗試沒有進行下去。“大躍進”不是恢復市場作用,而是完全取締了市場;另一方面,計畫也失去它的權威性了——權力下放到各省市,基本上是一種行政命令性的經濟,這就破壞了計劃經濟的綜合平衡。所以,在1961、1962年搞“調整”的時候,中央把下放到地方的權力又收回來了,修復計畫體制。因為當時不收回權力的話,調整就調不下去。調整有兩個傷筋動骨的舉措:一是大量的企業、建設項目的“關、停、並、轉”,二是把2600多萬城市人口“下放”到農村,這都必須有集中的權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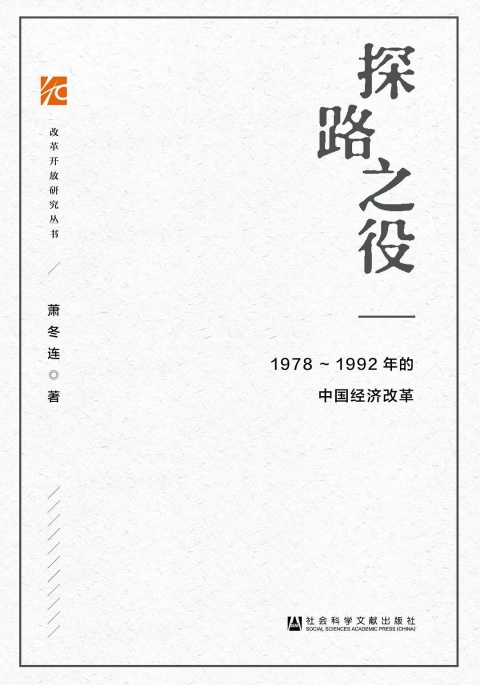
《探路之役》蕭冬連/著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9年3月
這樣一來,1960年代,權力又都集中到中央。但權力集中到中央,馬上又出現新的問題:統的過死,地方又沒有積極性了。而且,權力集中到中央,中央又分散到各個部門管理,其實又是一個分散、分割的狀況。因此,1964年,劉少奇主持了一個托拉斯工業管理體制試驗,同類的企業或者上下游企業聯合、合併起來,後來因為文化大革命,也沒進行下去。
到了七十年代,又有一次權力下放。當時這有幾個背景:一是戰備——“備戰備荒為人民”,毛澤東要求各省市都要建立起獨立的工業體系——包括武器製造都要獨立,因為打起仗來各地方就可以獨立應對。這是中國革命的一個傳統,過去各根據地都能夠獨立幹起來。第二個背景是“五七指示”:農民也學工,工人也學農。再一個是毛澤東提出1980年實現農業機械化的目標。這樣,在70年代,地方“五小工業”(小鋼鐵、小煤礦、小機械、小水泥、小化肥)有較多發展,社隊企業在一些地區就也發展起來了。
所以,到1978年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的體制跟蘇聯還是有很大的區別。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區別是:有更大的地方分權。蘇聯基本上是“條條管理”,我們是“條條管理”和“塊塊管理”的結合,地方經濟職能比蘇聯加盟共和國要大得多。第二個區別是:中國的企業大都是中小企業,當時統計,全國35萬家國有企業,真正的大企業只有4000來個,更多的是小企業。還有150多萬個社隊企業。小企業是地方管的,市、區,包括縣一級,也有國有企業。這樣,其實就形成了兩種經濟:一種是中央控制的經濟,一種是地方控制的經濟。地方控制的經濟,有很多很難完全納入國家計畫——因為中國地盤大,各地差別也大,所以地方管的那些企業,很多都是採取物資交換的方式。這種協作其實帶有半市場性質,它不完全是納入計畫的。鄉鎮企業(當時叫社隊企業)相當一批原材料供應,都是靠這種方式來獲得。完全納入計畫,一是國家管不了這麼多;再者,真正完全納入計畫,就缺乏靈活性了。
所以,即便沒有“文化大革命”,中國這個計畫體制的運作也是比較僵化的、不是很順利的。政府也不斷地在改這個體制,但始終沒跳出行政性分權的框框:要麼是中央集權,要麼是地方分權;要麼是“條條”管,要麼是“塊塊”管,就這麼一個迴圈。當時還沒有把分權深入到企業、讓企業成為一個可以獨立經營的實體。
總之,改革本身有它內在的驅動因素。當然“文革”是個催化劑——反思歷史、促進思想解放。但即使沒有“文革”,這個體制運轉也是不順利、需要改革的。鄧小平說,1975年的全面整頓,實際就是一次改革的嘗試。他當時首先考慮的,就是工業管理體制和企業管理體制問題。工業管理體制就是怎麼把大大小小的工廠編排的合理、符合經濟規律,不是部門分割、地區分割的。所以,改革開放後的經濟體制改革,最初就兩個內容:一是擴大企業自主權——開始是基金制,後來是企業利潤留成制、以稅代利……反正試了很多辦法,核心就是要給企業一定的利益、留利,讓他自己能辦自己的事;另一個就是企業改組,把企業“編辮子”、串起來,形成新的生產力。改革最開始的時候,想法也很簡單。
我說這個,是什麼意思?就是:改革確實有它的內在驅動力、內在的需求。從更寬的視野來看,改革也不是中國一個國家的問題。從1950年代開始,蘇聯東歐國家都在探索自己的改革路子,只是沒有走通、沒有突破。最早是南斯拉夫改革。蘇南關係衝突、南斯拉夫被史達林開除出共產黨情報局以後,獨立走出了一條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跟蘇聯模式不同。赫魯雪夫在1956年蘇共二十大的時候,也想改革:包括調整農、輕、重的關係,要發展農業,後來下放權力,要給地方積極性。沈志華講,蘇共二十大的時候,赫魯雪夫想到的那些改革,跟毛澤東想到的有相當的吻合。這說明他們面臨共同的問題。
到1980年代,社會主義國家改革已經形成一個潮流。但是一直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蘇聯東歐國家這種漸進改革一直沒走出來。在這點上,中國市場化改革、向市場化轉型,是一個特例。後來,蘇東國家政權顛覆了,走了另外一條市場化的道路。但這已經跟社會主義改革是不同的事情——所謂改革,至少改革的主體沒變。
八十年代主張改革的經濟學家,恰恰參與過計畫體制的建立
▌ 經濟觀察報:雖然一直有內在驅動因素推動中國改革,但改革開放之初,方向或許並不是唯一的:可能是類似于前蘇聯東歐那種標準的計劃經濟,而不一定會改到市場經濟。很幸運,中國最終走到了市場經濟。那麼,這個方向、這個目標是如何確立的?主要是偶然性因素,還是有很複雜的博弈?
▌ 蕭冬連:改革開放之初的中國,會不會更有可能回到原始的、經典的計劃經濟?我認為,沒有可能。這裡面有一個對陳雲的基本判斷。其實,陳雲想要搞的計劃經濟,也不是蘇聯式計劃經濟,他是要改良型的計劃經濟,也就是八大時他提出來的想法。1979年,他總結38年的基本經驗就說:社會主義經濟最大的缺陷,就是只有計劃、沒有市場,社會主義應該是計畫和市場兩部分經濟組成,現在更應該擴大市場調節的份額。他實際上是看到了蘇聯計畫體制統得過多過死的弊端。
有一個特別有趣的現象:八十年代主張改革的這批經濟學家,恰恰是參與過計畫體制建立的,如薛暮橋、廖季立、徐雪寒、馬洪、杜潤生……其中,薛暮橋最為典型。從1949年開始,薛暮橋就是中央政務院財經委員會的委員、秘書長,後來當過統計局長、價格局局長,反正一直當陳雲的副手,他完全知道原來的體制運轉不靈、有很多問題。比如,計劃經濟首先要有準確的資料,準確的資料依靠統計,可是,他當過統計局長,知道這個資料怎麼來的,反正沒有一個完整的統計。而且,全國這麼多資料要集中到中央,到底准不準確,光統計隊伍就不得了。中央的計畫部門窮於應付各種報表,應付不過來。“一五”計畫到1955年才通過,1957年“一五”就結束了。而這還是完成最好的一個計畫。其他的幾個計畫:“二五”計畫1958年就被拋棄了;後來“三五”、“四五”計畫都沒有做出來,可能只有個綱要。年度計畫也一樣:年度計畫要經過從下到上、從上到下的過程。中央做年度計畫,要徵求各省市的意見,如果省市不同意,那計畫執行不了,必須協調。可是這樣來一兩輪“徵求、回饋、修改”,這一年就過了一大半了,地方上半年不知道幹什麼,下半年就拼命地搶時間……所以,他們完全知道計劃經濟的僵化、不靈活、效率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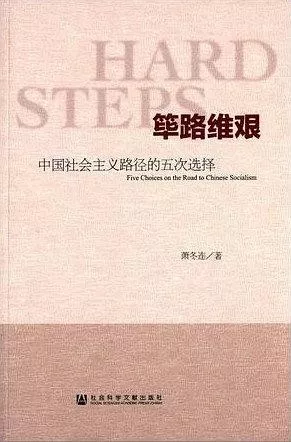
《篳路藍縷》蕭冬連/著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4年10月
陳雲因為長期領導財經工作,他也知道這裡面的問題,所以他的基本想法是,改良型的計劃經濟體制,並不一定是完全回到五十年代計畫時期。但他也不會走得那麼遠,像後來走到市場經濟,這是他沒想到的。他一直認為,必須計畫為主、市場為輔,必須有框框、有籠子,籠子有大有小、可伸可縮,但不管怎麼樣,必須有宏觀的控制在。
有人說,改革開放初期有四派:凡是派,還原派,改革派,民主派。這是很簡化的一種概括,具體到某個事情的時候就比較複雜,不一定是這樣陣線很分明的:在這個問題上他可能主張改革;在另一個問題上他可能比較保守。總之,要在計劃經濟中引入市場機制,是有共識的;但這種市場化走到什麼程度,是有分歧的,在八十年代有反復的爭論。
▌ 經濟觀察報:再回到改革初始條件的討論,因為後來改革開放取得了成就,隨之而來的一種觀點是,改革開放的成功離不開改革開放前30年的積累和條件,你怎麼看?能否用後來改革開放的成功來倒推、甚至肯定前30年?如何看待這其中歷史的連續性和斷裂性?
▌ 蕭冬連:歷史是有延續性的,但這個延續性是多面向的。首先,必須肯定,改革之所以能夠發生,是因為前30年發展不順利。第二,必須肯定,三中全會以後的發展模式跟前30年的發展模式有實質性的區別:一是指導思想從革命的軌道轉到了建設的軌道;二是從計劃經濟轉到市場經濟;三是從單一的公有制結構,轉到了現在多種所有制結構;四是,從封閉型現代化,轉向了開放型的現代化;最後,從運動治國模式轉向了民主法治的治國模式。
總而言之,改革開放前後30年有一個轉折性,如果不承認這個轉折性,改革開放意義何在?另一方面,歷史有一定的路徑依賴,從之前所承接下來的——結構性因素也好、政策性因素也好,它會在重組後對這40年發生影響。這只有通過比較,才能看出中國的發展模式有多少前期的因素在起作用。
前後30年的延續,第一個延續因素是党的領導和強有力的政府。這不是三中全會建立起來的,而是整個中國革命的一個遺產。一個強大的黨政組織系統,在第三世界國家是沒有的,因此,所謂中國模式很難被複製。
第二個延續因素,土地公有制。它在某種程度上型塑了中國的發展模式和改革模式。如果是在私有制土地上,高速公路、高速鐵路,各種各樣的城市化,等等,可能嗎?當然,土地公有制也帶來很多問題,比如農民權益保護問題、土地財政問題、尋租腐敗和浪費問題……但不管怎樣,它確實與我們現在的發展模式緊密相連,是個很重要的因素。
第三個延續因素,經濟結構。我們比蘇聯有更多的地方分權、更多的中小企業。這種結構在前30年,比蘇聯和東歐國家效率更低、技術含量更低,但要把它向市場化轉軌,相對容易一些,“船小好掉頭”。當然許多地方小企業、特別是社隊企業,它本身就在計劃經濟的邊緣和夾縫中生存,在某種意義上就帶有市場交換的特點。
我有一個觀察,可能經濟學家不是特別注意。經濟學家也講農村改革,但在分量上沒看得那麼重。我看農村改革,不僅僅是它本身的作用,而是它對中國整個市場化轉軌和經濟發展的全域性作用。但是,並不是主觀設計先農村改革、再城市改革。它不是自覺選擇的改革突破口,是農民在比較寬鬆的政治環境下、在提高農產品價格的刺激下,不斷衝擊原有政策的底線,然後又得到地方一些領導人的支援、默許,一步一步得到了高層的認可,形成政策。然而,因為農村改革見效比較快,為自己贏得了更大的話語權和合法性。這裡面有一個制度因素:中國的農業是納入計畫的,但是在計畫邊緣,中國的農民既要完成國家計畫,但又沒有享受國家的任何社會保障,他必然會追求自己的發展、尋求突破。農民作為中國改革的一個力量不是自覺的,他並不知道他包產到戶跟中國改革有什麼關係;他尋求的是吃飽飯、要解決溫飽,一個很直接的動機。可是,這確實不自覺的成就了中國的改革。
第四個延續性因素,改革開放前工業化最初的原始積累所打下的某種基礎。有人說,過去的工廠都沒有用了,那些破機器有什麼用?這個說法不對。關鍵是,它已經形成、培養了一批產業工人、技術力量。工業化本身是一個歷史的累積,不能否定前期的作用。
延續性因素裡還有些其他社會性因素——比如教育、識字率,還有傳染病防治,基本醫療保障。1949年,文盲率是90%,真正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更少;但到了1982年,文盲率是23%。中國勞動力是比較有素質的,至少有初中文化程度或者小學文化程度,經過簡單培訓就可以上崗,適應了改革開放初期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加工、適應了沿海地區“三來一補”對勞動力的需要。經濟學講中國的“人口紅利”,很大程度上就是農民工的紅利。
所以,對於歷史,不能感情用事。歷史有它的延續性,有它的轉折性,兩方面都不能否定:否定它的轉折性,改革開放的意義何在?否定它的連續性,那也不是歷史主義的觀點。
(待續)
♦ 專文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