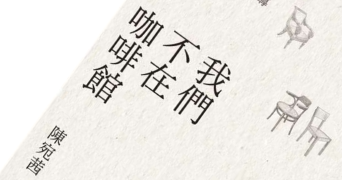♦ 本文轉載自 新新聞。若有侵害著作權,請速告知,我們將盡速移除 ♦
2021/1/18

章詒和撰寫《往事並不如煙》,讓世人看到反右鬥爭的地獄景象。(翻攝自章詒和臉書)
擁有許多讀者的作家往往是會說故事的人。但並非每位受歡迎的作家,天生就會說故事。很多時候,說故事是一種使命。
「我沒有別的本領,就只會說故事。」初冬的北京,章詒和在住家附近的星巴克接受我的採訪。我到現在都還記得,她擁有一雙比七十歲外表年輕很多的眼睛,眼神清亮銳利,彷彿能一眼把人看穿。
「我的家只有律師能進去」
那是北京奧運落幕之後。剛經歷傳統與現代的猛烈衝突,走進胡同,這個城市的歷史深處,觸目所及,到處掛上「拆」字,暗示一個時代要落幕了。但是,即將到臨的另一個時代又是甚麼?霧濛濛的霾害之下,疾走的人們臉上掛著迷惑。
在這些即將灰飛煙滅的胡同裡,人們開始尋找故事。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打開胡同的幽深大門,走出康同璧、儲安平、羅隆基、張伯駒、史良一個個從胡同走出來的最後的貴族,一篇篇美麗淒迷的老故事,迷濛了讀者的眼睛。
筆下人物豐富多彩,溫暖有情;章詒和本人卻有著冷酷的線條,像冬日裡老胡同四合院灰白的牆壁。她不大笑,用詞簡潔犀利;藏在眼鏡底下的眼神銳利如刀,注視我的時候,我感到微微的寒意。
經歷了天堂、地獄、人間三部曲
行前我打電話給章詒和,探詢是否可在她家中見面聊。多年累積的經驗,受訪者的家往往提供更多的線索與暗示,走進他們的家就像走進他們的內心。但章詒和冷冷回答:「我的家只有律師能進去。」
她約了我在星巴克見面,同時強調,她不接受拍照。
「我這輩子,經歷了天堂、地獄、人間三部曲。」坐在咖啡館裡,章詒和簡潔地總結人生的三個階段。
章詒和的父親章伯鈞,是中國民主同盟(民盟)的創辦人。民盟是在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所謂的「第三勢力」。「民盟」一度被共產黨重用,章伯鈞歷任交通部長等重職。章詒和隨父親搬進北京一處擁有九十三間房的大四合院,開始她天堂般的快樂童年。《往事並不如煙》裡的眾多人物,也在這裡登場。
一九五七年,章伯鈞被打成右派,章詒和的天堂生活逐漸走向終點。文化大革命期間,章家多次挨鬥,章詒和更因日記中批判江青,以「現行反革命」的罪名逮捕入獄,掉進了地獄。
二十六歲的章詒和被送到採茶場,過了十年「永遠處於饑餓狀態」的牢獄生活。「我學會了扯謊、罵人、偷東西──這是監獄生存必需的能力。」她曾在懵懂狀況下做了告密者,害人被槍斃。
「我從關進監獄的那一天起,就立志要把『往事』都寫下來。」
《一千零一夜》(又譯《天方夜譚》)中的波斯王妃,為了躲過被國王處死的命運,在夜裡訴說一個個故事。章詒和說故事,也是為了對抗死亡的陰影。她筆下那些高貴細緻、像刻在青花瓷上的故事,是在監獄的漫漫長夜中誕生。
天堂往事沒留下隻字片語
章詒和與齊邦媛,是我所接觸的作家中,記憶最驚人的兩位。齊老師八十歲開筆寫一百萬字的《巨流河》,細細描寫一生中重要的每一天每一幕,人物的對白動作、場景物件描繪細膩,彷彿對照日記。但齊老師告訴我,她的日記早在戰亂中佚失,書中字字句句皆是她根據記憶完成。
飛官張大飛給齊老師的最後一封信,長達逾千字,書中一字字記得清楚,彷彿信就揣在身邊。齊老師說,這封信幾十年前便遺失,「但是,你看過幾千幾萬遍,每天每天在腦海中複述,怎麼會不記得?」
在《往事並不如煙》中,章詒和巨細靡遺描述人物場景、細節動作,做到「往事歷歷如目」。然而經歷文革,日記盡付浩劫,章詒和的天堂往事沒留下隻字片語,只留在她的腦海裡。

章伯鈞(中)被打成右派受盡批鬥,甚至連累全家。(翻攝自網路)
土法鍊鋼開筆寫「往事」
章詒和的記憶力並非天生的好。她說自己國中時曾因「忘性驚人」,創下失物五十三件的紀錄。
十五歲那年,父親打成右派,章詒和被同學孤立,只能跟在父親身邊,記下第三勢力的點點滴滴。二十六歲關入監獄後,章詒和的記憶力更加發達了。在深沉的黑暗中,往事一幕幕在她腦海中上演,一遍又一遍,色彩鮮豔又美麗。
「一個人孤獨到極點,孤獨就成為力量,支持你去記憶。」章詒和臉上毫無表情,聲音卻充滿力量,一字字沉進北京微寒的冬日。
那一代的人,沒有打卡和臉書、雲端硬碟,連日記和信件都在戰火中灰飛煙滅。但是,他們把一生最重要的記憶好好地保存著,等待生命中某個開啟的時刻。
一九八○年代,出獄的章詒和從地獄回到人間。沒受過文學訓練的她,用土法鍊鋼的方式開筆寫「往事」。以史良為例,她在本子上一條條記下腦中關於史良的所有細節,再重新組織這些細節。
章詒和一遍又一遍地重寫、編排情節,同時大量閱讀文學小說、散文。她告訴我,「一個細節可以重寫幾十次」。
歷史是選擇性的記憶。章詒和說,國民黨記國民黨的歷史,共產黨寫共產黨的歷史,不左不右的第三勢力,卻在歷史上蒸發了。
章詒和的堂哥章培毅也是第三勢力。國民黨特務將他關進重慶的渣滓洞看守所嚴刑拷打,還把屍體丟進硝水裡。渣滓洞慘劇曾被改編成小說《紅岩》、電視劇《江姐》,在大陸人人盡知,「裡頭完全沒有提到他」。
章詒和知道,再不用筆勾住亡靈的一點魂魄,這些人曾有的豪情壯舉,就會在時間的硝水中屍骨無存。
回到人間的章詒和,說故事是她唯一的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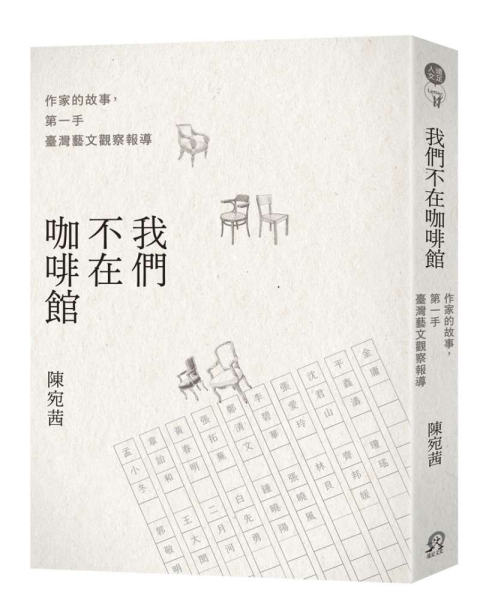
《我們不在咖啡館》收錄作者陳宛茜寫下關於《往事並不如煙》作者章詒和的專訪,談她怎麼經由牢獄寫出人間地獄。
筆下人物都有「亮相」的特質
十年磨一劍。一九九二年她完成第一篇〈憶張伯駒〉,但要到二○○二年,她把〈史良:正在有情無思之間〉登在《老照片》月刊,這才舉座皆驚。
《往事並不如煙》一出場便豔驚四座。章詒和卻足足練筆了二十年,應了梨園俗諺:「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
章詒和原本想念歷史,第一志願是北大歷史系。報考大學前,章詒和向父親請教填志願,章伯鈞喟嘆:「只有藝術家和科學家是乾淨的。」章詒和進了中國戲曲研究院。
章詒和認為自己寫的是人物,而不是歷史。「戲曲最重視人物形象。」研究戲曲多年,她下筆總是細細描繪人物的衣著打扮、舉止神態。她曾向山水畫家潘素習畫,因此文筆像畫筆,沾染層次豐富的色彩、高遠清雅的意境。
中國傳統戲曲最重要的是「亮相」。角兒上場,要先用最美麗的姿態向觀眾「亮相」,博得滿堂彩。章詒和筆下的人物都有這種「亮相」的特質,他們總是先用最美麗的姿態向讀者「亮相」,縱使接下來的命運是如何灰暗悲慘,一如章詒和自己。
「說了這麼多別人的故事,我最想說的其實是自己的故事。」訪問進行了一兩個小時,一直到這時候,我才感覺到章詒和的臉上線條稍微柔軟了,緊閉的內心世界有了點鬆動,四合院的大門輕輕打開一個隙縫。
自傳將是此生「最後一本書」
畢業後,因為家庭成分不好,章詒和被分發到四川川劇團工作,「每天只是寫字幕、賣票。」她和劇團樂師唐良友談戀愛,向政府申請結婚,也因家庭成分遲遲不准。
唐良友陪她逃到了北京,又在鐵窗外等了她十年。出獄後章詒和被朋友「逼婚」,她卻倔了起來:「過去你不讓我辦,現在我偏不辦。」某天這對有情人一時興起跑去登記結婚,終成眷屬半年後,唐良友卻因急性膽囊炎猝逝。
「半夜裡他突然大叫,我開燈,將他抱在懷裡,他已經斷氣了,右眼角緩緩流出一滴淚。」說起這樣疼痛的往事,章詒和臉上還是看不出表情,彷彿述說別人的故事。我不禁想,她是否也在腦海中演練了一遍遍這些情節,努力想找到說故事的方式。
女兒是章詒和另一個痛。她在獄中產下和唐良友的愛情結晶,將她交給娘家撫養;出獄後,母女還是兩個世界的人。「我的後事將由律師辦理」,她臉上還是雲淡風輕。一生以父親遺志為己任的章詒和,卻有一個老死不相往來的女兒。
「我的一生太痛苦了,現在還沒有勇氣提筆。」章詒和說,自傳將是此生「最後一本書」。
採訪結束,我拿了一盒茶想送給章詒和,她搖搖頭:「我不收禮物。這些東西放在家中,死後怎麼處理?」冷冽的話語再度讓我心中一凜,曾經向我開啟的這座四合院,大門再度緊閉。
說完故事,章詒和又把自己關了起來,在身邊築起了一道冷硬的牆壁。身為一個說故事的人,她把炙熱的溫度,都留給了故事。(摘自輯一第十八章〈說故事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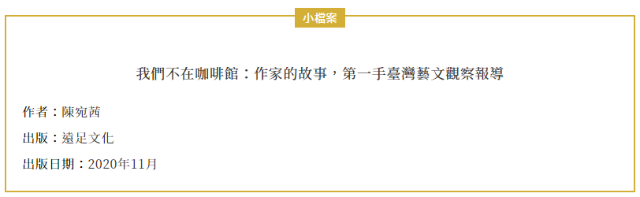
♦ 專文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