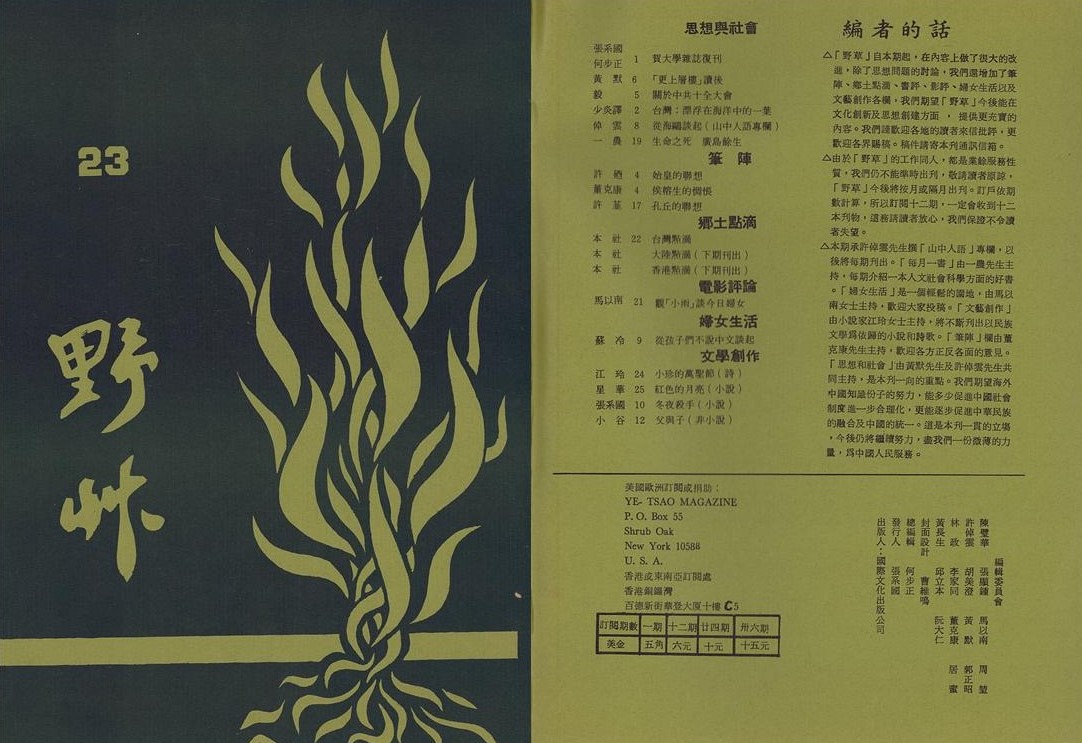編者的話
作者:野草編輯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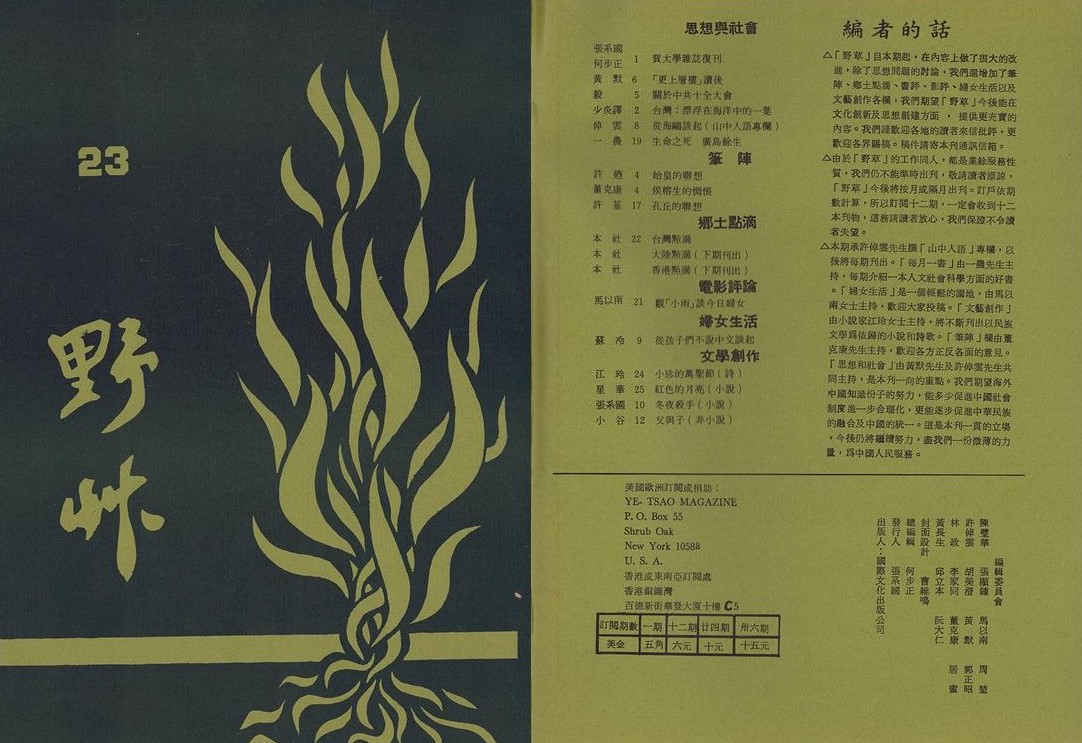
野草第23期內頁
編者的話
- 「野草」 自本期起,在内容上做了很大的改進,除了思想問題的討論,我們還增加了筆 陣、鄉土點滴、書評、影評、婦女生活以及文藝創作各欄,我們期望「野草」今後能在 文化創新及思想創建方面,提供更充實的 內容。我們謹歡迎各地的讀者來信批評,更歡迎各界賜稿。稿件請寄本刊通訊信箱。
- 由於「野草」的工作同人,都是業餘服務性質,我們仍不能準時出刊,敬請讀者原諒,「野草」今後將按月或隔月出刊。訂戶依期 數計算,所以訂閱十二期,一定會收到十二本刊物,這務請讀者放心,我們保證不令讀者失望。
- 本期承許倬雲先生撰「山中人語」専欄,以後將每期刊出。「每月一書」由一農先生主持,每期介紹一本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好書。「婦女生活」是一個輕鬆的園地,由馬以南女士主持,歡迎大家投稿。「文藝創作」 由小說家江玲女士主持,將不斷刊出以民族文學爲依歸的小說和詩歌。「筆陣」欄由董克康先生主持,,歡迎各方正反各面的意見。 「思想和社會」由黃默先生及許倬雲先生共同主持,是本刊一向的重點。我們期望海外中國知識份子的努力,能多少促進中國社會制度進一步合理化,更能逐步促進中華民族的融合及中國的統一。這是本列刊一貫的立場 ,今後仍將繼續努力,盡我們一份微薄的力量,為中國人民服務。今日的女性所應持的態度。中國人常有一種委曲求全的美德。但是我以為這個「全」是「不全」的,尤其是在一個由兩個人共同組成的家庭裏。其實,所謂的「今日婦女」,是一個相當繁雜的複合物。我們這一代的婦女,是正夾在過渡時期中的一代。上一代,是差不多完完全全的家庭附屬物,而下一代,由現在發展的趨勢著來,將是完全被「解放」的一代。而我們,適夾其中,既承受了傳統式的三從四德教育,也接受了現代的解放教育,在兩種思想的沖激中,折中的生活著,也可以說是矛盾與兼顧的情形中生活著。換言之,今日婦女是在一種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中合情形下,是以很難求得一個完全無懈可擊的完美生活形態。

野草第23期(1974/10/01) — 遊子魂--冬夜殺手
作者:張系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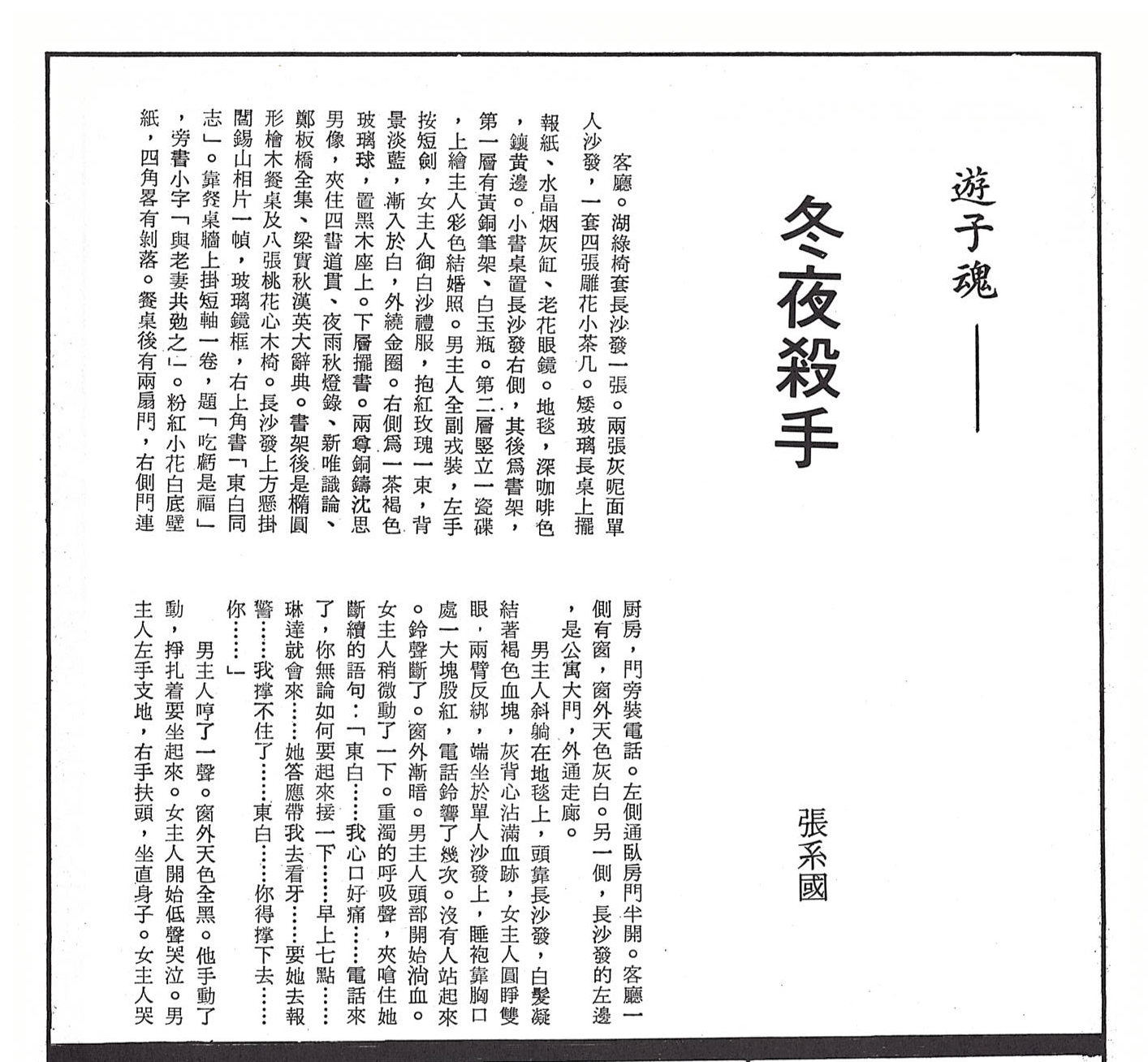
野草第23期(1974年10月)第10頁

野草雜誌老友 2017年10月 何步正 李雅明 張系國 馬以南 胡一凱
客廳。湖綠椅套長沙發一張。兩張灰呢面單人沙發,一套四張雕花小茶凡。矮玻璃長桌上擺報紙、水晶姻灰缸、老花眼鏡。地毯,深咖啡色,鑲黃邊。小書桌置長沙發右側,其後為書架,第一層有黃銅筆架、白玉瓶。第二層豎立一瓷碟,上繪主人彩色結婚照。男主人全副戎裝,左手按短劍,女主人御白沙禮服,抱紅玫瑰一束,背景淡藍,漸入於白,外繞金圈。右側為一茶褐色玻璃球,置黑木座上。下層擺書。兩尊銅鑄沈思男像,夾住四書道貫、夜雨秋燈錄、新唯識論、鄭板橋全集、梁實秋漢英大辭典。書架後是橢圓形檜木餐桌及八張桃花心木椅。長沙發上方懸掛閻錫山相片一幀,玻璃鏡框,右上角書「東白同志」。靠餐桌牆上掛短軸一卷,題「吃虧是福」,旁書小字「與老妻共勉之」。粉紅小花白底壁紙,四角畧有剝落。餐桌後有兩扇門,右側門連廚房,門旁裝電話。左側通臥房門半開。客廳一側有窗,窗外天色灰白。另一側,長沙發的左邊,是公寓大門,外通走廊。男主人斜躺在地毯上,頭靠長沙發,白髮凝結著褐色血塊,灰背心沾滿血跡,女主人圓睜雙眼,兩臂反綁,端坐於單人沙發上,睡袍靠胸口處一大塊殷紅,電話鈴響了幾次。沒有人站起來。鈴聲斷了。窗外漸暗。男主人頭部開始淌血。女主人稍微動了一下。重濁的呼吸聲,夾暗住她斷續的語句:「東白...我心口好痛...電話來了,你無論如何要起來接一下...早上七點...琳達就會來...她答應帶我去看牙...要她去報警...我撑不住了...東白...你得撑下去...你...」
男主人哼了一聲。窗外天色全黑。他手動了動,掙扎著要坐起來。女主人開始低聲哭泣。男主人左手支地,右手扶頭,坐直身子。女主人哭聲更重些。男主人轉過頭,對著大門,沙啞了噪子喊。「你們不要跑!我的頭,天哪!」門開處,兩個黑人跑出去。男主人站起來,攔住高大的一個。高個子的黑人拿什麼東西重重敲他的頭。另一偶拔出短刀刺向女主人胸前。女主人狂喊救命。男主人大聲和兩個黑人論理。女主人陡然尖嚷起來。兩個黑人把女主人按住,拿電線反綁住她的雙手。高個子的黑人抓住男主人的背心,猛力搖撼。「珠寶。我們要珠寶。懂吧?」男主人拼命搖頭,黑人用力抽了他一記耳光。男主人打開女主人的皮包,將所有的東西都抖落到長沙發上。高個子的黑人把鈔票拾起來,數了數,顯出不滿意的神情。女主人咕嚕了一句,被另一個黑人一推,她跌坐在沙發上。男主人挾住女主人,兩人不停地發抖。兩個黑人冷靜的打量他們。矮個子的黑人說:「不許叫喊。趕快拿錢來!」男主人想關上門,但擋不住,兩個黑人推開門衝進來。男主人按著門問:「是誰?」外面回答的聲音聽不真切,似乎說:「修理熱水管。」男主人拔開門門,門被擠開,一隻黑手冒出門縫。男主人放下報紙,摘下老花眼鏡。女主人不高興的說:「這麼晚了,誰還叫門?東白,你去看看。」門鈴響了。一次。兩次。三次。
客廳裏很安靜。男主人坐在長沙發上,戴上老花眼鏡,拿起報紙。女主人在收拾餐具。男主人伸了個懶腰,嘆口氣。「兩個小傢伙簡直無法無天。他們不來,想他們,來了,又嫌他們吵。」女主人站在窗口,自己輕輕搥著背。「唷,今晚可折騰夠了。一頓飯吃了兩個鐘頭。真不曉得平常偉成和琳達怎麼應付。還在下雪。他們回去可不好開車。小傢伙該鬧睏了」
窗外飄著雪。偶爾雪花沾上玻璃窗,隨即化為幾滴水珠。餐桌上杯盤狼藉。男主人握住女主人的手,站在門口送客。偉成抱著方方,琳達牽著圓圓。兩個孩子愉快的喊。「公公再見!奶奶再見!」孩子們笑鬧著,互相追逐著,繞圈子跑來跑去。大人們坐下來。琳達幫女主人端出咖啡。偉成和男主人談論紐約股票市場的行情、水門案件和能源危機,不時喝止方方的惡作劇。安排了半天,大家終於都圍繞餐桌坐好。女主人從廚房端出菜肴,有偉成愛吃的清蒸魚,男主人喜歡的水晶豬蹄,為孩子們燒的糖酷排骨。琳達不吃什麼。琳達在節食,只能喫兩片麵包夾沙丁魚。偉成帶來一瓶杜松子酒。男主人找出開瓶鑽。偉成熟練的拔出瓶塞。杜松子酒時有的香氣,便彌漫在餐桌四週。女主人和琳達都笑了。孩子們一進門就跳上長沙發,蹦上蹦下。琳達連哄帶騙,兩個孩子才肯叫公公和奶奶。琳達先帶孩子進門。偉成好一會才進來,解釋說公寓附近不容易停車。他脫下大衣,抖落一地的雪。白色的雪片,嵌在地板縫內,好一會才消失,留下一點點涇痕。
客廳復歸安靜。現在是下午。女主人在廚房裏切菜。男主人獨自站在窗前。可以看到一棵松樹,松針被凝結於小小的冰柱裏。每一枝松針,都像一根有綠蕊的透明小蠟燭,在陽光下晶亮晶亮。男主人點燃一根香煙。他的目光搜索著松樹後的天空。陽光照進來。他看見空氣裏飄浮的微塵,無目標的遊盪看。光綫順著男主人手中香煙的藍絲,緩緩移動。日光變暗上。松樹了的小蠟燭一齊熄滅。雪花隨即從松樹的後方飛過來,幾乎成水平的角度,從近窗口,才斜斜的落下,仍舊是平穩的、從容不迫的下降。男主人彎下腰。把暖氣開關扭開。女主人剝肉的聲音,有規律的從廚房裏傳出。「下雪了」。男主人喃喃自語。良久,他又重覆了一次。「下雪了」。
中午。男主人和女主人在餐桌鋪上兩張報紙。女主人拿出麵包和果醬。男主人到廚房倒出兩杯牛奶。兩人坐下,默默的吃著。男主人喫完,把麵包屑集中在報紙的一角,小心翼翼的折疊報紙。兩折。四折。八折。女主人看他聚精會神的工作,自己喫完麵包,把報紙依樣折好。兩折。四折。八折。男主人把折好的報紙拿到廚房。女主人收起麵包、果醬、空牛奶杯。他們回坐到餐桌前。男主人說。「他們來喫晚飯?」女主人點點頭。男主人沒有再說話。
下午。女主人拿出吸塵器,一絲不苟的掃遍客廳每一個角落。男主人整理書桌上的兩本書,一疊信紙,他戴上老花眼鏡,從抽屜裏拿出幾封舊信,慢慢的閱讀,讀時嘴唇輕微唸出聲音。女主人細心擦試書架第二層的瓷碟。男主人站在地毯中央,緩慢的練習太極拳。他們坐到餐桌前。男主人到廚房倒出兩杯橘汁。兩人喝完。女主人收拾空橘汁杯。男主人拿抹布拭淨桌上的殘液。他們走出臥房門。臥房門關了。客廳空無一人。窗外天色灰白。松樹漸黯淡成昏黑的樹影。客廳內的傢俱和陳設,猶依稀可辨。天色更暗。只認出書架上的白玉瓶,瓷碟中央的白紗禮服。天色全黑。客廳內毫無聲息。遙遠的,輕微的可以聽見,臥房裏傳出男主人的竹月廿十鼾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