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內容轉載自《文化縱橫》微信:whzh_21bcr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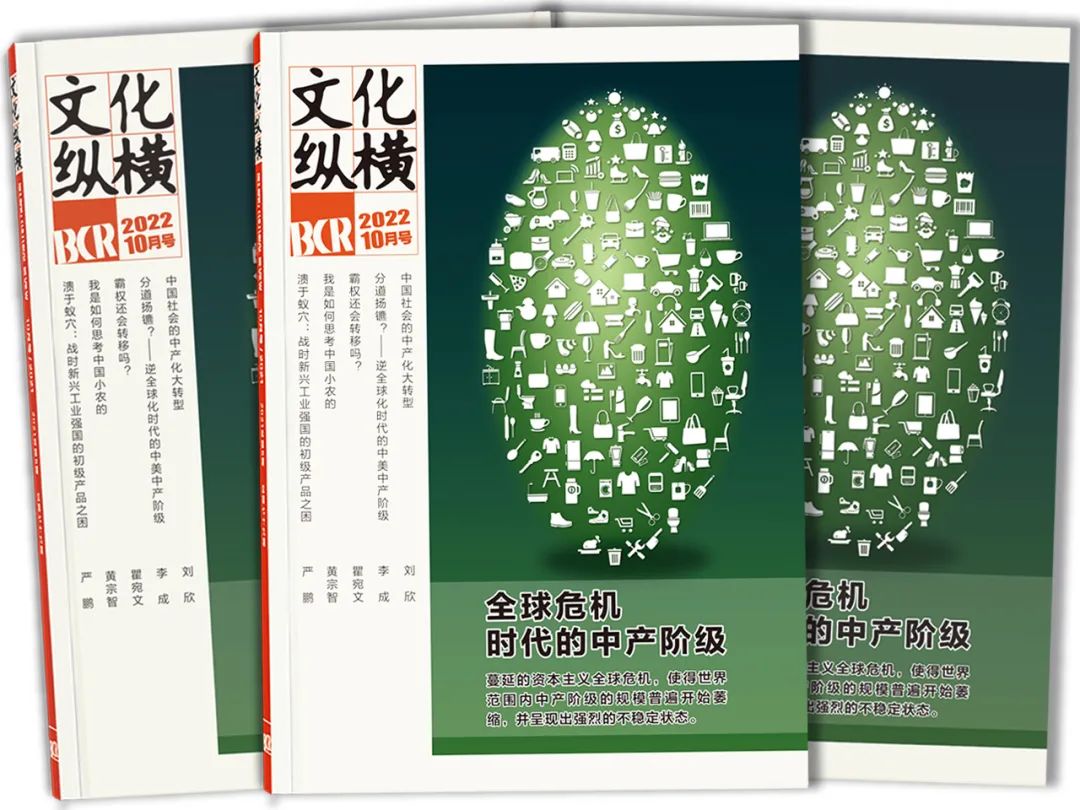
《文化縱橫》2022年10月新刊發行
點擊上圖在文化縱橫微店訂閱
文化縱橫微信: whzh_21bcr
投稿郵箱: Email住址會使用灌水程式保護機制。你需要啟動Javascript才能觀看它
《文化縱橫》郵發代號:80-942
✪章永樂| 北京大學法學院
【導讀】當地時間2022年10月30日,巴西勞工黨候選人盧拉擊敗有著“巴西特朗普”之稱的右翼政客博納索羅,當選巴西總統,標誌著拉美左翼力量“再下一城”。美國一直以來視拉美為自己的後院,歷史上傾向於扶持拉美國家的右翼力量,對左翼政黨則比較警惕。雖然有分析稱近年來拉美政壇新興起的左翼力量反美色彩遠不如以往激進,但仍可以視為拉美國家對自主性的一種探索。那麼,如何理解在地理上直面美國霸權的拉美的主體性?拉美對主體性的探尋,對中國有何啟發?
本文從拉美依附和反抗美國霸權的歷史著手,嘗試對上述問題做出回答。自19世紀末以來,美國的西半球霸權在一個多世紀中從未動搖過,但拉美與西方的關係非常複雜:拉美的前西方文明已基本被毀,現存的拉美文明主要是殖民之後的發展;在拉美許多國家,歐洲移民、美洲原住民和非洲裔居民的混血程度較高;拉美的主要語言與主導性宗教都來自西方;拉美的經濟受美國經濟乃至經濟政策的影響非常深。這些都是拉美反抗美國霸權的艱鉅挑戰。但作者認為,無須期待拉美擺脫“西方性”,真正重要的是,拉美能否在政治經濟上擺脫西方尤其是美國的支配和壓迫,為自身多元因素混合而成的傳統獲取自由舒展和生長的空間。事實上,在思想層面,拉美知識分子始終堅持剖析霸權的構成,思索如何反抗霸權以及如何塑造自身的主體性,由此產生了豐厚的思想成果。而這些對另一個可能世界的深刻思考,恰恰可以和中國的思想者形成“接力”關係。
作者指出,無論我們通過美國還是拉美,認識世界和自我都是可能的。從美國的視角來看待世界,或許可以直觀地認識到支配的快感,讓認識者或認同既有的支配結構,或生長出“彼可取而代之”的雄心。然而,以中國的巨大體量,一廂情願地認同和尋求“融入”既有的支配結構,並不會被霸權接納;而如果尋求對霸權力量的簡單替代,不僅會遭遇反擊,更無法得到既有支配結構下被支配者的認同。因此,作者建議,中國更應該取道拉美而認識世界和自我:中國屬於發展中國家,中國最為堅實的基礎在於“第三世界”;只有當中國與全世界大多數民眾站在一起的時候,才有可能凝聚起足夠的力量,突破支配體系的“薄弱環節”。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22年第8期,原題為《霸權、依附與反抗:拉丁美洲的主體性》,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參考。
霸權、依附與反抗:拉丁美洲的主體性
如果不是因為寫作“門羅主義”全球史著作《此疆爾界》的機緣,我也許很難真正從心靈上“重逢”拉丁美洲。17年前,我曾經在洛杉磯的“小哈瓦那”迴聲公園(Echo Park)居住一年,每天穿過熙熙攘攘的講西班牙語的人群。我知道那些古巴流亡者可以與美國的“歷史終結論”者發生什麼樣的共鳴。但對於“門羅主義”話語和實踐的思考,讓我意識到,拉丁美洲的諺語“離天堂太遠,離美國太近”背後有著多麼痛切的歷史體驗。
自19世紀末以來,美國的西半球霸權在一個多世紀中從未動搖過。美國的軍事霸權、金融霸權、技術霸權牢牢箝制著西半球。不僅如此,用一位拉美國家高級外交官的話說:“美國更像是梵蒂岡,你很難被其接納,你必須遵守很多規則,而且還要去懺悔,但你仍有可能會受到詛咒,而不是去往天堂。”這顯然是一個充滿天主教色彩的類比,美國絕不僅僅是一個世俗權威,它經常祭出自己的正當性原則,不斷質問拉美國家,並要求其“懺悔”。
要理解被殖民者長期稱為“西印度”的拉丁美洲的處境,不妨將其與殖民者眼中的“東印度”即東南亞地區做一個對比。西班牙和葡萄牙16世紀就在這兩個區域建立起穩固的殖民統治,後來又有荷蘭、英國、法國等殖民者加入。在兩個區域的不少地方,發展出了類似的社會經濟特徵,如大莊園、大地主和天主教的強大影響力。拉丁美洲的民族獨立運動比東南亞要早一個世紀,但兩者的歷史境遇大大不同。由於地處冷戰前沿,不少東南亞國家獨立後得到美國的扶持,同時也獲得日韓製造業的帶動。中國經濟進入高速增長期後,東南亞國家加強與中國的貿易和產業合作,經濟發展進一步加速。在地緣政治上,很多東南亞國家也是“左右逢源”獲取資源。
而19世紀以來,許多拉丁美洲國家獨立後經濟上先依附於英國,後依附於美國。二戰後,隨著美國霸權的進一步鞏固,拉美各國受其影響程度也逐漸加深。如巴西在1960—80年代一度推行“進口替代”戰略,實行貿易保護,吸引外資在國內建立工廠,然後補貼中產階層購買國產工業製成品,以期建立相對完整的工業體系。1970年代,由於石油危機的影響,美國開始實施寬鬆的貨幣政策,在國際借貸利率較低的情況下,巴西大幅舉債,擴大公共開支。然而美聯儲從1979年開始加息,國際資本大量流出巴西,導致債務危機爆發。至1990年代,巴西走上新自由主義道路,還處於保護期的許多本國工業企業在進口商品的衝擊下紛紛垮掉,大量國有工業企業被私有化,公共服務大幅削減,貧富差距急劇拉大。21世紀重新上台的左翼政權走上了依靠出口農產品和礦產資源等大宗商品、補貼窮人以拉動消費市場(同時也保證選票)的道路,但這樣就缺乏資源投入基礎設施建設與製造業,嚐到社會福利甜頭的勞動者也很難再安於枯燥的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崗位。由於拉美政權無法避免國際大宗商品市場的波動與美聯儲貨幣政策的巨大影響,一旦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外資撤離,財政收入暴跌,政治動盪也就接踵而至。而政黨輪替通常意味著經濟政策的大幅震盪。最近拉美的政治鐘擺再次向左偏移,但只要經濟基礎沒有改變,恐怕拉美就很難擺脫這種充滿動蕩的政治週期。
拉丁美洲沒有成為“世界工廠”,更談不上進一步升級為“世界實驗室”。與東南亞相比,它的製造業要更加薄弱,在互聯網等新興領域,拉丁美洲更是美國跨國企業的天下。即便部分拉美國家開始在大國之間搞平衡,也沒有東南亞那樣的地緣政治條件。美國在拉美的霸權是相當穩固的,缺乏扶植拉美經濟的動力。拉美國家如果觸動美國資本的利益,其結果或是政黨輪替、經濟政策轉向,或是像古巴和委內瑞拉那樣被長期制裁,經濟外向發展空間嚴重受限。
儘管如此,拉丁美洲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幫助我們認識這個世界秩序的本來面目,進而更好地理解中國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下的主體性所在。以西方殖民者為中介,中國在明代就與拉丁美洲發生經濟關聯——大量美洲白銀的流入對於中國內部經濟的運行產生了深刻影響,美洲農作物的傳入更是影響深遠。但中國與拉美的直接交往要等到19世紀。廢除奴隸制後,一些拉美國家偷運華工填補勞動力缺口,而中國與這些國家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往往從華工問題開始。如1874年,中國與秘魯就華工問題展開磋商,簽訂《中秘友好通商條約》,但由於兩國圍繞在秘華工保護存在分歧,直到1909年才完成換約。甲午戰爭之後,在對中國被列強“瓜分”的恐懼之中,像康有為這樣的精英人士還產生了華人大規模移民巴西、再造一個中國的想法。同時,由於美國“排華”的影響,很多在美國的華工也轉往拉美,而他們勞作的種植園有許多是完全掌握在西方資本家手裡。正因如此,在反抗殖民主義的鬥爭中,華工往往和拉美本地底層民眾並肩作戰,共同爭取政治經濟獨立和自主。
接下來,中國人對拉美的認識進入政治制度層面。1906年,康有為曾經在墨西哥的托雷翁設立華墨銀行,投資有軌電車,並一度想前往巴西考察。1911年,墨西哥先於中國發生革命,反政府武裝攻入托雷翁,洗劫了華墨銀行,並殺死大量華人,其中包括康有為的族人康同惠。而這為康有為對於共和製的負面看法增添了新的材料。在民國初年,康有為不斷撰文論證共和製會造成種種不穩定和動盪。為此,他不得不將美國處理為一個例外,即認為它能行共和製而保持穩定,只是因為存在一些特殊條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隨著共和製在歐亞大陸的傳播,康有為的這些批評意見就很少有人追隨了。但可以說,由於康有為的介入,在美國與拉美政治制度的比較研究方面,中國的起步絲毫不晚,儘管此後缺乏持續跟進。
一戰之後,隨著“覺醒年代”的到來,中國的進步人士在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框架裡,認識拉美被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壓迫的歷史,並產生深刻的共情。1949年之後,中國更是大力支持全球的反帝反殖革命以及第三世界國家獨立自主的經濟發展。1960年周恩來總理接見智利文化教育界人士時提出:“美國有門羅主義,而你們拉丁美洲應該有個新的拉丁美洲門羅主義,不讓人家干涉,自己團結起來,完全組成一個強大的經濟力量。”周恩來總理建議的“拉丁美洲門羅主義”,其重點就在於拉美國家建立一個共同的經濟體系,自主地與其他國家展開經濟交往,擺脫美國的控制。1970年代中美關係緩和;1980年代以來,中美經貿關係日益緊密。但與此同時,中國與拉美交流中的經貿分量,也在不斷加重,尤其是“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後,雙邊經濟合作更是有了長足進展。
這些歷史經驗可以幫助我們思考當代中國主體性的構成。中國有著非常完整和系統的、從未中斷過的古代文明,在近代是少數未完全淪為殖民地的非西方國家之一。中國通過深刻的社會革命,重新獲得獨立自主,走出了一條“自主性開放”的道路。而拉美的前西方文明已經基本上被毀滅了,現存的拉美文明主要是殖民之後的發展。在拉美許多國家,歐洲移民、美洲原住民和非洲裔居民的混血程度較高。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強調的,在殖民地時期,歐洲移民的後代克里奧爾人(Creole)已經發展出與宗主國不同的民族認同。但西方性一直存在於拉美的血脈裡,其主要語言與主導性宗教都來自西方。無須期待拉美擺脫這種“西方性”,因為人無法選擇自己的祖先。真正重要的是,拉美能否在政治經濟上擺脫西方尤其是美國的支配和壓迫,為自身多元因素混合而成的傳統獲取自由舒展和生長的空間。
拉美在思想上所貢獻的最為深刻與普遍的成果,大多與對霸權的抵抗有關。在認識層面,拉美思想者對西方的各種“輝格派史觀”進行祛魅——這種“輝格派史觀”認為西方的繁榮源於其內在製度的優越性,而製度優越性又可以追溯到其遙遠的文明源頭。自1980年代以來,這樣的敘事模式對中國的思想界與學術界影響深遠。但拉美學者集中審視內外關係,指出其殖民宗主國的富裕,首先並非因為製度和道路有何內在優越性,而是憑藉強大的暴力,在外部進行剝削和壓迫,汲取了額外的財富,從而改變了自身發展的環境和條件。殖民地依附於宗主國的局面一旦形成,即便照搬那些所謂“優越”的製度,也無法擺脫依附和不發達的狀態。著名的“依附理論”就源於拉美思想者的探索,普雷維什(Raul Prebisch)、弗蘭克(Gunder Frank)、卡爾多索(FH Cardoso)、多斯桑托斯(Dos Santos)等學者均有深刻貢獻,後來又有阿明(Samir Amin)這樣的拉美以外的第三世界思想家加入。而美國社會學家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則通過綜合依附理論與現代化理論,創立世界體系理論。阿根廷經濟學家普雷維什的結構主義發展觀雖然沒有促成拉丁美洲國家擺脫不發達狀態,但在第三世界產生了很大影響,以林毅夫為代表的中國經濟學家正是在普雷維什的結構主義發展觀的基礎上,推進“新結構經濟學”的建設。
在政治層面,墨西哥學者海因茨·迪特里希(Heinz Dieterich)提出“21世紀社會主義”,這個口號被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Hugo Chávez)接過去並進行新闡釋,一度對拉美的新自由主義產生強大衝擊。在“21世紀社會主義”口號之下,查韋斯發起美洲玻利瓦爾替代計劃(後改名為美洲玻利瓦爾聯盟),抵制美國倡導建立的美洲自由貿易區。巴西學者、政治家昂格爾(Roberto Unger)引領了美國的批判法學運動。拉丁美洲也是反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的基座所在,許多共產主義者、社會民主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與民粹主義者參與了這個論壇的討論。拉美豐富的民粹主義運動也產生了重要的理論成果。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隨著歐洲與美國民粹主義的興起,阿根廷思想家拉克勞(Ernesto Laclau)對民粹主義的解析,獲得了全球性關注。
此外,更不用說哥倫比亞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García Márquez)的《百年孤獨》給1980年代的中國作家帶來的衝擊。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莫言坦言自己和馬爾克斯“搏鬥”了多年。當然,莫言只是藉用了馬爾克斯魔幻現實主義的風格與技法。而正如書中馬孔多屠殺所集中體現的,殖民主義、霸權和反抗,是深嵌在《百年孤獨》中的主題。對於1980年代急於“走向世界”的許多中國作家來說,《百年孤獨》激發的是他們對於中國文明的絕望感,甚至20世紀的中國革命也被他們納入了對於歷史輪迴的想像之中。而到了21世紀,全球政治與經濟版圖的變遷,讓我們越來越能看清,我們經歷的絕非一場輪迴——沒有20世紀的中國革命,就不會有獨立自主的中國工業化道路和吸引全球注目的經濟崛起,也不會有今天美國統治精英對其全球霸權失落的深刻恐懼。
在今天,1980年代“走向世界”的問題意識,有必要獲得新的發展。關鍵的問題是“走向一個什麼樣的世界”。中國需要與廣大發展中國家一起努力,打破既有國際秩序的霸權結構對於發展權的種種不公正限制,而這意味著中國自身主體性的某種更新。二戰後的日本思想者竹內好曾從主體性塑造的角度立論,倡言“以亞洲為方法”。在他的視野中,“亞洲”代表著一種“抵抗”的主體性,而不是一個地理性的實體——因此,古巴也可以屬於“亞洲”,而以色列則不屬於“亞洲”。類似地,可以說拉丁美洲代表著這樣一種主體性:其內部包含西方文明的許多因素,卻又受到現實的西方尤其是美國霸權的壓迫;它不斷地進行著抵抗,探尋新秩序的可能性。儘管尚未走出一條很成功的發展道路,但它的探索與抵抗本身就是對這個霸權秩序的不公正性的揭示。正如拉丁美洲的“結構經濟學”在中國激發“新結構經濟學”,拉丁美洲思想者對另一個可能的世界的思考,很多是相當深刻的,恰恰可以和中國的思想者形成“接力”關係。
當然,在日本還可以看到這樣一種回應:強調對霸權的抵抗,也可能帶來受制於霸權所設置的議程的結果,因而走向一種相反的一元化秩序想像。這正是溝口雄三對竹內好進路的擔憂——竹內好對中國近代以來道路的肯定,將日本置於反思對象的位置之上。而溝口自己的“以中國為方法”,則試圖用中國前殖民時代的歷史經驗和原理,來理解和解釋中國近代以來的一系列變化,通過一個特殊的中國,將西方特殊化,從而展示出世界的多元圖景;在這樣一個多元世界中,日本也能獲得一個比較舒適的位置。
而我們無須過多捲入這些爭議細節之中。竹內好的視角將古巴與“亞洲”關聯在一起,這正好提示我們,中國一度大力倡導的“亞非拉”認同具有多麼強大的思想力度。在反抗世界的霸權結構方面,中國與拉美有著相通的歷史記憶和共同利益,拉美對自身發展道路的思考和實踐,是中國探索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的重要參照。在原住民文明被殖民主義摧毀的拉美,像溝口雄三研究中國那樣挖掘前殖民時期的歷史經驗和原理看起來是極其困難的。但我們可以梳理所謂“地理大發現”以來歷史的層層累積,在其中可以看到,一些殖民主義的因素後來被轉化為反抗的資源。比如,來自伊比利亞半島的傳教士曾經在殖民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今天神學可以轉化為批判霸權的資源。拉美共產黨人在處理與天主教的關係方面,有著許多獨特實踐。而經歷過拉美“解放神學”熏陶的方濟各,已經成為天主教世界的教皇。在這方面,中國與拉美恰恰能夠互為鏡鑑,在對方身上看到自己的特殊性,同時也更深刻地認識到彼此社會實踐的強烈共時性。
無論我們通過美國還是拉美,認識世界和自我都是可能的。從美國的視角來看待世界,或許可以直觀地認識到支配的快感,讓認識者或認同既有的支配結構,或生長出“彼可取而代之”的雄心。然而,以中國的巨大體量,一廂情願地認同和尋求“融入”既有的支配結構,並不會獲得霸權力量的接納;而如果尋求對霸權力量的簡單替代,不僅會遭遇反擊,更無法得到既有支配結構下被支配者的認同。
相比之下,取道拉美而認識世界和自我,也許更能接近世界的真相——而這不過是20世紀歷史已經揭示的一個道理:中國屬於發展中國家,中國最為堅實的基礎在於“第三世界”;只有當中國與全世界大多數民眾站在一起的時候,才有可能凝聚起足夠的力量,突破支配體系的“薄弱環節”。正如馬克·吐溫所言,歷史並不會重複自身,但會押韻。一個片面尋求“融入”支配體系的時代已經結束,一個更為自覺地建設更加公正的國際秩序的時代已經開啟。讓我們在這個時代剛剛落下的韻腳之處,與拉丁美洲重新相遇!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22年第8期,原題為《霸權、依附與反抗:拉丁美洲的主體性》。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


(點擊文末左下角“閱讀原文”訂閱新刊)
訂閱服務熱線:010-85597107 13167577 398(微信同)
工作時間:週一至週五早8點至晚8點
♦專文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