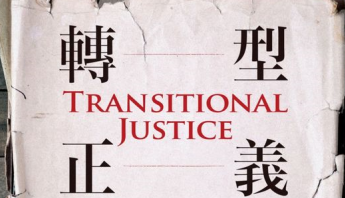Transitional justice is made of the processes of trials, purges, and reparations that take place after the transition from one political regime to another.
Jon Elster(2004: 1)
Transitional justice can be defined as the conception of justice associated with periods of political change, characterized by legal responses to confront the wrongdoings of repressive predecessor regimes.
Ruti G. Teitel(2003: 69)
Transitional justice is a response to systematic or widespread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It seeks recognition for victims and promotion of possibilities for peace, reconciliation and democracy. Transitional justice is not a special form of justice but justice adapted to societies transforming themselves after a period of pervasive human rights abuse. In some cases, these transformations happen suddenly; in others, they may take place over many decades.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n.d.)
The notion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discussed in the present report comprises the full range of processes and mechanisms associated with a society's attempts to come to terms with a legacy of large-scale past abuses, in order to ensure accountability, serve justice and achieve reconciliation. These may include both judicial and non-judicial mechanisms, with differing levels of international involvement (or none at all) and individual prosecutions, reparations, truth-seeking, institutional reform, vetting and dismissals, or a combination thereof.
Kofi Anna(2004: 4)
為實現社會正義、司法正義、歷史正義、土地正義和分配正義等轉型正義,由國家設置調查和解委員會,對歷代統治者所掌控而加諸原住民族的國家暴力歷史進行再梳理與詮釋、發掘真相,藉以釋放被壓抑與噤聲的歷史記憶,建立具各族群共識的「共享歷史」,達致「真相追尋」、「族群承認」,以及「國民和解」的目的;並對原住民族因而流失的土地、語言、文化、征戰傷亡等給予適當賠償;任何調查結果產生前,由總統代表政府為四百多年來原住民族所遭遇的剝削,向原住民族道歉。
蔡英文(2016)
轉型正義
「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是指「轉型時期的正義」(justice in time of transition)(Mouralis, 2014: 87)。簡單來說,轉型正義是指在一個國家在進行民主轉型(democratic transition)之際,要如何面對先前威權、或是極權體制所造
成的人權侵犯;相對之下,廣義的轉型正義是指國家在經歷巨幅的政治變動之後,要如何來看待過去(coming to term with the past),特別是舊政權(ancien regime)所留下來的不公不義(injustice),也就是支配政治、經濟掠奪、社會壓抑、以及文化霸權(Elster, 2004: 1; Teitel, 2003: 69; Olsen, et al, 2001a: 9-13)。因此,轉型正義並不侷限適用於正在從事民主化的國家,而那些已經確立的民主國家(established democracy)並沒有排除適用的道理。
根據Teitel(2003)所提供的系譜,轉型正義的發展可以約略分為三個階段(phase)1:第一階段(1945-89)是指由戰後到冷戰結束,主要是由戰勝國對於戰敗國所從事的國際正義,也就是紐倫堡大審、以及東京大審對於戰犯的審判;第二階段(1989-2000)是指由冷戰結束到千禧年到來之前,由中美洲軍事政權、東歐共產政權、到非洲獨裁政權相繼民主化,政治轉型之際如何處理人權侵犯、同時著手社會的和解;第三階段(2000-)則是指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轉型正義已經被世人廣為接受,尤其是「國際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CC)在2002年設立,因此稱為「穩定狀態」(steady-state)的轉型正義,也就是所謂轉型正義的正常化。
我們如果把轉型正義分解為成因(X)、機制(Y)、以及目標(Z),機制是被解釋的應變數、或是政策產出(output),而成因是用來解釋的獨立變數、或是輸入項(input),最終要看所轉型正義的結果(outcome)是否能達成原先意圖的目標。首先,就轉型正義的機制而言,不管是加以報復、或刻意失憶,都不是好的選項,那麼,在光譜的兩個極端之間,可以有司法審判、行政洗滌、真相調查、補償還原、及特赦除罪等作法(圖1)。
接著,轉型正義的立即目標就是要伸張正義,才有可能進一步談社會和解;同樣地,如果社會不能和解,民主的實踐將淪於投票主義,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再回到進行轉型正義之際,必須先釐清真相,否則,就不會有起碼的正義;當然,和平又是更高的境界,特別是正面的和平。由真相、正義、和解、民主、到和平,表面上看來,這是一個環環相扣的鏈狀因果關係(causal link),然而,我們認為這是一系列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換句話說,儘管前件的完成未必保證能獲致後件,前件卻是要達成後件所必須(圖2)。
正義可以分為修正式正義(rectificatory justice)、以及分配式正義(distributivejustice)(Estrada-Hollenbeck, 2001; Roberts, 2002; Rawls, 1971; Barkan, 2000):前者是強調如何處理過去所犯的錯誤,又可以進一步分為處罰式正義(retributive/retroactive justice)、及修復式正義(restorative/restitutive/reparative justice)兩大類,後者則是追求政治權利、經濟資源、社會地位、及文化認同的公平分配。我們可以說,前者是為了課責(accountability),後者是為了公平(fairness)。如果以前述轉型正義的發展來看,第一階段關注的是處罰式正義,第二階段是修復式正義,第三階段兼顧兩者(Muvingi, 2009: 165)。
再來,究竟要如何促成轉型正義,那是政治運作的實務,必須歸納實踐的經驗。我們先前建構了一個轉型正義的概念架構(施正鋒,2016),分別以人民的需求、以及政府所的提供 2 ,來說明政治菁英從事轉型正義的意願:前者包括他國的示範效果、先前的壓迫經驗、以及舊政府的退場方式 3 ,後者除了直接面對選民的壓力,還會考慮政治場域的競爭、以及國際的壓力;至於媒體的報導、以及憲政法庭則扮演中介的角色,可以強化、或是弱化轉型正義的進行(圖3)。
最後,轉型正義過程的行為者當中,除了受害者(victim)、以及加害者 4(perpetrator),在光譜的中間(圖2),往往也有置身度外、甚至於冷血的路人甲旁觀者(bystander, onlooker)。旁觀者是否那麼無辜,值得探討,因為,有些人即使並非權貴、更非幫兇,卻是「不小心的受益者」(accidental beneficiary),當然要捍衛舊體制 5 ;當然,前者至少還可以藉口在不得已的情況下虛與委蛇,未必都是機會主義者(opportunist)。然而,學者林健次(2016)卻點出所謂「聰明的利用者」,難怪不少人堅持維護國民黨政權的現狀。
真相調查委員會
自從第三波民主化在1974 年於葡萄牙展開以來,四十多年來,約有一百個國家經歷民主轉型,其中,如果以比較嚴格的標準來看,有超過三分之一採取真相調查的模式 6 (Dancy, et al.: 2010; Hayner, 2006, 2001; Freeman, 2006: Appendix 1)(附錄1)。不管稱為「真相委員會」(truth commission)、還是「真相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這是一種妥協的轉型正義途徑,也就是說,在司法審判不可能的情況下,又不甘心就此遺忘,只好選擇採取真相調查,至少能讓真相水落石出。基本上,這是一種相對上比較薄弱的轉型正義工具;東歐國家的轉型正義普遍進行洗滌,而拉丁美洲國家則多半採取真相委員會,主要是因為軍頭尾大不掉、文人政府投鼠忌器(Skaar, 1999)。
真相委員會是國家針對過去一段特定時期的人權侵犯,臨時成立的一個具有調查權的委員會(Teitel, 2003: 78; OHCHR, 2006: 1; Dancy, et al., 2010: 49; Hayner, 2011: 11: Freeman, 2006: 18)。國家的調查委員會(commission of inquiry)大體有三種:首先是由國會或是行政部門針對特定事件、或議題所成立的特別委員會,前者在任務完成即解散,後者則比較像是諮詢單位;接著是常設的人權保障獨立機構,包括人權委員會 7 、或監察機關(ombudsman);再來就是為了處理轉型正義所特別成立的真相委員會,這是一個任務行的編組,通常是在撰寫調查報告以後就解散。
國家之所以要成立真相委員會,顧名思義是要調查過去所發生的人權侵犯,也就是想辦法了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再來是透過調查報告的撰寫、及公布,一方面宣洩社會長期壓抑的不滿,另一方面則具有教育大眾的作用;接著是政府承認過去做錯了事,而社會也接受自己有相當程度介入的事實;只有在大家都願意面對事實的情況下,特別是加害者及受益者原意祈求原諒、而受害者也願意原諒,整個社會才有可能和解、受傷的心靈才能獲得撫慰及復原;最後,委員會的報告必須提出具體建議,才能避免重蹈覆轍(Schlunck, 1998: 418-19; Hayner,2001: 24-31)。總之,就是了解過去、承認錯誤、避免犯錯(OHCHR, 2006: 1-2)。
當然,徒法不足以自行,光是設立真相委員會未必就會有真相、更不用說達成社會和解 8 。為了避免資源或權力不足,真相委員會的運作必須有相當的條件。首先是政治菁英必須有和解的意願,否則,真相委員會很可能淪為政黨意氣之爭的另一個場域:再來是整體社會是否支持、百姓會不會給政府的壓力,否則,也不過是另一個掛虛有其表的機構(Schlunck, 1998: 419; OHCHR, 2006: 2-3)。當然,政府是否有心推動,還是會衡量社會大眾的要求、以及剛下台在野力量的拉扯,換句話說,朝野的相對實力是關鍵(Skaar, 1999)(圖5):
圖 5:社會要求與舊政權的角力
由於擔心政治力量介入,絕大部分國家排除國會調查、或是行政調查,另外成立超然的調查委員會,聘請社會上具有公信力的人擔任委員,不設在總統府、或是國會之下。同樣地,司法單位即使可以針對孤立事件進行調查,畢竟還是屬於國家體制的一部分,獨立性難免被質疑;國史館的任務是國家歷史的纂修,恐難獨挑調查真相的大樑。而國家人權委員會所面對的是當下的人權侵犯個案、而非過去的通案,並不適合;監察機關主要處理人民跟政府來往之際的權利受損,範圍還是有其侷限性,尤其是國家對於原住民族的集體權侵害。
一般而言,國家級的真相委員會要不是透過國會立法、就是總統頒佈行政命令所設置(見附錄1)。不管設在立法、行政、或是聯合運作,真正的差別在於是否國會立法授與調查權(subpoena power)(Freeman, 2006: 188-204; Hayner, 2001:214)。經過修憲後的中華民國體制,儘管朝向總統制,卻還有一個行政院長,總統成立的任何組織只能算是諮詢機構,類似目前的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表面上位高權重,卻不會有真正的調查權,這也是目前原住民族最關注的地方。
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
到目前為止,轉型正義的框架主要用在威權體制的民主化,尚未被廣泛運用到被視為榜樣的西方自由式民主 9 (liberal democracy)。就概念上而言,這裡牽涉到語意、以及相關的時間軸線爭辯。誠然,就字面來看,轉型正義是由轉型、及正義兩個概念所組成,由於transition 又有「過渡時期」的意思,難免讓人望文生義,誤以為只是後威權時期的短暫措施。事實上,轉型正義就是要處理過去所有的不公不義(historical injustice),也就是為了歷史正義(historical justice)。難道,正義會隨著時間的遞嬗而有所不同?如果硬是要區分「過渡時期的正義」、以及所謂的「歷史正義」,這樣恣意的歷史切割,其實就是一種推卸責任的作法;根據Barkan(2000: xxxi),有點像是吃自助餐,只點想要吃的菜。
儘管轉型正義已經蔚為國際社會的主流,Sharp(2013: 151-52, 157)認為它迄今未能觸及深層的結構性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 10 ,因此主張如果真的要建構和平 11 (peace-building),也就是追求正面的和平(positive peace),就不能光是重視政治制度的改革、或是斤斤計較法律技術枝節,而是必須採取整體的(holistic)途徑,將關心的範圍由傳統對公民與政治權的關懷,延伸至一向被當作邊陲的社會權、經濟權、及文化權保障,亦即前述分配式正義、或是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 12 ;他同時也力促,應該將關懷的對象由國家及個人擴及社區及群體。Sharp(2013)把這些當務之急稱為第四代的轉型正義。在這樣的脈絡下,先進的民主國家成為必須面對轉型正義的對象,尤其是那些建立在征服原住民族的所謂墾殖國家 13 (settlers’ state),譬如美國、澳洲、紐西蘭、及加拿大(圖6)。
拉丁美洲國家比較傾向於使用真相委員會進行轉型正義,其中,瓜地馬拉、秘魯、智利、巴拉圭、以及阿根廷涵蓋跟原住民族的和解(EMRIP, 2013: 19)。瓜地馬拉的調查委員會是透過游擊隊與政府的和平協定設置的,原住民族並未參與;政府原先拒絕接受調查的報告,經過十年,才終於在2011 年承認軍方進行滅族,逮捕了一名將軍(Arthur, 2012: 37, 40)。澳洲國會在1991 年立法設置了原住民族和解理事會(Council for Aboriginal Reconciliation),於2000 年提出報告,教 育社會大眾的性質比較高、實質效果有限( Gunstone, 2005; Weston, 2001:1036)。加拿大政府面對原住民族針對當年教會寄宿學校的人權侵犯集體求償,只 好 庭 外 和 解 , 被 迫 在 2008 年 立 法 成 立 了 真 相 和 解 委 員 會 14 (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於2015 年完成報告六冊(Arthur, 2012: 39; Jung, 1999:6-9; Angel, 2012; Park, 2015)。
比較特別的是紐西蘭的「外坦吉特別法院」(Waitangi Tribunal),這是依據『外坦吉條約法』(Treaty of Waitangi Act, 1975)而來的常設準司法機構,主要的任務是受理毛利人對於『外坦吉條約』(Treaty of Waitangi, 1840)保障下的權利的聲索(claim),行使調查權,功能有點像台灣的監察院,不能算是真相委員會。雖然外坦吉特別法院的報告沒有約束力,不過,司法單位、以及行政單位往往不敢輕忽它的看法、以及建議。在1985 年,外坦吉特別法院被授權回溯調查毛利人在過去的土地權、以及漁獲權受損( Byrnes, 2004; Hayward & Wheen,2004)。
聯合國(United Nations, 2010: 8; EMRIP, 2013: 18)以「真相權╱知的權利」(right to the truth, right to know)著眼,認為真相委員會是近用正義(access tojustice)的途徑之一。只不過,真相委員會未必能解決原住民族的問題,除了在實際運作上的技術問題,譬如委員會的獨立及公正性、政治干預、經費不足、族人的參與不足、以及缺乏後續執行方案,整體來看有下列重大的挑戰(Jung, 2009; EMRIP, 2013: 19-21; Librizzi, 2014: 188-91):
範圍:原住民族所遭遇的人權侵犯包山包海 15 ,包括主權╱領域╱土地╱以及資源的流失、與國家簽訂的條約╱協定╱協議未被遵守、以及集體的被殖民經驗。然而,就廣度與深度而言,往往真相委員會被授權調查的範圍受限、過於零碎,自然未能真正挖掘問題的根源。其實,所有墾殖國家與後威權國家的最大不同,就是原住民族的主權不被國家承認、傳統領域在無主之地(terra nullius)的假設下被剝奪、以及土地資源以各種藉口被挪用;因此,如果政府不能正視這項事實、重新定位國家與民族的關係、調整以墾殖社會為中心的心態,那麼,任何的補救將有如以繃帶掩飾傷口。
途徑:傳統的真相委員會習於以個人受害者來檢視個案,忽略到原住民族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甚至於環境權利遭到侵害,包括政治排除、流離失所、強迫同化等等;由於這是有系統的集體迫害,墾殖者國家是最大的加害者、而墾殖者通常被描繪為無辜的受益者,因此,就沒有人必須負責 16 。此外,各國的真相委員會同常會以可行性為由,將調查所涵蓋的期間限於轉型之前的威權統治時期,換句話說,假設見證人還活著、或是文字記載還留著;然而,他們無視原住民族遭遇迫害已經有好幾百年,肩上的重軛並未隨著時間推移而消去,族人的苦難透過口傳代代傳下來。最後,這些委員會的調查往往以國家為中心、忽視原住民族的世界觀,轉型正義不過是墾殖者確認現有支配的工具。
動機:對於政府來說,轉型正義的目的之一是在歷史劃一道線,透過調查、道歉、以及補償,墾殖社會可以跟原住民族說:「我們從此不欠你們了!」換句話說,當下的政府把轉型正義當作一個場域,用來告別歷史、不必再為過去負責,而原住民族在國家領導者道歉後也應該可以閉嘴了 17 。相對地,原住民族認為轉型正義並非一道牆、而是橋樑,要透過真相委員會將歷史帶入現在、用過去的政策批判現今所遭受的不公義處境;所以,轉型並非切割、而是關係,透過真相的承認來引導政府接受自己的責任,並經過公共的爭辯來理解,原來,原住民族的生存受到限制、發展受到打壓,其實是源自政策底層的隱形壓迫性結構。
在所有的墾殖社會,原住民族的邊陲化是因為長期被排除(excluded)在主流社會之外;然而,如果轉型正義只是透過納入(inclusion)來鞏固國家的正當性,那是一種包藏禍心的再殖民(recolonization)(Matsunaga, 2016)。因此,我們再回頭檢視轉型正義的目標(圖2),不談民主、或是和平,由真相到和解之間,必須先有正義,問題是,我們需要何種正義?由轉型正義四階段的發展,我們可以看到,已經由修正式正義的推廣到分配式正義,難道這樣還不夠?
Fraser(2005)主張正義應該有重分配、承認、以及代表三種,不可脫鉤處理 18 。首先,即使支配者願意進行重分配,如果不能轉換彼此之間的關係,轉型正義終究也不過是確認現有的宰制,也就是必須由「確認式正義」(affirmative justice)提升到「轉換式正義」(transformative justice);亦即,社會、或是經濟場域的重分配,必須建立在承認彼此文化差異的前提下,而非假設不對稱的同化關係是自然的(Petoukhov, 2012; Gready, et al., 2010)。換句話說,如果不能以「民族對民族」(nation to nation)的方式來相互傾聽,所謂的重分配也是假的(EMRIP, 2013: 21; Jung, 2009: Librizzi, 2014: 188)。
再來,Fraser(2005: 305)認為不公不義的背後除了有經濟社會場域的「分配不均」(maldistribution)、以及文化場域的「錯誤承認」(misrecognition),其實,在政治場域的「失幀」(misframing)也必須同步解決。也就是說,面對政治空間的傑利蠑螈化,弱勢者光是有發聲的機會還不夠,在戰術上還必須結合國內外的進步力量。因此,當漢人國家以任何理由來合理化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的分開處理 19 ,即使出於善意,那又是另一種形式的排除,我們必須戒慎小心,並竟,原住民族在四百多年來,又不是第一次被騙。
(明日待續…)
*發表於小米穗原住民文化基金會主辦、台灣原住民研究學會合辦、台灣原住民族政策協會協辦「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學術研討會」,台北,立法院群賢樓 101 室,2016/7/30。
1 請勿與 Huntington(1991)的人類三波(wave)民主化浪潮混淆:第一波始於十九世紀、第二波始於戰後、第三波始於 1974 年的葡萄牙康乃馨革命迄今。不過,Teitel 的第二階段轉型正義與Huntington 的第三波民主化倒是有重疊。另外,有關於轉型正義做一個研究領域的發展,特別是在 1990 年代,見 Mouralis(2014)。事實上,轉型正義在 1980 年代已經成為專門的研究領域(fieldof study)。位於紐約的「國際轉型正義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成立於 2001 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的期刊《國際轉型正義學報》(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itionalJustice)已經進入第十年了。
2 我們發現,Dancy 等人(2010: 45)也有類似的構思,他們的用字是「對於正義的需求」(demand for justice)、以及「所提供的轉型」(supply of transition)。
3 Huntington(1991)觀察第三波民主化的經驗,根據朝野的相對實力,將民主轉型的模式分為舊勢力主導質變(transformation)、朝野協商(transplacement)、及由反對者取而代之(replacement):一般而言,如果是由舊政權主導轉型,改變的幅度會比較小;相對地,要是由反對勢力來主導,就比較有可能巨幅改革。
4 當然,我們也可以把幫兇(collaborator)列入加害者,特別是線民。
5 譬如那些擔任接收大員的「半山」,或是一些附和國民黨、「光復有到」的人。
6 根據 Olsen 等人(2010b: 806-807),在 1970-2004 年期間,總共有 74 個國家經歷民主化、從事91 次轉型正義、成立了 53 個真相委員會。
7 如馬來西亞人權委員會(Human Rights Commission)調查原住民族土地權(EMRIP, 2013: 18)。
8 有關於真相委員會的效果,見 Bakiner(2013)、以及 Brahm(2007)的實證研究。
9 Jung(2009)稱這些沒有進行政權轉移的社會為「非轉型社會」(non-transitional society)。相較於轉型正義是非常時期的正義,Ohlin(2007)稱為「尋常正義」(ordinary justice)。
10 根據和平研究學者 Galtung(1969),暴力有三種,我們最討厭的是直接暴力,也就是流血跟戰爭。其實,弱勢者每天早上睜開眼睛所面對的是結構性暴力,隱諱不明,卻是殺人不見血。當然,最高段的是文化性暴力,由支配者決定價值思想的對錯,絕對不允許有討論的餘地。
11 由暴力到和平,可以有三種途徑:比較保守的作法是保持現狀,在衝突發生以後,想辦法避免近一步惡化,也就是「維持和平」(peace-keeping)、或是「恢復和平」(peace-restoring);比較主動的作法是要「營造和平」(peace-making),積極降低彼此的敵意、辦法建立和諧的關係,甚至於不惜改變現狀,全力「建構和平」。
12 參見 OHCHR(2014)、United Nations(2010)、Muvingi(2009)、Sankey(2014)、以及 Schmid 與 Nolan(2014)。
13 Balint 等人(2014)則乾脆稱之為「墾殖者的殖民國家」(settler colonial state)。
14 美國緬因州政府在 2013 年成立類似的真相和解委員會(Maine Wabanaki-State Child Welfare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已經在 2015 年完成調查報告(EMRIP, 2013: 19; Sharon, 2013; McCrea, 2013; MWCWTRC, 2015)。
15 不管稱之為結構性傷害(structural harm)、結構性不正義(structural injustice)、墾殖者的殖民(settler colonialism)、還是內部殖民(internal colonialism)(Balint, et al., 2014; Arthur, 2009; Park, 2015; Short, 2005)。
16 譬如加拿大的真相委員會被限定調查個別學生的創痛,族人則希望能探究集體的文化戕害,有相當大的差距(Jung, 2009: 10)。倒是 1991 年成立的「原住民族調查委員會」(Royal Commission on Aboriginal Peoples, RCAP),針對原住民族的困境,在 1996 年完成有六千頁的五冊調查報告,向政府提出 440 項未來二十年的政策建議,範圍比較綜合性(Hurley & Wherrett, 1999)。
17 保守黨出身的加拿大總理 Stephen Harper(2006-15)便認為,加拿大政府對原住民族的人權保障已經做得很好,沒有必要再簽署『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2007)(Fraser-Kruck, 2009)。
18 參考 Fraser 與 Honneth(2003)有關於重分配(社會經濟結構)、還是承認(文化認同)孰重的對話。
19 譬如林雍昇(2015)、或是陳翠蓮(2016)。
推薦閱讀: